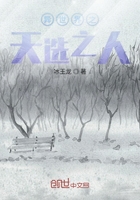半黎心思转了几转,目光落在赵元隽身上时,突然闪过一道精光,不落痕迹的低下了头,心中冷冷的笑着,
“真是无冤不成父子,无债不成夫妻。”
人生四喜,前三喜她还没遇上,今儿倒是让她赶上了一出,真真就是他乡遇故知——债主,这个国公爷,指的就是镇国公府,她看着眼熟的赵元隽正是半黎的亲生父亲,那个弃她们母女不顾,连带着想不起有她娘这个人,更加不关心她存在的生父。
俗话说,生女肖父,更得父亲的偏疼,原主儿却是白生了这张脸了,连带着得生父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
也就只起了个DNA认证的作用,不必二十二对染色体基因对比,就可以百分百的确认血亲,她刚就觉着赵家父子看着眼热,尤其是这赵元隽真是面熟的很,却原来是因着与半黎相貌像了八分。
半黎悄悄的抬眼不着痕迹的又是看向正握在赵元隽手中的那杯茶,这一杯茶算是她敬的吧,以后多多关照,父慈女孝了。
戏台上伊呀的唱腔十分优美,梨哥儿的杜丽娘,无论是伴相还是唱腔,都是美到极致,就算是不懂行的听着了,也真是一眼就惊才绝艳,半黎耳听得梨哥儿字正腔圆的唱曲,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朝飞暮倦,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
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人世之中,何尝不是一出游园惊梦的戏,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半黎娘一世凄苦,只留一句,苦死也叫冤,十五岁的半黎,饱受作践,生生叫人打死,这赵家欠了半黎母女的,命运转了个轮回,却又是让她撞回来了。
这是上苍,也给她一个重来的机会吧,这么一来,一切计划都要改了,原想着,借着这个堂会,跟京中贵人攀上关系,下一步上京城寻亲爹时也有个靠山,诺大的京城,又不知道镇国公府的身家内情,若没有个可依靠,单是她和琪哥儿二个弱少年,必会给欺负了,现在,倒是更好了,连拐弯都不必了,正撞上正主。
半黎在心中默默的计算着时间,楼台上的戏文唱再精彩也是戏,楼下的戏才真更具观赏性的真实人生。
再唱得二出戏的功夫,半黎眼瞧着赵元隽的脸色有些发白,后排座的几个人趴到了茶桌子上,面如土色,就是碍于贵客在,咬牙强撑着不敢动,神色越见灰败,紧紧的揉着小腹。
半黎悄悄的探手到衣角,捏紧了手中的绣花针,这是要发作了,也快该是到她登场的时侯了。
赵元隽面色更加难看,腹中绞痛,头晕一阵阵的发作着,忍不住的恶心欲吐,自小就是娇养的爷,从未受过什么磨励,怎么经得过,这样的折腾,也不及向许世友告退,翻过身子,趴在桌子上,先是冲着地就是一阵呕吐,污秽之物溅得满地都是,酸腐之气冲充在戏楼里。
台上正是琪哥儿刚上场,正演到鲁智深醉闹五台山,琪哥儿正唱着《寄生草》的曲儿,
“漫搵英雄泪,相离处士家。
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
没缘法转眼分离乍。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
未等着唱完,就被楼下这一出更加精彩的戏打断了,傻愣愣的看着台下,不知所措,连着拉琴的师傅,都是呆怔着忘了给转折,把这段曲再糊弄过去,台上台下,目瞪口呆的看着还在狂吐着的赵元隽,面面相觑。
赵东泰气得胡子都经倒竖起来,这个嫡子,就是不给他作脸,出来个作个客,身子骨也弱成这样,居然在人前这样豪无形象的吐着,都是让他娘自小宠惯坏了!
虽是生气,到底还是关心儿子,冷着脸,赵东泰低声问:“你怎么了?可是吃着寒凉的食物冲撞了脾胃?”
赵元隽有气无力的摆摆手,面色如纸,半合着眼晕眩着,说不出完整的话,许世友毕竟是见惯了世面的人,面不改色,关切的问,
“元隽兄,即是身体不适,可先到客房中稍事休息,我现就去请名城中名医,给元隽……”
话还未等他说完,坐在后排座分散的几个人,却也是绷不住了,背过身呕吐起来,顿时满戏楼里都是酸臭的味道,楼上的女眷己是坐不住,磕磕绊绊的座椅声中,哭泣声,尖叫声,喧闹声都有,下人们也是乱了套,跑进跑出。
许世友的脸色极为难看,若说是单赵元隽一人吐,还可说是他身体不好,给他请个好大夫,国公爷还要记得自己这番维护之情,可是这一戏楼的宾客,都有呕吐的,这不主是明晃晃的说,是在他的地盘上,出得变故,实实在在就是打了他一个耳光,许世友站起身,怒斥着一屋慌乱的人群,
“都慌什么!各回各位!”
一声令下后,到是稳住了局面,半黎站在门边,颇为赞赏的看着许世友,临危不乱,处理果决,不愧是能掌控两淮盐运的主儿,确有几份本事,她倒是不急着出手,看他接下来怎么处置,一台戏里,总有要配角才能突出主角,这个压轴的时机,还未到。
许世友一声令下,招呼着周管家:“快去把辛大夫请来。”
辛大夫是扬州城名医,住在槐子街,离许府颇远,来来回回,也要个半把时辰,这屋里己经痛的几近要打滚的人,却是等不及了,痛嚎声,呕吐声不绝不于,赵元隽更是最突出一个,直接眼一翻晕了过去,正好躺在了他身己刚吐完的那堆秽物上。
国公爷这时也反应了过来,不是自家儿子有问题,而是许家这里出了茬子,面上当即就是一冷:“世友,还是请扬州知府过府一查罢,我看这是另有蹊跷,幸得淮安营参将李德路派兵先把住这四外,不要让人自由进出的好。”
经过几朝的朝局更迭,国公爷心中自是明镜一样,今天这事,必是人为的,说得不好,或许还会与金鸾殿那把座椅有牵扯,否则哪会那么巧,真就赶在他们父子来作客时出了这种事,先保护着现场,控制住进出人员,把事儿查个一清二楚才能定论,圣上年迈,朝中正为着下一位继任人,争闹不休,这种局面下什么事都会有。
半黎冷着眼看着国公爷的处置,是个有远见有谋算会运筹独握的,这样短的时间就有这个判断,并作出应对对策,果真不愧是朝中重臣,可惜,他还是算的错了,这上演的可不是朝廷上那样包着阴谋的明刀暗枪,内闱的手段不是一个男人能意会的了的。
许世友额角流出了冷汗,忙应下来,正在叫呼人去隔壁淮安营参将李德路中支会一声,国公爷板着脸一挥手,从身后的随从中站出一个人,小步的跑向戏楼外。
许世友张了张口,想解释又合上嘴,现在他说什么都没用,国公爷显见的把自家也算进去了,这样的事,也只能等辛大夫来查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再去分辨了。
半黎不着痕迹的冷着眼看着,早在帮着许府下人,打点摆放盘果时,她就做下了手脚,做局要不留缝隙,四角俱全,因此上在选目标是,她定下的目标就不是在最前面正中主座上,即是许府最重要的客人,连着许府老爷都要尊着的人,那自然不能动。
否则一出了事,府里官职最高的是许大人,他自是不会把人留在这里等着查问,先就怕担干系的急送回府中救治了,哪里还有她出场呢,必先要有个官职比他高的人,身份上能压制得了他,却也不能不给他几份情面。
而且若单只是一个人出事,更是太过明显,把目标分散开了,都有同样的症状,这才能把事情当场闹得大了,就此二相对恃,必须在当场解决,这才会有她出场的机会。
半黎又是看了国公爷父子一眼,显见得是父子情深,赵东泰己是急的变了脸色,捏紧了手中的针,默默的盘算着,现在,还不是时侯……,蹬蹬蹬的脚步声,从楼上跑下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妇人,人影未到眼前,先是一阵夹着香粉的娇哭声,
“老爷,老爷,你这是怎么了,可不能有事呀,我们母女俩下半辈子就指望着老爷您了,这可怎么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