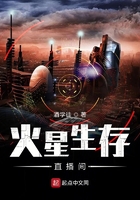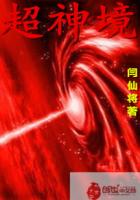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在一家酒店里找到了传菜员的工作。
为了庆祝我们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余良就花了一大手笔买了一台现代朗动。他说,这台车是去年南美的销售冠军,一直都想买,赶上最近在降价终于决定买了。我问,降了多少?他说,不多,也就几百块钱。我说,那不等于没降嘛。他说,那别人做生意也就是为了赚钱,所谓的降价也就只是意思一下而已,要是一降几万块,那还不强疯了。对于余良突然的大手笔,我表示这是个完全没有预知的结果,因为在事前毫无声息。但不知为何,我竟然有些迫不及待想要见到的感受。
那一天余良将车买回来停在了学校的围墙外,他带我去看车时我们一起翻过围墙。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那边有门,而且还没有上锁。他说,你不能这样想,我们应该居安思危,要是门上锁了,那我们不就出不去了。我指着一面墙道,其实即使门上锁了也可以出去,你看,那面墙就有个大窟窿。余良说,你不觉得那样太简单了吗?这样子更感到惊喜呀!我的心情依然很平静,但我知道余良此刻的心情肯定是不能平静。我平静是因为那车不是我的,而他不能平静的原因正是相反。
见余良满怀激动的表情,我只好假装心情跟他一样,但无论如何也只是假装,无论怎么假装都不能将他的车变成我的。虽然我们将共同行使在一条路上,而且我也将获取这辆车的使用权,但我终究找不到驾驭的满足感。
我跟余良来到车内,余良津津乐谈向我介绍这车的性能。余良说了半天,我能听懂的就是知道这个车是自动挡的。当然,这跟我平时一向不管心车有关。即使是关心也不能如何,我也不再做无谓的冲动。依余良是个富家子弟来看,他必定对车了解许多。
我心生不解,问道,“这车既然是自动挡,为什么还要保留手动挡?难道会用手动挡的人还不会用自动挡吗?”
余良解释道,“这你就不懂了,手动挡省油,而且变速快。”
我在一边应承道,“还是你懂得多。”
余良介绍时,他说到音响时吸引了我的关注。他说,这部车一共有四台音响,前排两个,后排两个。我暗自想,在这么小的空间就有四台音响,打开播放器的时候肯定是无敌地震撼。人就是这样,总是想去尝试自己所感兴趣的东西。还没来得及等我去打开多媒体的音乐,余良就已经点了一首歌,果然重低音的效果达到了至极,至少是我所认为的至极。
在买到车的第二天,我们驱车来到工作的地方。酒店里的员工见我们开车来做传菜员表示惊讶不已,在他们眼里里可以看得出来恨不得这车就是他们的。我们工作所在酒店足有九层之高,除了吃饭住宿之外还提供娱乐场所。因为是新开张正缺人手,毫无顾忌的我们就漂流到了这里。
老板性格很好,整天乐呵呵的。他总说这家酒店是整个城市里最大的,由此他还说他就是这个城市里最大的老板。这位老板穿着很是喜庆,他也喜欢很喜庆的东西。让我们认为喜庆的是,许多事物在他的眼里都是喜庆的。因为这样,我们的工作也就容易的多。他还给自己的酒店起了个自己认为很是喜庆的名字,叫做“如喜酒店”。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老板希望如喜能够如他所愿。但更多时候名字其实是个象征,而所谓的象征往往是很难办到的。
赶上忙的时候,除了传菜之外我们还担当配菜的任务,虽然我们配出来的菜一直都不是很好看。当然,当我们传菜时揭开盖子的一瞬间偶尔还是会听到顾客的抱怨。这也说明了一点,只要是味道还不错,模样难看点还是可以勉强吃下去的。但我想,要是我们传的不是菜而是小姐我们早就被开除了。出于一直没有人向老板反应我们配的菜模样太难看,我们一直侥幸地继续工作着。这家酒店也这样在我们手下勉强继续经营。
在酒店里我们遇见了一个姑娘,她是一个来历不明并且莫名其妙的姑娘。当我们第一眼碰见的时候,那姑娘就一把拉住余良不肯放手。再仔细看着那姑娘时,才知道原来她模样还算漂亮,就是举措让人心生不解。
余良不停挣脱道,“干嘛?”
姑娘继续拉住余良的衣袖不放。余良一脸莫名其妙地表情,我在一旁更是看傻了眼,完全不知所措。
余良不再挣扎,再一次道,“你这是要干嘛?”
姑娘说,“你要对我负责。”
余良慌乱了,我也惊讶不已。余良无辜道,“小姑娘,你可别乱说话。我都不认识你,负什么责啊?”
姑娘倔强道,“你干了什么,你自己知道。”
余良再一次表示莫名其妙。我小声凑到余良耳边说,“你干了什么,赶紧承认了。不然把事情搞大了不好。”
余良大声道,“一直都跟你在一起,我的那点破事你还不知道啊。你要知道,我是无辜的。”
我再一次心生不解,不过马上又感慨道这年头怪事就是多,遇见一两件也不为奇怪了。姑娘也是无辜的表情,我想她绝不会撒谎,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误解了。我再一次凑到余良耳边轻声说,“她肯定跟其他人有个什么事,误认为是你了。”
余良惊讶道,“啊!那怎么办?”
我依然小声道,“这事情传出去不好。依我看,还是先安顿好这姑娘,然后再把她送回家去。”
余良点点头,道,“也就只能是这样子了。”
正当我们要把姑娘安排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老板走过来了。老板远远朝我们道,“干嘛呢?偷懒呀。”
余良说,“老板,这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姑娘,非说要我负责。你看,能不能安排在酒店住一晚,明天我们就把他送回去。”
老板笑咪咪道,“哦,这样子啊。我懂我懂,那就安排个地方住一晚上吧。不过,你可要好好负责啊。”
余良赶紧道,“老板,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这姑娘没关系的。”
老板故作正经道,“小伙子,你别解释了。解释就是掩饰。大家都是男人嘛,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余良无奈道,“算了算了。还是安排房间吧。这事情要是传出去就不好了。”
余良付了房钱,我们将姑娘安排了房间里。在这件事情上,余良还算是大方,一声没坑就垫付了好几晚的房钱。不过,这也算是被逼无奈。
离开了那姑娘,余良就开始抱怨了。他说,“这姑娘也真是的,人都认不清楚,就乱跑出来。”
我说,“那也不能怪她。干那事情都是在晚上,熄灯瞎火的,谁看得清楚啊。”
余良说,“啊。这男的也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之后,我们了解到那姑娘来自陕西,跟沙潇是一个同乡。在莫名其妙之余,我们感伤起来。人不能一直怀念,就算是一直怀念也不能只是怀念一个人。少了新鲜感,就多了绝望,在怀念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我暗想。余良完全错乱了神经,糊涂之下问道,“你认识沙潇吗?”
姑娘睁大眼睛说,“你不就是沙潇吗?”
余良这才醒悟,我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想把事情弄清楚的念头更为强烈。余良说,“你找的是沙潇啊。”
姑娘说,“对啊。你不就沙潇吗?”
余良说,“你认错了,我不是沙潇。我是他的朋友,他失踪了。你不知道吗?”
姑娘说,“失踪了,去哪了?”
余良说,“失踪了,就是不知道他去哪了。”
姑娘说,“不可能。沙潇明明就是你。”说完姑娘从口袋里掏出相片,摆在余良眼前。我接过相片仔细看着,我第一反应就知道这人就是小时候的沙潇,再更仔细看时才发现着小时候的沙潇模样确实跟余良有些相像。
我说,“这相片确实是沙潇,也确实是跟余良挺像的。但他不是余良,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你是沙潇什么人?为什么现在才过来找他?”
姑娘说,“我是他小时候的邻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找他,就只突然有个念头想要找到他。确实,你跟他长得真的好像。你真的不是他?”
余良说,“真的不是。我也想找到他。”
事情到了这里也算是弄明白了个大概。在晚上我卧在床头不能入睡,无事烦扰的时候我总是容易困惑,换一种说法这叫作闲得慌。过几天就入伏了,想必更是燥热。夏天有三伏,有的年头一伏更比一伏严热,有的年头一伏更比一伏凉爽,不知今年会是如何,对于还未真正到来的夏天我在心里暗自猜测着。
对于白天遇见的事情,其中有许多不解依然让我在不停地思索。为什么会这么巧,那姑娘会找到我们?我想这个世界还真就是这样小,每一次相遇又都是命运的安排,如此之巧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我暗想,不知道那姑娘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她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余良就是沙潇。对于姑娘所说的责任,这让我依然不能理解。对于这个问题毫无头绪,完全不能让人有所思索,我的意识也在这样毫无头绪之中慢慢消失。
当我意识清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余良请了一天假,决定见姑娘送回她所在城市。为了不出意外,我也请了一天的假跟着余良一起去了。
余良开着车兴奋不已,想必他在等待能够出行的机会已经好久了。在车行驶了好久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去的方向不是火车站。我心生不解道,“你这是要去哪?不去火车站吗?”
余良直视着前方,边开着车边说道,“当然是去火车站了。不过,我们要绕开走。你也知道这个时候路况最拥挤了。”
我终于明白,道,“你就是想过过开车的瘾吧。你看,你这是耽误了姑娘回家。”
余良不懈道,“都已经往这个方向过来了,还不如一路到底吧。”
每一次坐车对于我来说都是值得享受的,但这一次我却紧张不已。我的注意力异常集中,我想如果是发生了意外我还可以在知道了情况之后再死。余良大概是猜到了我此时的感受,不停地强调说他的技术是如何如何地好,而我却对此半信半疑。余良话还没说完,因为没有来得及拐弯眼见得就要撞上了前面的护栏。坐在后排的姑娘见了尖叫不止,我大喊“刹车”。在距离护栏几公分处,余良把车停住。
我大骂道,“****的,你这是怎么开的车?”
余良依然在紧张着,没有说话。很久之后,余良还是没有反应过来,堵在后面的车越来越多。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按响了喇叭,余良依然没有反应。余良这时吓傻了,我想。我用力拍了拍余良的肩膀,余良浑身一阵颤抖这才反应过来。我说,“没事了,专心开车吧。你把别人的车都堵在后面了。”
余良重新点燃引擎,这一次车在余良掌控之下平稳了许多。人大多是在自信之下被惊吓,而在惊吓之后老实许多,我这样想道。
因为是绕道而行,路况还不算是拥挤,车平稳行驶一路畅通无阻。城市里不拥挤的地方一定繁华不了。这座城市也不例外,我们一路上遇见的都是破旧的楼房,就连最高的房子也不超过十米。更让我诧异的是,房子的门前大多挂着某某研究所的牌子。我不禁感叹搞科研的果真是穷。
在行驶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余良把车停到了停车道,一个人下车去环视着四周。不知出现了什么状况,我也跟着下车去,在心里暗想道这家伙肯定是迷路了。我问道,“怎么了?迷路了?”
余良指着遥望的路,道,“在这里转弯,往前笔直走就到火车站了。我只是中途停一下车,看看剩下的距离。我不想走得太快。”
我说,“那到火车站还需要多久?”
余良说,“在这里休息两三个小时再继续上路的话,刚好在黄昏的时候可以到。”
我说,“难道你要让姑娘在黄昏的时候上火车?”
余良说,“我都计划好了。要是在今天黄昏上火车,到达陕西的时间刚好是明天清晨。”
此处是个荒凉之地,除了看得见公路之外就只剩是泥土了,而我背后所面对的是一面矮矮的山坡。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原野,看着这般贫瘠突然感觉还是多一些修饰的好。如果这里不是穿插着公路的话,这里早已经遍地高楼大厦了,我想。
趁闲余时间里,余良蹲在一旁抽了根烟。他把烟抽到一半时,才想起应该要递给我一根。我透过车窗看见姑娘在已经在车里睡着,这才把烟接了过来。不知为何,我不太适应在女人的眼前抽烟,感觉就像是在警察面前犯罪一样。如果站在我面前的女人是个警察的话,我想我连抽烟的念头都不会有。我就是这样故作正经的一个人,值得庆幸的是更多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个人。
姑娘昨晚定是没有睡好,她肯定是在纠结一个问题,余良究竟是不是沙潇?如果是,为什么说不是?如果不是,那谁是?以此来看,姑娘在纠结的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无论结果是怎样在心底总会将问题转移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所有的答案在一开始都不对,一连串的思索都会是胡思乱想。但思绪无止境的时候,却是想要结果就越是深刻,最后就导致了失眠。当然,关于姑娘为什么会在此刻睡着,我所得到的结果也都只是猜想。或许,就是因为余良开车技术太差而导致了姑娘晕车罢了。
当我思绪结束的时候,烟头已经到了过滤嘴的地方。我一气将嘴里的烟雾吐出来,将烟头扔到旁边的水沟里。余良在旁边还在抽着烟,这是他抽的第三根烟。我知道他抽烟的习惯,一般时候很少抽烟,一旦第一根烟开始就不知会到第几根的时候停止,但这个过程一定会很漫长。
余良突然掐灭了烟,说,“你想不想尿尿?我有点儿想。”
我说,“哎呀,你真是麻烦。你自个去吧。”
正当余良要走时,我说,“哎呀,就怪你说这话,我也有点儿想了,还是一起去吧。”
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完全找不到能够遮挡的障碍物,我和余良无奈走了很远的地方才敢宽衣解带。当我们折回来时发现姑娘不再车里。我们四处寻找也不见个人影,想着在这么空旷的地方即使走得再远也能够见得到一个人影。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姑娘蒸发了,但如果这样解释就连自己也不敢相信。
无奈之下,我们只得是坐在车里等待姑娘回来。可惜,直至深夜都不见姑娘依然没能够回来。在万般担忧之下,我说,“都怪你,都怪你跑去尿尿。”
余良反驳道,“那你也有责任,要是你留下来的话,也不见得姑娘会消失。”
我深沉问道,“人失踪多久后可以报警?”
余良说,“现在就可以报警。如果要立案的话要等到四十八个小时以后。”
我说,“那你就报警吧。”
余良说,“我从未报过警。现在让我报警,感觉还蛮怕的。要是一紧张说不定还把我当成嫌疑犯了,你也知道我长得就像是嫌疑犯,这警还是你报吧。”
我在一番深思熟虑后,掏出手机拨打了110。很快,对方接通了电话。我想对方工作还真是勤,这么晚接电话还能够接得这么迅速。对方说道,“你好,这里某某分局。”
我支吾道,“我报案。我的朋友失踪了。”
对方问道,“请问你最后见他是在哪里?”
“在通往火车站的公路上。”我说。
对方又问道,“那他叫什么名字?”
我转头问身边的余良道,“她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知道。”余良摇头说。
于是我对着电话说,“我怎么知道。”
“你是在报假案啊!”对方很生气的语气道。
还没等我来得及解释,就听见电话被挂断的忙音。我第一次报警就这样以失败结束。顿时有一种受挫感涌在我的心头,我想我的人生真是太失败了。
在之后的夜里,我们继续在原地等待。依然不见姑娘的身影,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们原本焦急的心情也变得默然。而我也不敢再报警,要是在被怀疑报假案,那我肯定会被抓起来,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