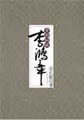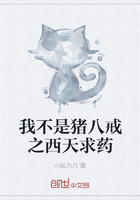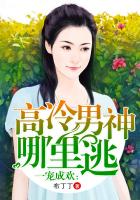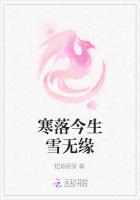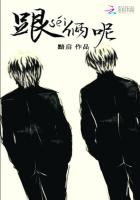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政府的唆使下,为了防止中央政府势力进人西藏,竟派兵阻止康印公路勘测队入藏,并以“佛示不准”为借口,于1942年1月13日要求国民政府“收回成命”。针对这一情况,蒋介石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多次召见西藏驻重庆代表罗桑札喜,请求藏方深明大义,不再阻止康印公路的修筑,并答应向西藏提供一定的财政补助;另一方面在西康和青海部署军队,企图以武力压迫西藏地方政府让步。他将原驻河西走廊的马步芳第八十二军主力韩起功部调回青海,又任命马步青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率所部骑五军移师西宁,增加对西藏的军事压力,并密电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康藏集结兵力。
在英印当局的支持下,西藏地方政府也采取了强硬态度。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政府成立了所谓“外交局”,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加恶化。次日,噶厦致函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称西藏摄政决定新设“对中国及他国办理外交人员之机关”,“今后汉藏间事无巨细,请径向该机关洽办”。
在数度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孔庆宗建议中央对西藏当局采取强硬态度。但重庆政府姑念汉藏两族的兄弟情分,将军事解决视为下策,仍积极争取政治解决。蒋介石于8月26日乘飞机巡视青藏边地区,认为解决藏事以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只要西藏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就足够了,于是决定“对藏暂时隐忍,以冀其自觉”。此时正值英美宣布放弃在华特权,蒋介石希望以此为契机,从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入手,一揽子解决西藏问题。但是,这种把希望寄托于第三力量自动退出的设想是行不通的。
1943年初,面对西藏局势的演变,中央政府认识到单靠政治手段尚不足以解决藏事,必须辅之以军事压力。1943年4月,西藏噶厦停止了汉藏驻运路线后,蒋介石便命令青海、西康和云南的军队向西藏边界开进。由于多种原因,云南和西康的军队实际上没有采取行动。但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在得到中央军事援助后——骑枪200支、轻机枪50挺、子弹数万发和一些军费,调集数千军队开赴青藏边界。
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蒋介石于5月12日在重庆召见了西藏驻京办事处主任阿旺坚赞等人。阿旺坚赞首先向蒋介石陈述了噶厦“请求制止军事行动之意”,蒋介石给予了严厉的回答,“调动军事,乃一方防止日寇勾结西藏,一方保护修筑中印路及驿运”。蒋介石还提出了藏遵照办理的五点要求:“协助修筑中印公路;协助办理驿运;驻藏办事处向藏洽办事件必与噶厦洽,不经外交局;中央人员入藏,凡持有蒙藏委员会护照者,即须照例支应乌拉;在印华侨必要时须经藏内撤。蒋介石指出:“如西藏能对此五事遵照办事,并愿对修路驿运负保护之责,中央军队当不前往,否则,中央只有自派军队完成之。”蒋进一步表示,“中央绝对新生西藏宗教,信任西藏政府,爱护西藏同胞。但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机飞藏轰炸”。
面对中央政府的军事压力,西藏地方当局确实慌了手脚,噶厦立即致函英国驻拉萨代表,“请求我们最大的盟友英国政府,通过印度政府给予我们尽可能的援助,以支持和维护我们的独立地位”。
英国人对于西藏噶厦的求助立即做出了多方面的反应。首先是在外交上施加压力。在5月20日于美国举行的太平洋作战会议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公然称西藏是“独立国家”,引起与会中国官员的愤慨。外交部长宋子文当即向邱吉尔严正指出,“西藏并非首相所谓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皆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
面对英国的外交干涉,国民政府表示出强硬态度。蒋介石指示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将薛穆送交的备忘录退回,表示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他指出:“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受任何国家干预。英国如为希望增进中英友谊,则勿可再干涉我西藏之事。如其不再提时,则我方亦可不提;如其再提此事,应请其勿遭干预我国内政之嫌,以保全中英友谊。”
面对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在西藏主权问题上的坚决的不妥协表态,英国政府检讨了自己对西藏的政策,7月7日,英国战时内阁通过了《有条件承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决议》。英国对于西藏仍然贼心不死,他们用宗主权代回避领土主权,声称“对中国宗主权的任何无条件承认,都会削弱英国政府保护西藏自治权的立场。”这样,英印当局向西藏提供军火便是很自然的了。同时,英国于1943年秋派遣军官组成军事训练组,赴江孜、拉萨等地,帮助藏军扩编军队,检修藏军所有的山炮,训练人员等。
英国政府虽然希望把汉人的影响从西藏排斥出去,但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无法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分离举动在军事或外交上予以公开声援与帮助。
广大西藏爱国人士坚决反对噶厦的分裂活动。一位西藏人告诉孔庆宗说,“西藏虽欲独立,但无资格能力,终必依一大国,中央对藏向有主属关系,不比外国’,不能归入外交局,中央如欲保藏,需及时设法加以处理,免依他邦;而藏人向由汉官管理,理由正大,尤其由中央严电坚持根本解决。”
西藏地方政府在此情况下,不得不找台阶下,他们声称“当前的麻烦并不在汉人政府本身……我们没有理由因猜忌而同汉人闹纠纷”,他们将责任推到了马步芳身上,认为“马步芳的行动必定有他重要的个人目的,这一目的可能对西藏和印度的利益皆有不利。”噶厦终于在蒋介石关于汉藏关系向西藏地方当局提出的五点指示基础上向中央做出了让步。
到1944年,国际形势发生更大变化,中国的国际声望日隆,蒋介石于是又重视起西藏问题来。蒋介石决定派自己信任的沈宗濂为新任驻藏办事处处长,以求西藏地方政府完全归顺中央。
沈宗濂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留学美国,为人精明干练,富有谋略。在郭泰祺任外交部长时,沈任其总务司长。1941年末,他调入侍从室第四组为秘书。此后他潜心研究各类问题,几年来为蒋出谋献策,颇多建树,深得蒋的赞赏。其中有一份意见书,就是进言蒋介石利用当前时机,加强与西藏的关系。这一意见正中蒋的下怀。此外,沈宗濂在外交部任内,曾随戴季陶特使出访过缅甸和印度,对印度情况相当熟悉。戴曾在蒋的面前夸赞沈宗濂思考周密,有胆有识,这也给蒋介石留下了印象。所以这次委派沈宗濂出使西藏也是有此缘故的。
沈那时正届壮年,身体已经发福,头发半秃,鼻上架一深度近视眼镜,弯腰躬背,行走时常持一根手杖,步履蹒跚而脸色庄重。蒋介石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大员出使西藏,一般不详内情的人自然颇觉不可理解。
沈宗濂上任前,蒋介石召见他作了一次详谈。蒋介石特别强调此行工作艰巨,使命重大,要沈宗濂在不引起英印当局疑虑的情况下,很好地完成四项任务:其一,宣扬中央的实力和统一中国的决心。其二,强调中央政府对藏民的一贯友善和尊重态度,指出只有加强同内地联系,与之结成一体,西藏才能有光明前途。其三,要求西藏方面同意中央派员勘察修筑康藏公路,迅速打开西藏与内地交通隔绝的局面。其四,加强双方间的友好合作。此外,蒋介石答应拨出一笔特别款项,以黄金、外币计算,作为沈宗濂此行的活动经费。沈在行前可作一预算计划,开列进藏需用各项开支,包括购置礼物,直接馈赠的费用等等。
沈宗濂曾在侍从室同仁为他饯行的酒席上坦率地说过:“我此行花钱如流水,不是不懂得节约,只是同落后又专制封闭的西藏政教上层人物打交道,不但要施之以威,还要诱之以利,在器量和魄力上都压过他们,否则是会被他们小看的。”
当时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盟国之一,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必然对印度独立运动以及整个形势产生直接的巨大影响。所以这时英印政府一改以往的冷漠态度,十分重视国民政府派沈宗濂驻拉萨之举。这次沈宗濂到达拉萨一个月后,英印方面驻锡金的行政官、英人古尔德爵士也带了大批礼品,追踪到拉萨作所谓“友好访问”。此行显然是为了探视沈宗濂到拉萨后的动作和西藏当局对沈的态度。
沈宗濂入藏后,通过论宴、赠礼、布施,广泛交往噶厦的主要官员、僧官、大小活佛,还约见了达赖。虽耗费巨大,但终于造成了沈宗濂入藏的浩大声势,颇令拉萨上层人物刮目相看,汉藏之间的感情也因此较前有了好转。
1945年8月14日,台电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拉萨举行了火炬游行,庆祝抗战胜利。次日,沈宗濂举办庆祝宴会,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噶伦、各大寺的堪布和活佛莫不前来参加,驻拉萨的英印、尼泊尔代表也率员赶来祝贺。在一片欢庆的气氛中,中央的声望再次大振。
英国一直以宗主权回避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沈宗濂在入藏前曾拜会过英印当局的外交部长卡罗,双方对此有过争执。最后卡罗爵士含蓄地说:“依我理解,当一个国家强大时,宗主权可以说是主权的同义词,并无区别,但是如果国家实力不逮、内部分裂,则这个主权自当别论了。”
志得意满的沈宗濂此时又想起那一番话,更深切地觉察到了其中滋味,因此,他决心把握时机,趁热打铁。他建议蒋介石一边消除西康割据,一边修筑康藏公路,就像当年修筑史迪威公路一样。外交上,则在联合国支持印度独立,同时与印度签订协定,要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恰恰在此时,蒋介石却无暇顾及西藏问题。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的发展颇出乎国民党的意料,蒋介石一面依靠美国调停国共内战,一面却又在作重打内战的准备。况且当时东北、新疆、内蒙问题也日趋突出。蒋介石嘱咐陈布雷电告沈宗濂,谓“奉委座指示,目前国内局势复杂,故西藏问题只能维持现状,不宜多事更张。吾兄才华卓著,年来在藏多有建树,弟所钦佩,唯按之现实,只能以无事为大事,以无功为大功。区区愚见,谅蒙明察。”沈宗濂是聪明人,接到这个复电后,知局势既已如此,事已断不可为。自此他也就无心恋栈,而亟谋脱身之计。当初一番雄心,只能付之东流了。
沈宗濂虽萌退志,然以他好强之个性,仍欲作最后建树,以陪衬他的引退,也好向南京政府有个交代。后来,在他的努力下,西藏派出代表于1946年春到达南京庆祝抗战胜利,准备参加“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