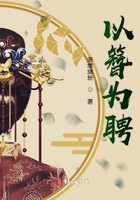我敛衽为礼,袅袅娜娜地说:“参见王妃。”我用了平生以来最可人的语气和声调,连我自己听了都觉得像是出谷黄莺。但我相信,这声音落在她的耳中,一定比半夜鬼啼还要可怕一些。
她有些踉跄地走到我面前,扶起我,熟视我的面颊。终于,她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听出她声音里带着“嘶嘶”地吸气声,如同不胜寒意。
我仍然在微笑:“我叫莲奴。”
她被这四个字打倒了,一连后退了几步,险些跌倒。乌就屠再次扶住她,皱眉道:“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她回头看看乌就屠,用一种尖利的语气问:“她来干什么?”
乌就屠微笑道:“她是我新收的妾室。”
“妾室?!”她不可置信地看看我,再看看乌就屠,然后她就像猛醒一样,双手掩面,转身飞奔而去。
乌就屠莫名其妙地看着她的背影,喃喃自语:“她这是怎么了?”
我便微笑着回答:“她一定是妒嫉了。”笑得时间太久,我觉得脸上的肌肉都开始麻木了,相信我此时的笑容一定是僵硬的,但我却仍然想笑下去。不可笑吗?许多年后,有人写过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我常想,这世间最可笑的人其实就是我自己。如此一想,便忍不住要笑,一笑起来便停不下来,笑到连眼泪都会流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笑也是如此悲哀的情怀。
次日,乌就屠才刚离府,她便出现在我面前。我想她一直在等待着乌就屠离开。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女子,她是我的母亲,却仍然年轻美丽,只像是比我大几岁而已。事实上,我知道如果单论容貌,我甚至还及不上她。不过,她毕竟是生过孩子的女人,而我还青春年少。对于男人来说,女子和蔬菜水果有些相似,新鲜有时比美味还要重要得多。
我们两人黯然相对,她眩然欲涕。她拉住我的手,我却不耐烦地推开。我使脸上的厌恶之色明显而浅薄。她怔怔地看着我的脸,低低地问:“莲奴,你可知道我是谁?”
我虚假地微笑,“你是我的母亲。”
她便忽然泪流满面,她似想要拥抱我,却被我脸上距人千里之外的神情镇住了,她道:“孩子,我一直都在思念你。”
我默默不语,我才不相信这种谎言。
她道:“你怎么会到乌孙来?你父亲呢?”
“死了。”
她怔了怔,又问,“外祖母呢?”
“也死了。”
“可怜的孩子。”她终于抱住了我。于是我再次闻到她身上那如莲般淡淡的幽香,十七年来,我一直怀念的味道。如今,她与我近在咫尺,所有的爱皆已远去,剩下的只有恨。
我任由她抱着,低低地道:“以后我叫你什么?王妃?姐姐?还是母亲?”
这个问题使她柔软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硬,她推开我,仔细地观察着我的脸。可是她能看见的只是一张冷漠的面颊。她沉思许久,才回答:“孩子,这么多年,我都不在你身边,现在我们竟又能相逢,这大概是上天的旨意。那就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吧!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
怎么?她已经不再介意母女共事一夫了吗?十七年前,就是因为撞破父亲与外祖母之间的奸情,她才离我而去,现在她终于被这残酷的现实打倒了吗?对了,乌孙也是不讲人伦的国度,同匈奴一样。听说在这个国家里,父亲死了,儿子就可以娶父亲的妻子,只除了自己的母亲以外。
那么我的母亲已经开始适应这种风俗,竟要与我共同生活。不过我不会让她如愿,其实我之所以要嫁给乌就屠,就是为了不让她如愿。我微笑道:“可是我不喜欢做小妾,如果你真的为我好,以后就由我来做正妻,你来做小妾吧!”
莲花色一怔,她大概万万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只是一怔,很快便点头同意。说起来这是多么可笑的协议,两个女子决定互换身份,丈夫尚且不知。
次日,我和莲花色一起出现在乌就屠的面前,他似正从宫中回来,眼中隐有忧虑。不过女人们可管不了那么许多,对于女人来说,府里的天下便是整个天下。
我将这件事向他诉说了一遍,他满面惊奇地看着我,问道:“这是谁的主意?”
“当然是我的。”我毫不隐讳。
他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望向莲花色问:“你呢?你也同意?”
她点头,低低地回答:“我同意。”
他的脸沉了下来,我以为他要发脾气,他却只是无力地挥挥手,“随便你们吧!我现在没有心情理你们的事情,随你们怎么闹。”
我大概选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当然在说以前我并不知道。
只不过这种名义上的调换对我影响不大,虽说府中的佣人都知道现在我是大老婆,她是小老婆,可是许多年来,他们早已经习惯于听从她的吩咐,有什么事情,总是先去问一下她的意见。我每天都在忙于改变他们的想法,然后再制造各种生活上的琐事来与她对抗。
这样的情形,乌就屠并非没有感觉。他有一次问我,“你就不能收敛一点吗?”
我却用从青提那里学来的媚人功夫,撒娇道:“我不想收敛啊!谁叫我那么爱你。我就是不喜欢她,要是你是我一个人该多好啊。”
我尽全力让他以为这只是醋海生波,而他缺少的也正是这种感觉。听下人们说,这些年来,无论他与哪个女子共眠,莲花色都不闻不问。我想,他或者是把我当成她的翻版,但我却比她多了许多让他赏心悦目的特性。
若是可以相安无事,也许以后的事情便不会发生。可是,我却想让她悲伤,她不悲伤,我便悲伤。她对于我所制造的各种麻烦并不介意,甚至让我有一种错觉,只要她每天能够看见我,她便很快乐。于是,我很不快乐。
我想像着总要将她从王府中赶出去,要让她变得更加凄惨,这样或许能够弥补这十七年来,她对我的亏欠。
若是我直接对她说我想赶她走,她会不会走呢?这个问题我只是想过一次,对于这样的方法我并不喜欢,有些污辱了我们之间斗争的激烈性,虽然这斗争很可能只是我想像出来的。但我很快学会权谋,学会通过斗争使人生显得更加丰富,或许这只是天性。
那一天,冯嫽前来拜访。她来的时候,乌就屠进了宫,我想她是故意趁着乌就屠不在专程来见莲花色。
她从花园中经过时,我正在花园里苦苦构思如何将莲花色赶出王府的方法,这真是一件费神的事情,如同构思一个无中生有的离奇故事。
她淡淡地看了我一眼,我心里便是一寒。她的目光十分犀利,似乎想要看穿我的心思。我对她微微一笑,我可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人啊!
她回以一笑,向着莲花色的房中行去。
我便也悄悄地走到她的房外偷听,内容无非是东拉西址。听了半晌,我总算明白了,冯嫽是想探听乌就屠对于目前形势的态度。已死的翁归靡是乌就屠的生父,但杀死他父亲的偏偏又是他的母亲。因而乌就屠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地位。
莲花色只是含笑听着,最后的回答是:我并不知道王爷心里所想。
其实我们都知道,乌就屠对于两方的斗争漠不关心,他所关心的是如何从这斗争中得到自己想要的。
冯嫽又绕着圈子问了半晌,莲花色一直含笑回答,但答案始终如一。冯嫽最后只得无奈地告辞了。
一件很平凡的事情,落在精心构陷的女子眼中,便不那么平凡了。
冯嫽出来的时候,我随着她走了几步。她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我。我笑笑,屏退左右,“我知你所图,我也一样。我可以助你们杀了暮云,但有一个条件,你们也需得助我除去莲花色。”
她默然不语,熟视我的脸,我与她对视,毫不躲闪。她问:“你是为了男人吗?”
我笑笑,“世间女人谁不为了自己的男人。你不是小妾,你不会明白此间的艰难。”
她冷哼,“我不相信。”
我默然无语。
她又道:“其实无论你是为了什么都与我无关,有没有你对我们都无关紧要。”
我淡然一笑:“我知道。我听说你武功高强,乌孙国里就没人是你的敌手。但是,这么多年,你应该比我清楚,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问题。真正能够使一个人最终获胜的不是你能击败几个敌人,而是阴谋诡计。我身为暮云的儿媳妇,你们却是她的敌人,她对你们早便有所提防,但她却不会提防我。”
她迟疑了一下,慢慢地说:“我怎么能相信你?你也说了,你是她的儿媳妇。”
我笑道:“确实难以令人相信。不过,你只要相信一点,那就是我要把莲花色从这个王府赶出去,我要让她无家可归,走投无路。”
最后一句话我是咬牙切齿地说出来的,那恨意,再怎样都无法假装。尘埃落定后,我孤独地飘荡在这世间,我才明白,那恨根本就是假的,所有的恨不过是源于我无所着落的爱。我恨她遗弃我,恨她不爱我,只因我是如此地爱着她。
这恨说服了冯嫽,她终于问:“你有什么计划?”
于是一个阴谋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