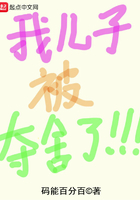紫瞳便不再说,只是随着她找了一间客栈落脚。当天夜里,紫瞳听见隔壁的安心离开房间的声音,他想她必是忍不住回王宫去探视亲人。
只是当他推窗时,却只听见安心在院中徘徊的脚步声。
他悄无声息地聆听着,她来来去去走了不知多少圈,到底不曾离开客栈。直到东方破白,他才关上窗户。他想安心真是一个古怪的女子,有时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都可以送掉性命,有时连自己亲人的丧礼都置之不理。这女子有些可怕,或者是可怜,不过他也说不上他为何会觉得可怕和可怜,这本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特性。
无论如何安心至少应该哭上几声,表达一下思念之情吧!安心始终不哭。
后来,许久以后,他方才知道。安心是不哭的。
无论是怎样令人哀伤的事情,她都不哭。
他并不喜欢这种个性,一个女子便应该欢喜的时候笑,悲伤的时候哭。不流泪本应是男人的事情,若是女子也如此了,又与男子有什么区别?
这使他对安心又多了一种新的感悟。他觉得这个女子古怪得超出了他的想像,他不愿与她更加接近。好吧!到了天空之城就让这一切结束吧!他有些后悔当初答应带她去天空之城,也许他应该再次食言。只不过他有些懒了,都已经走这么远了,就继续走下去吧!
后来进入大汉的地界,看见巍峨的皇宫和巨大的城市,这些皆与西域不同。饮食惭惭改变了,物饰也不再相同。紫瞳不明白的是,他与安心都不必吃饭度日,可是安心却坚持每天两餐,从不耽误。安心也如同普通的女子一样,在市集之中选购衣服首饰,使自己不至于显得过于古怪。
后来,他终于忍不住诘问安心:“为何一定要吃饭,这些食物让我觉得恶心。”
安心默然半晌才回答:“因为吃饭的是人类,不吃饭的是妖。”
他呆了呆,冷笑道:“再吃多少饭,是妖的还是妖的。你以为你吃了这些食物就能变成人吗?”
安心不与他争论,仍然坚持进食无误。过了几日,本来决定不吃饭的紫瞳竟也终于屈服于她的执着与毅力,拿起了筷子。
他经常觉得安心讨厌,一个如此固执的女子是令人讨厌的。而且她的讨厌不止在于她的固执,还在于她似乎有影响别人的力量。她可以完全无视别人的存在,只是按照自己的想像去执着于一件事情,结果就是身边的人不得不屈从于她。
他讨厌这样的女子,因之想到暮云。
说起来暮云与安心也并非全无相似之处,至少她们都是善于影响别人的人。只是暮云与安心的不同在于,暮云会利用一些女子的手腕如同撒娇吵闹来达到目的。安心却只是骄傲地无视别人,骄傲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这种骄傲深深地刺痛了他。
事实上,这骄傲也只是他想像出来的。他并不知只是因他过于重视自己,才会比其他的人都更加敏感。
终于走到东海之边时,已经不知过了多少时日了。
向海边的渔人们打听海中的小岛,有渔人说曾经在海中见到倏然来去的仙人。只是仙人的行动很快,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传闻零零总总,没有要领。
紫瞳皆不置可否,若要找到城便要先找到离情岛,只是他离开天空之城的时间过久,大海中的方位又与陆地不同,完全没有参照的东西。于是便赁舟出海,四处寻找,只是在大海之中找一个小岛却如同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
幸而两人的生命是无穷的,用这无穷的生命寻遍东海,总有一日能找到离情岛。
后来有一日,海上风波大作。
在海上的时日多了,多遇风波,刚开始时,两人都不在意,直到风浪越来越大,才猛然惊觉,原来这是前所未遇的大风浪。
船夫们惊慌失措,抛去船桨抱做一团。安心匆匆跑上船头,只见海中的风浪有几丈之高,这只船在惊涛骇浪之中被抛来抛去,若非船造得结实,只怕早已经成了碎片。
她连忙找到船夫首领,问他如何是好。
船夫回答:“小姐,这样的风浪几百年都难遇。是海神动怒了,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安心蹙眉,她自己不怕,相信就算是船沉了,她和紫瞳也不会有大碍,只是在这么大的风浪之下,就算她想救这些船夫,只怕也办不到。
她游目四顾,忽然看见不远的地方,似乎在风浪之中有一个小小的缺口。她连忙自己掌舵,将船向着缺口的方向尽力划过去。
紫瞳安坐船头,不被风浪所动。他知道安心在划船,到了海上以后,两人之间的交谈便更加少了。其实也没什么好谈的,每天不过是蓝天、大海、白云和海里的鱼虾,而紫瞳又看不见。有许多时候,两人似乎都忘记了对方的存在。
那缺口的地方渐渐现出小岛的影子。无论周围风浪如何的大,小岛附近的海水却平整如镜。最奇异的是,安心分明在小岛的上空看见飞龙盘旋。
她大喜,指着那岛叫道:“是离情岛吧!”
紫瞳没有回答,又是那熟悉的感觉,许久许久以来,族人都是被严禁外出的。孩子们总是能想出办法溜出去,只要不被人发现。
船到了岛外平整的水域,却再也没有办法靠近小岛。无论如何划水,船都只能在小岛外的水域中盘旋。
“那是结界。”紫瞳淡淡地说。
八部众的故地都被结界保护着,以免外人侵入。这岛看似全无戒备,其实是固若金汤的。一轮圆月挂在正空,又是十五的夜晚。
月亮正正地照在海面上,将小岛的影子投射在水里。岛上之城清晰可见,近在眼前,偏偏又远如天涯。
“那是无欲城,那迦族住的地方。”
安心一怔,本以为岛上之城便是天空之城,却又不是。那为何要到这里来?
她回头看看紫瞳,紫瞳神情莫测高深。她忽然发现水中的影子过于明晰,如同另一座城市。她俯首看着水中的城,海面太清澈,怎么看都觉得水中的城是真实存在的。
她又抬头看岛上的城,亭台楼阁,花草树木,历历可见,似乎还能隐隐看见城中人们的身影。
许多年后,有人传说东海中有三座仙山,山上住有神仙,传闻来自于离去的渔夫。倒影中的城一草一木都与岛上的城毫无二致,唯独水中没有人影。
安心揉了揉眼睛,再次抬起头。不错,城中确实时而能见到飘然而过的身影,但水中又确实没有那些人的倒影。
她心里一动,“天空之城是在水中吗?”
“你很聪明,很快便猜到此中真相。许多年来,人们都以为天空之城是在天外,谁也不曾想到,天空之城居然隐藏在那迦城下的水中。连那迦们都不知道。”
“为什么?这是显而易见的。”
“有的时候离真相越近,反而越是迷茫。”安心一怔,她还是第一次听见紫瞳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有些不同寻常。
紫瞳忽然拉住她的手,跳入水中。
城在水的最深处,越往下沉,便越是清晰可见。但越是靠近,安心却越觉得异样。岛上的城偶尔还能看见一两个人影闪过,水中的城却死气沉沉,全无活物存在的迹象。城外有奇异的空气包围,这也是结界吗?据说八部众掌握了地水火风的力量,可以轻易操纵结界,这是半神所特有的本领,除了半神外,只有佛和天人能够控制结界之力。
迦楼罗城并非是在离情岛的正下方,离情岛也不像是普通的岛屿一直与海底相连。在离情岛的下面,有一条与众不同的水柱,周围的海水到了水柱边都会绕道而行,离情岛就像是水柱上盛开着的一朵莲花。
那是真龙之水。这念头是忽然产生的,完全没有来由。
注意月影的移动,当月影迁移之时,结界会出现极短暂的间隙。这念头也不知源于何方,就这样生生地在脑海中形成了。
只要动作足够快,就可以在结界再次形成以前进入天空之城。拉着她的紫瞳忽然向前冲去,安心心里一紧,眼前一花,定晴看时,两人已经进入结界之中。到了结界之内,就不再有水,如同站在陆地之上。
头顶上是荡漾着的水波,一轮月影便悬挂在头上。
紫瞳淡然一笑:“你已经到了天空之城。又能怎样呢?族人都死光了吧?我走的时候只剩下不多的一些人了。拯救他们?你根本不可能拯救任何人。因为我们这个族是注定要毁灭的,早便注定了。”
前尘
记忆中的乌孙乏善可陈,不过是一个很大的都城罢了。
唯一留在岁月经纬里的便是青提夫人那张略显苍白的面颊。我最初对她的印象并不好,她经营一家妓院,我住在妓院对面的客栈中。
每天早上走出客栈,都能看见对面楼头青提夫人对镜梳妆的侧面。她是个美人,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动作也文雅,对镜簪花的手必然会小指、无名指、中指微翘,这三根手指翘起来的高度不同,形成一条柔和的曲线。
插上那枝花后,她便会转过头对着我微微一笑,然后高声道:“姑娘,以你的姿色一定会红遍全城,来吧!”
她的眼睛下面永远都因纵欲过度浮起淡淡黑色,这黑色并没有影响她的容貌,反而带着奇异的蛊惑。我相信许多男人是因她走进妓院,而她并不接客,也不是完全不接,心情好时,也会与男人共度良宵。
一个喧宾夺主的老鸨,在乌孙都城并不太繁华的街道上,开了一家生意不好不坏的妓院。一切都看似平平无奇,只是看似。
我每天早上出门,四处游荡,偶尔问路人是否见过相貌与我神似的女子。无人见过。
寻找是能迅速令人感觉厌倦的工作,当问了十个人得到相同的答案后,便懒得再去问第十一个了。
此时需要休整一下心情,若无其事地做些旁的事情,等到忘记了挫败感可以再次鼓起勇气向人询问同样的问题,然后得到同样的答案。
虽然如此,我却固执地相信母亲一定在这座城中。
这坚信全无来由,只是因我道听途说地相信了一个远行之人的话,而他当时所说的无非是:似乎有那么一个女人。
或者除此之外,还有说不清的预感。
我预感到在这个东方的城市中,有什么东西正在等待着我。是什么东西我一时也说不清楚,有可能是我的母亲,也有可能是其它的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或者只是命运。
不久后,我听说神僧目犍连在城外的精舍中传法。我记得这个僧人,一岁那一年,母亲请求他为我祈福,却被他拒绝,回家之时,母亲便撞破了父亲与外祖母之间的奸情。
他也到乌孙来了吗?冥冥之中,有缘之人总能相逢,无论是否有意。
我于次日一早随着大批信众去往精舍听经。十几年的光阴,他一点没有改变,仍然如同十几年前,白衣飘飘,一尘不沾。面貌也不曾衰老,当然也不可能年轻,就是一点也没改变罢了。
我坐在信徒之中,低眉顺目。不知为何,我不敢抬首,不敢与他对视,刻意避开他的目光。因我有奇异的直觉,只要让他看到我一眼,便能认出我是谁,且能看破我深藏不露的居心。
幸好到场的人实在太多,我混迹人群之中,头巾遮住了半张脸。他终于没有看见我。
不久后,阍者传道:“王妃驾!”
人们纷纷起身,中间让开一条道路。
一个女子,身着华服,微微含笑,穿过人群。
我看见她的脸,于是目眩神迷,心胆皆丧。比莲花还纯净的笑容,与我七分相似的容貌,我不会看错,这世上只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我的母亲,她竟然已经成了王妃。
我怒不可遏,勉强压制。她怎可这样?她怎可在我们全家都受苦受难之时过着尊贵繁华的生活?她本该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才对,哪怕是沦落成了妓女也比成为王妃要强得多。
我觉得我被出卖了,被我亲生母亲所出卖。只因为她不曾在离开我后,生活在痛苦之中,只因为我始终认为她是使我、父亲和外祖母挣扎于痛苦之中的原凶。
但,她华服丽容,一看便知,过去十几年过得尊宠奢侈。她抛去亲生女儿,完全不曾感觉到内心的痛楚吗?
我听见有人的牙齿被咬得“格格”做响,几乎碎裂,后来我发现这声音出自我的口中。于是我止住神经质的咬牙行为,却又发现我的双拳握得太紧,以至于指甲刺入了肉中,鲜血正在慢慢地渗出来。
我的仇恨在看见她的瞬间无可抵制地暴发。我曾设想过无数次再见到她的场景和我应该出现的心情,但那无数次的场景及心情都没出现。因为在这无数次的设想中,从来不曾有一次把她想像成一个王妃。
而我曾以为会出现的孺子之情全部化成了最简单直接的怨恨。
她怎么可以这样出卖我?
我从来不曾觉得她出卖了父亲。父亲如何,与我无关。我所关心的只有我自己。
她虔诚顶礼,坐在离僧人最近之处。
她坐下后,身后的人们方才坐下。于是我也只好坐下。我仍然用头巾蒙着半张脸,露出来的眼睛一眨不眨地落在她的背影上。
不知她是否感觉到了我的注视,我看见她回首过三四次,只不过身后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只要她一回首,我便立刻垂下头,由始至终,她都没有看见我。
我是一个很好的伪装者,是在那一天,我才忽然发现了这个特性。
讲经结束后,我随着大队人群离开精舍。但我并没有离开,而是躲在无人可见的阴暗角落。
我看见众奴仆拥着我的母亲走出来,她身后不远是送行的目犍连。目犍连在精舍门口止住了脚步,目送我母亲的车骑离开。然后他的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我藏身之处,我不知他是否看见了我。他只是扫视了一眼,便转身走回精舍。我忽然觉得双膝发软,心头酸楚。
其实我想大声痛哭,只是我不是喜欢哭泣的人。这许多年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变故,我都不曾哭泣。
在成长的过程中,父亲染上酗酒的恶习。他每逢喝醉就会用皮鞭抽打我,一边抽一边痛骂,即便如此,我也从来不曾哭泣。
父亲和外祖母死时,我亦不曾哭泣。我曾以为我不会哭。原来并非如此。
原来我一直不哭,是因为没有感觉到真正的悲伤。因父亲和外祖母都是我漠不关心的人,我唯一关心的便是母亲。
如今,我看见她,她是王爷的妻子。
我坐在地上,坐在竹林中,在泪水即将涌出之时,一双丝履停在我的面前。
我抬头,泪眼朦胧中看见青提苍白的脸。也许是因竹林中的光阴昏暗,她的脸色显得比平时还要苍白。
她在我对面坐下来,不顾这样会弄脏自己身上昂贵的丝裙。
她说:你哭什么?
我说:我母亲,她做了别人的妻子。
她说:那王妃就是你母亲吧?你们长得可真像。
我说:我一直以为她生活得很艰难。
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然后微微一笑:你真是一个自私的女孩。
这是她对我的评价,也是我对自己的评价。
为了转移话题,我问她:你为何会在这里?是妓女祈求内心的平静吗?精舍与妓院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在此处只有圣洁,而在妓院中却只有污秽。
她淡然一笑:妓女和僧人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喜欢这种含义不明的话,它让我感觉到我无法明了说话人的心思。也许他们隐有所指,也许他们只是胡言乱语。
后来她拉着我起身,离开精舍。
在回去的路上,她说:你相信吗?那个和尚,目犍连,他是我的儿子。
我惊愕地望向她。
她哑然失笑:你真的相信吗?多么荒诞的事情啊!
笑有时候是一种掩饰。只是我清楚地记得我一岁的时候,目犍连就是二十多岁的样子,现在我十八岁了,他还是二十多岁的样子。他到底有多少岁,无人知晓,因为他是传说中的阿罗汉,已经参悟大道之人。
如果青提夫人是他的母亲,那么青提夫人又是什么人呢?
只要这样一想,就能轻易拆穿青提夫人的谎言,无论如何,一个妓女也不可能参悟大道。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我忍不住仔细观察着她的脸。苍白的脸,一如既往的苍白。除非,她是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