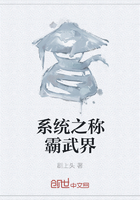福星躺身甲板上,闻悉宿婉情和萧影的一番对话,大梦方醒,原来携了惊鸿簪逃跑的不是如尘,却是自己的女儿。而自己还大费周章,为了抢夺簪儿,险些丧命在李府。到头来,自己的老命倒是捡了回来,却一掌打死了宝贝女儿。
一时间悲痛欲绝,老泪纵横,还未听完,竟致撕心裂肺地失声恸哭:“天啊,我竟然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老天啊,活生生一个娃儿,是你不长眼睛,将她送到我的掌下……女儿呀,你干么性命不要,也要护着萧影这厮,你怎会这般傻啊!你明明喜欢他,为什么又不说出来,憋在心里,这又是何苦……”
又听宿婉情最后叫了这声“爹”,一颗心似是被人撕裂一般,奇痛锥心,一声狂啸,竟至冲开了被封的穴道,身子弹射而起,起掌拍向萧影。
萧影正自伤心之际,未及接过宿婉情递来的惊鸿簪,右手环抱她香颈,左手握住她递簪过来的手,陡见福星疯也似地扑来,将头一矮,急忙避让。
不意福星气急败坏,这一掌来势直是飞沙走石,宿婉情恰也在这时断气。她手一软,惊鸿簪自手中滑落下来,福星一掌正好拍到,簪儿受掌风一带,倏地飞出,穿过李瑶的头顶,波地一声落入湖水中。
李瑶吓得“啊”的一声惊叫,船上人人也是大惊失色,定格在那里,呆若木鸡,半晌作声不得,竟致不敢相信,人间至宝就这般打了水票,此前的性命相搏,竟然成为大梦一场。
萧影脸上变色之余,待要飞入湖中打捞,却哪里来得及?簪儿一入水中,自身份量不轻,瞬间便沉下湖底。
福星大悲大惊之余,浑身骨骼似散了架一般,再无半点力气,一交跌坐甲板上,捶胸大哭大骂起来。
萧影抱着宿婉情的尸身,悲痛之余,心下一片茫然,喃喃自语道:“为什么,为什么你骗了我,又不把簪儿交给你爹爹,难道你也想要这稀世宝藏?不,你的心地这般纯真善良,绝不会这样子做。但是……但是你费尽心思,妆扮成我师父,一路自大西北跟我来到江南,难道是闹着玩儿么?不……这一切究竟为何,究竟为何……”
猛然间他想到一事来,不由心下盛怒,便欲抛开她的尸身,却又不忍。
那日大漠自己垂死之际被人救去,在洞中醒来之时,宿婉情便已容易成师父的模样儿,陪伴在侧,这一切都是事先预谋好的。
但想宿婉情一颗心单纯如雪,这样的阴谋诡计绝不可能是她的意思。逃出山洞后,外面有大批辽兵把守,自己和她仍能轻而易举脱身,当时自己便心下起疑,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师父身上去。
后来耶律楚南等人自后追来,明明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追上,却偏生放了师父和自己脱走。这等阴谋当真高明之至,耶律楚南一向诡计多端,定然是他设下的陷阱无疑。
萧影又想,婉情自太原失踪后,数月来一无消息,难道她受了耶律楚南的骗?抑或她脱逃后,遇上耶律楚南,与他日久生情,心甘情愿做他的棋子,不顾性命帮他夺取惊鸿簪?然而瞧她不顾性命替自己挡去福星一掌,却是真真实实,绝无半点假意,显然对自己情深意重。
思来想去,竟是半点摸不着头脑。他心下黯然,这其中的是非原委,是那样的高深莫测,婉情死了,这一切也将成为永远的秘密,随她一起湮没尘世!
想到这儿,不由仰天怆然一声悲啸。
福星哭丧得一阵,黑黑的胡须上面,一张老脸板起,样子十分吓人。
他飞身过去解开另外三星的穴道,寿禧二星哭天喊地跑将过来,挨在宿婉情的尸身旁,泪人一般,哭得甚是伤心。
萧影见二星似孩童一般,心中的喜怒哀乐率性而发,全没大人架子,心想世人倘若都像他们一样,活得单纯坦诚一些,少一些尔虞我诈,便可少一些头破血流。
正自想着,耳听福星大声喝骂道:“萧影,婉情是你害死的,我要你为她陪葬!”
寿星一听,哭声立止,见大哥怒容满面地向萧影扑过来,连忙阻止道:“杀他不得,杀他不得,杀了他婉情可要伤心流泪的……”
福星一愕,正要喝斥他几句,那禧星却自收泪道:“放屁放屁,情儿都死了,怎还会伤心流泪?”
寿星道:“正所谓……正所谓那个……那个冤有头,债有主,情儿分明给大哥一掌打死的,怎可怪在他人头上?”
福星闻听之下,伸双手在眼前看了又看,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似是这双手染满了女儿的鲜血,面色恍惚,不由全身颤抖,几欲摔跌。
禧星全没注意大哥已然伤痛欲绝,仍自道:“错了错了,情儿分明便是萧影害死的!”
寿星道:“你睁着眼睛说瞎话来着,适才大哥这么一掌,打在情儿的胸前,你又不是没看到!”他边说边照福星拍向宿婉情的一掌比划起来。
禧星道:“我说你笨不是,这世上的事儿,岂可全用眼睛瞧,得用脑袋瓜子想想,懂么?”
寿星也不发怒,说道:“俗话说得好,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脑袋瓜子想出来的,全是稀里糊涂的东西,更是做不得数!”
禧星道:“你想啊,当初若萧影不来归鹤山庄,你道会怎样?”
寿星道:“定然是去了别的山庄!”
禧星道:“说你笨,果真笨得可以。他不来归鹤山庄,那咱们闺女情儿便不会与他识得。”
寿星道:“你这不是废话么,两人见不得面,眼睛瞧不见对方,自然识不得。”
禧星道:“这话倒不假,既是两个不识对方,那便怎地?”
寿星道:“那情儿便嫁不出去了呗!”
禧星道:“呸,咱情儿美得花儿似的,还愁嫁人?两人既是识不得,情儿便不会喜欢上萧影这小子!”
寿星道:“识得也不一定喜欢。”
禧星不理寿星,继续道:“既是不会喜欢上这小子,那便不会为他整日价失魂落魄,茶饭不思;既是情儿好端端的,咱们这趟出门就不会带上她;既是不带她出来,那便……”
说到这儿,又号啕大哭起来,寿星亦跟着哭得不可开交,反把福星晾在一旁。
眼下他泪也干枯了,眼见两个兄弟哭得这般伤心,倒是不知该上前相劝呢,还是再哭一场。
哭着哭着,寿星突然止歇道:“总之,萧影不该杀!”
禧星道:“杀也不好,不杀也不好,这可要糟!”
这时小船已然随风飘荡至岸边,福星怒声道:“你们两个又傻又呆的家伙,说了这许多屁话,该闭嘴了!”
抢身而上,一把将宿婉情的尸身抱在怀中,飞身上岸,嘴里厉声道:“萧影小子,念你为情儿掉了几滴眼泪的份上,今日老夫暂且饶你不杀,往后若是遇上,定不相饶……”说着消失在树阴之后。
禄星横了一眼萧影,与寿禧二星一齐连声大叫:“大哥,等等我们……”追了上去,片刻间声影全无。
萧影舍不下宿婉情,举步要追,李瑶一把拉住他,柔声劝道:“让她去吧,福星是她父亲,定然会好生安葬于她。”
萧影心想,她说的也对,自己虽与宿婉情极为投缘,早将她当成知己看待,不过再怎么亲近,终归比不了父女情深。心下对宿婉情此前的一番举动,仍自耿耿于心,不觉又叹了口气。
李瑶柔声又道:“你还在怪她易容偷簪儿一事么?”
萧影一愕,心道:“我的心事,她一猜就中,这倒奇了!”只是这个“偷”字大为刺耳,心下黯然,默不作声。
李瑶道:“原来女儿家的心事,你一点都不明白。宿姑娘真了不起,为了自己所爱之人,不惜舍却自己的性命!”
萧影疑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李瑶脸一红,说道:“人家喜欢你,你却不知。哼,我只道你是一介翩翩风流少侠,原来却不懂风情!”
萧影知她有心戏耍自己,本待说几句反唇相讥的话,心下难过,便也无心与她多费唇舌。心想她说宿婉情喜欢自己的话,福禄寿禧四星隐约也说过,听来倒是不假,只是她扮成师父的缘由,日后若有机缘,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想到这儿,见天色大明,提步上岸。
李瑶道:“哎,你去哪儿?你身上的伤……”
萧影经她提醒,适才伤心难过,倒忘了此前中过仁义二怪两掌,但觉五内疼痛入心,浑身轻飘飘地,头脑昏晕,几欲倒地。
随即他运起真气守住心脉,淡淡地道:“不碍事。只是那惊鸿簪,乃是你祖上之物,本欲亲手交还与你,却落入湖中,唉!”
李瑶道:“小小一枚惊鸿簪,又打什么紧。你不远千里以死护簪,已然尽心竭力,那也怪不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