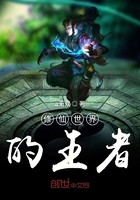据我所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加里的生活相对平静。那时候,他正服用各式各样的处方药,来应对一些开始潜入他生活的感染。他仍然在实验室里做全职工作,尽管他每天都需要在自己放置在桌下的蛋箱和泡沫橡胶床垫上面小睡,当他告知我关于自己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时,我一直不愿相信,恐怕他一定认为我是反应迟钝。这并非是仿佛我从未在别人那里听到过同样的话。一定是来自于我拒绝接受艾滋病是不可治愈的现实,以及拒绝接受我儿子必须忍受随之而来的痛苦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9月份,可怕的流感嗜血杆菌控制了加里,而且再也不肯放手了。他脆弱的免疫系统无法彻底将它打败。即使在他从流感中恢复过来可以回去工作之后,他仍然持续不停地咳嗽。有一次,当下班开车回家经过海湾大桥时,他开始剧烈地咳嗽,并由此引起呕吐。他根本没有办法把车停在路边。他感到难受极了,然而当他到家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必须得先清理车子,然后才能走进屋里倒在床上。
他继续在实验室工作,然而他晚上到家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没法做晚饭了。于是他通过爱心计划(ProjectOpenHand)1参加了一个上门送餐项目,该项目为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其他重病患者以及老年人提供营养服务。好在,他能够支付这项服务,尽管他并没有被期望这样做。加里拒绝了以残疾身份退休的可能性,他决心继续战斗到底。
和表亲们在圣荷西市共度感恩节对于加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是一场他不会错过的节日聚会。于是,在一个愿意开车载他去那儿的朋友的帮助下,他设法出席——然而他病得太重,以致于无法参加。睡在楼上他的表姐南希的床上,他一直躺在那儿直到南希上楼取点东西。幸亏她注意到了他,因为他已经虚弱得无法大声叫唤,更别说走到楼下去表达他的困难处境。他显然明白自己已经病到需要住院治疗,那是自从他11年前确诊后的第一次。事实上,那也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一向都是个健康的孩子,在学校里从没缺过一天课。现在他的体温达到了华氏104.6度2。
我的哥哥埃利奥特那个假期和他的妻子子女都在那儿,他开车把加里送到医院,还有一些家人一起去帮忙。他们通知最好尽快赶到加州去。星期六,午夜以后我赶到了我侄女的家,非常迫切地想看到加里,但我必须要等到第二天。
等我到医院的时候,情况正在好转,加里精神状态很不错,那之后的一周或是10天左右都是如此。他感觉好多了,显然是医院里他的主治医生所制定的某种神奇疗法在起作用。当轮到我自己儿子的时候,他的病痛,以及他得到的关照,而我却不在他身边,同样的事情我为很多其他人都做过,这些都令我感到痛苦难当。一方面是因为其他人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另一方面是因为加里一直坚持不想让我产生任何焦虑。或许也是因为我完全不想承认我的儿子会得这种绝症——或者更糟,他已接近生命的尽头。我恳求护士告诉我任何我可以亲自为儿子做的事。我提出做肺移植,她说那不可能。我告诉她:“如果可以实现的话,我愿意给他一个生命移植。”
她很同情,不过当然,又一次拒绝了。
呆在圣荷西市欧卡诺医院的日子里,加里给比尔·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所有给予艾滋病患者的研究与治疗的感激之情。他不允许我阅读那封信,因此我说不清楚加里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唯一我肯定的是他非常感激他所受到的治疗,而且也非常高兴自己还活着。
后来加里写给我:“……总而言之,住院治疗并不是一次糟糕的经历。事实上,那是一次非常感人的经历,因为我明白成千上万的人们尽心尽力,他们所有人的努力日日夜夜都流入了我的臂膀。而且,我也处于一种异常亢奋的精神状态之中,每个人都听我讲话,提出有趣的问题,而没有把他们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我身上。”
接下来的星期三,他真的蹦蹦跳跳地出了医院,开他自己的车回到了旧金山,车之前留在圣荷西市供我使用。唯一的问题是,就在我抵达的那天,消音器掉落在了医院的停车场上。我试图在在加里出院之前到圣荷西市的一家经销商那儿把它换好,然而他们没有帮我达成心愿。那是我第一次行驶在加州的高速公路上,而当我们从路面上咆哮而过时,我很怕会被高速公路巡警拦下来。然而那恐惧在我们身后消退了,它很快就被在前方旧金山等待我们的事情所替代了。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加里每天都要接受8个小时的静脉输液,在那期间他掉了15磅的体重,也几乎失去了在圣荷西市所获得的所有力量。他试着去吃我为他准备的饭菜,但静脉治疗的伤害似乎超过了它的益处,它引起了持续的虚弱和恶心。然而,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要从自己所遭遇的明显是卡氏肺孢子虫肺炎的第一轮袭击中恢复过来。他的男护士保罗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年轻小伙,他每天都骑摩托车过来,自从他进入我们生活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鼓励加里。他的任务是每天进行戊烷脒和头孢曲松钠的静脉注射。
加里把保罗称作“摩托车上的护士”。我更喜欢“骑行者护士”。我以为他是个同性恋,但他并不是。他向我表达了自己担忧,对于同性恋群体中有关于艾滋病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伴随在这一领域内的偏执。他和许多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男人一起工作,也听这些人说过他们被家庭抛弃以及失去工作和朋友的故事,从整体上讲,他们失去了健康和人身自由。待到他为期两周的工作结束时,加里给了他一笔丰厚的礼金作为酬谢。在最后一次离开加里的病房之前,保罗弯下身子在加里的耳边低语着真诚而慈悲的再见。
12月17日是鲁米3的祭日,他是苏菲主义4的创始人,在西雅图将举行一场盛大的集会。鲁米的追随者们将它称之为“新婚之夜”——那意味着,鲁米“嫁给了永恒的生命”。加里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去参加赛玛仪式的机票,他打算参与这具有转折意义的典礼。
随着他一天比一天虚弱,我不敢去问他,他觉得自己是否还能走这一趟,更别说去参与活动了。但在12月16日,他让我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取消我们的预订,因为他知道自己去不了了。他已经打了场硬仗,但还没有赢得战争。然而,他充满感激地接受自己正在好转的事实,并且计划着等过完了新年假期就回去工作。当身体的虚弱让步于仅存的尊严时,他硬撑着参加了加州海湾对面费尔法克斯的跨年庆祝仪式,但没能够完成跨年的部分。正如他在1995年1月2日写道的那样:“我的力量连同我能够完整地参加每年苏菲祭日庆祝仪式(赛玛)的能力在11月就都已经消失了。我本想在仪式最短的一个环节(萨拉姆)里露面,然而还是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力气。一个急转过后,我还是发现自己摔在了地上。我走到族长那里,鞠了一躬,然后转身回到内场我自己的地方。然而,我很快就发现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位置,于是,凭借着15年芭蕾训练的优雅,我右转退出了场外。我不得不在接下来的两个萨拉姆仪式中都坐在外面,这在仪式上是很失礼的。”
然而,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许多时候,当我想起鲁米,这位13世纪苦修僧人的创始者,我都会有一种快乐而振奋的感觉,那与以物质为基础的世俗快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考虑到他那虚弱而疲惫的身体,他参加赛玛的坚持不懈以及那甚至更为强烈的,他想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的决心,这些都令我感到无比骄傲而又难以抑制地悲伤。不过,他也明白自己提前离开场地的行为,当时他的同伴们都参加了全部的4场萨拉姆,整整45分钟的时间,如果与他在中场仪式最重要的环节晕倒相比也算不了什么。
第二天,星期六,12月12日,爱心计划打来电话询问加里那天是否会在家,他们想要送一个圣诞节礼包给他。当然,那再好不好。我们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我看着加里一个个打开那10个或12个包裹。我们都受宠若惊。我们之前都曾做过志愿者,而且我们为自己足够幸运不需要依赖慈善机构活下去而感到非常感恩。我们都被那站在另一个角度的感受所征服了。
礼物之中有小孩子们描绘并涂色的画,他们用甜蜜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同情与爱,它会让你的心为之一动。一幅特别的绘画上面有一匹马。显而易见的是这位小画家对马有浓厚的兴趣,无论它是否与圣诞节有关。那也正是这份礼物的特殊之处,那个孩子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分享了自己的爱。
这些孩子们是谁,他们又是如何参与进来的?这让我们热泪盈眶。
在我回家之前我们打算出去一天。在看完电影《沙漠妖姬》之后,加里说他自己想吃个甜甜圈垫垫肚子,我们一起去了马克斯餐馆吃东西,那是一家加里最喜爱的路边小饭店,我们要了一个外卖的盒子装好了大部分第二天所需的食物,然后回家。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每到年底,来自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们都会聚集在伯克利的实验室里回顾过去一年的成就并且讨论新一年的计划。加里被分配的任务是给与会者做报告。为了预备他无法参加的可能性,他打电话给一个同事提醒她可能需要顶替自己的位置。可是第二天,幸好我们还是去了,因为当我们抵达实验室的时候,她并不在那里。加里做了报告,由保罗辅助着,并不是那个加里的护士,而是如果加里去世了这个被雇佣来的人会接替他工作。讽刺的是在数月前,当加里通知他的主管有关自己的病情之后,他被告知自己要单独面试并决定雇佣他自己的接班人。至少可以说,这是一项令人很不舒服的任务。但由于他是唯一一个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的人,由他来向申请者解释说明是合乎逻辑的。他选择了保罗作为最合适的人选并且开始训练他,尽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接手加里的工作。保罗在报告过程中负责演示幻灯片,而加里穿着自己厚重的羽绒服站在人群前面,显得异常寒冷而虚弱。待到他的部分一结束,他就准备离开了。当我们匆忙从门口撤退时,保罗跟在我们身后并感谢加里如此亲切有礼。
当我们穿过海湾大桥回到城里时,我问加里怎么看待以后保罗会成为什么样的角色。他的回答,尽管我确信那只是轻描淡写地,是“怪怪的”。
在接下来一周他的新年信件里,他写道:“当我看到自己的血液指数(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都在下降时,我决定告诉单位里的所有人并要求雇佣另一个程序员,这样我就可以培训他们了。物理系同意了。面试接替我的应聘人员以及培训这个新手看起来像是一个荒谬的安排,但我主动要求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这对于和我共事的可爱的人们来说是最公平的方式。”
几天之后——虚弱而又充满希望——加里开车送我到机场,我们互相道别。我不想离开,但我回忆起十几天前我提醒他说他对于我的探访通常是两周的期限,这一次已经延长到了四周。我知道独立自主对于他来说有多么重要。
“我知道,”他说,”但是我真的需要你。”而这一次,我知道我们再也不会一起去任何地方了。
1994
***
1爱心计划:一个非营利性的志愿者机构,为旧金山和阿拉米达县的客户提供爱心便餐、食品服务和营养教育。
2华氏104.6度:约摄氏40.3度。
3Rumi,鲁米,全名莫拉维·贾拉鲁丁·鲁米(MolanaJalaluddinRumi),伊斯兰教苏菲派诗人的。
4Sufi,苏菲神秘主义,伊斯兰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一说源自阿拉伯语“赛法”(Safa),意为“心灵洁静、行为纯正”;一说源自阿拉伯语“赛夫”(Saff),意为“在真主面前居于高品位和前列”。苏菲派赋予伊斯兰教神秘奥义,主张苦行禁欲,虔诚礼拜,与世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