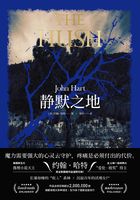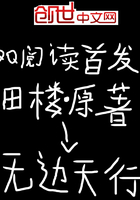那时造反派信任他胜于副书记。因为自三年灾荒以后,杜老实际上只是挂名,S市工作全是危楼二双的爸爸,倒应该算作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独自支撑着。虽然正直得不免迂腐,卖力得近乎傻干,却一心想叫S市老百姓温衣足食的。唯其如此,“文革”一来,首当其冲,成了走资派。滑稽的是,斗归斗,干归干,他还得让S市的各级职能机构运转。说来也可怜,副书记(S市人至今还惦念这位副书记,似乎副是他的姓,书记是他的名)每天结束了工作和被批斗以后,漫漫长夜,象个木头人似的伫立着,仰望天庭。那时,同关在牛棚的人很多,有的说他在看北斗星忽明忽灭,是不是毛主席老人家受了蒙蔽?有的说他在研究天体国运,是不是果真要改朝换代,王八登基?也有的如危楼的乔老爷说:“屁,他只不过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能象一个人似的出那口鸟气罢了!”
如今,他即使英魂不灭,也无可依托。给他开平反追悼会时,骨灰盒里其实是空的,所以也无从获悉他当时在夜空里怅望什么了。
夜壶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杜老觉得光给“中央文革”发致敬电还不够,根据他的领导经验,声势是顶顶要紧的,投上级之所好,千万别怕过头。错了,责任不在你,对了,功劳就加番。而且,形势永远大好,越来越好,哪怕错,也错得正确。所以,他给造反派出主意:“顶顶革命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棋高一着,满盘皆活。S市三忠于活动要做到‘旗手’说过的出绿,最好仿这古铜器,做成忠字纪念章,保险,能在全国打响。记住,铜一锈,就出绿了!”
马屁也要会拍的——
《新唐书》二〇二《宋之问传》:“于时,张易之等蒸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乏。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
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出绿,真亏他想得出来。一纸命令,到了当着走资派还要抓生产的副书记手里。幸好是夜壶,倘若是抽水马桶,副书记还未必能在S市筹集到那么多做纪念章的铜呢!
副书记自然不敢怠慢,其实他本人也是尽忠,效忠,甚至是愚忠的一个。同关在牛棚里的老乔偷偷劝过他:“跑吧!跑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哪怕当盲流,也比这活受罪强!”
他喃喃自语地说:“我应该经风雨,见世面,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应该触及灵魂,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毫无疑义,造纪念章,让S市人人脖子上挂一只夜壶,也是应该的了。
乔老爷浪荡公子出身,正经学问有限,三教九流,左道旁门,倒堪称得杂家。有一天夜里,他悄悄附在副书记耳边说:“我想起来了——”
副书记吓了一跳,只以为半夜三更又押他去触及灵魂呢!“别害怕。”他连忙安慰这哆哆嗦嗦的老上级,然后,提了个荒诞的问题,“古代人小便不?”
副书记不解其故,没有回答。
“古代人用不用夜壶?”
不知其所以然,仍在暗中发怔。
“副书记,我看这青铜器,很可能是那玩意儿呢!”
他堵住老乔的嘴:“你疯啦!你想讨死!你活够了!你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夜无话,可乔老爷听得他辗转反侧,彻夜未眠。天麻花亮,他忍不住了,趴过来问:“老乔,你根据什么这样看?”
乔老爷说:“造物者必有所本,万变不离其宗。夜壶这东西,总是脱胎性器官而来。”
副书记懵懂了,可那是一个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年代,他怎敢违拗,只好布置下去。不过,他和杜老不同之处,当上上下下脑袋发热到四十度的时候,他宁可冷一点,否则,最终吃苦头的还是老百姓。所以,他去找他的对头,希望能影响一下造反派,万一真是夜壶,那亵读罪可是十恶不赦的。
“什么?夜壶?胡说八道……”杜老差点没蹦到房顶。
“你冷静些!”副书记对他并不怎么客气。要不是他儿女多,儿女亲家多,死保住他,不撤职查办,也该卷铺盖滚蛋了。副书记也自有革命天真之处,总期待着他的觉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譬如他将拆迁危楼的经费,盖了他住的四合院,倒是副书记在全市党员大会上检查自己没坚持原则。其他劣迹,恕我为维护老人家的名节,就不一一写了。杜老自己也很坦然:“有什么?大家都犯的错误,大家都搞的特权,大家都沾的便宜,大家都有的关系网。彼此彼此,我虽不比谁少,可也不比谁多,才不在乎咧!”他进一步阐发这理论,“大家都这个水平,大家都这个作风,大家这些年都这么过来的,你能拿大家怎样?大家不怎么样,我杜某人又能如何?”
“您老高见!”我不得不钦佩。
“这就是气功!”他没头没脑回答了一句。
好久我没能悟透杜老这句话的真谛,后来终于明白,气功练到炉火纯青地步,就出神入化,刀枪不入了。
杜老听到副书记冷冷的语气,更是火上浇油。那时,他有造反派撑腰,而且他家把我们危楼的一位半仙之体,武老头,悄悄地请到四合院里,让这位阴阳先生看了看风水,是发还是不发?发在儿孙还是发在本人?希望得到启示。武老头外号武铁嘴,旧社会在城隍庙靠算命打卦为生,他知道这位大干部,不好意思出面,躲在屏风后面,竖着耳朵;便天花乱坠,云山雾罩地开讲,科学术语,革命词藻,阴阳五行,善恶轮回,一锅大杂烩把杜老说得心悦诚服。最后又掏出一张大团结票子,请老神仙摇了一卦签,签上四个字:“福至心灵”,差点没把屏风后边的人,高兴得滚落到藤椅下面。压了好些年的杜老,“文革”一来,副书记靠边,他便有了小老婆扶正的得意感,指着对手说:“你不觉得天变地变人也变么?老黄历看不得,老调子已经唱完,老路压根儿行不通了么?老弟,奉劝你一回,大家都不认为是夜壶,大家都希望表忠心,你还是不要跟造反派小将作对,闭上你的嘴,去好好干吧!”
我们S市发放小夜壶那天,真是一个风和日丽、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全市人载歌载舞,喜迎宝章的狂热劲头,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那时值得敲锣打鼓去游行庆祝的事件,节日,喜讯,指示就够多的了,但由于是S市自己的献忠活动,越发搞得有声有色,挂小夜壶成了隆重的授勋仪式。排场之大,花钱之多,连怂恿造反派放手干的杜老,也不得不赞叹小将们的勇气。
危楼自不例外,也应该轰轰烈烈。可是,世界上最善于搞繁琐哲学者,莫过于我们自己了。谁有资格挂,谁无资格挂,订出来五条十八款三十二项细则的标准,各街道成立资格审查委员会,一个人一个人过筛子。可怜我们危楼近百名居民,能够上台伸长脖颈套小夜壶者,只有范大妈等有限的几位。至于已经定性的坏人,也就死了这颗心。可半好半坏的人,或不好的好人,不坏的坏人,却十分看重这夜壶,它等于是通行无阻的腰牌。没有它马上被视为异类,成了印度教不可接触的贱民,或是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下的黑人、犹太人一样。
危楼成了一锅粥,那还了得,夜壶等于是通灵宝玉,有它不见得多好,没它可是性命交关。争的抢的,哭的闹的,好端端的,平添一段烦恼,弄得人仰马翻,鬼哭狼嚎。现在回头去看,危楼一部争斗史,你咬我,我咬你,恶性循环,似乎人到世上来就是咬人与被咬的。其实换一种不龇牙咧嘴的生活方式,彼此相安无事,地球也未必转得慢些。好,连有一个最最革命名字的老太,也剥夺了夜壶悬挂权。因为她散布过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论。
“我活了八十岁!”吴清华找绳子要上吊。
挂了几次,危楼的木头早朽烂了,硬是吃不住劲,还没等绳圈套住脖颈,便断了。大家见老太死意坚定,便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打报告。结果批下来了,四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她想上吊,奈何奈何!”危楼人文化水平不高,怎么也揣摩不透“奈何奈何”的题外之意。老太自己也胡涂了,不知是生好,还是死好?手里掂着根绳子,两眼发直,已露出精神分裂症的先兆了。
S市人民至今犹缅怀死于“文革”的副书记,恐怕还在于他能把老百姓放在心上。其实S市的子民,最容易满足,他们并不要求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哪怕先天下之乐而乐,能够分一杯残羹给大家,也就可以了。所以,副书记对拆迁危楼的经费,被杜老挪去盖四合院,从心里觉得愧对危楼百十口人,总是不能释然于怀,时不时来Y大街,踅进J巷看看。正巧这一天,四句偈语下达,老太生死两难之际,副书记被危楼吵闹得如四级地震般摇晃不已的状态吓坏了,问了究竟,方知为了宝章差点闹出人命。这位布尔什维克一面感叹,中国人的命也太不值钱;一面更沉重地思索,革命本来平等,共产主义的目标乃世界大同,却偏偏要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尊尊卑卑,等级森严,贵贱有别,层次分明。可想到自己也成了九类分子之一,不禁苦笑,真有白革了这多年命的怅然若失感。不过,小夜壶手里尚有数枚,全掏出来,交给这群鸡争鹅斗的人。
他以为本可以平息这场争吵,危楼再经不起折腾了。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些自以为是好人,脖上已挂有夜壶者,又愤激地表示抗议:“他们也有资格佩戴宝章,我们通红通红的红五类往哪儿摆?”
副书记想想也不能怪他们自恃高贵,这些年自己不也助长这可悲可怜的胎里带的优越感吗?“好了,好了,你们成份好,出身好,家庭没有污点,个人历史清白如玉的,一人可以佩戴二枚宝章!”
万岁!
于是,危楼百十口人,浩浩荡荡,成双列通过J巷,Y大街,朝十字路口进发。龙种们胸前,两夜壶撞击,叮当作响,好不荣光。非龙种们脖下,虽仅有一枚夜壶,形单影只,但聊胜于无,也足够维持心理平衡。一路上,锣鼓自然要敲,样板戏自然要唱,也许心情太激动,来不及西皮二簧,一板一眼,干脆在范大妈的手势下,只喊:“谢谢妈”三字,不言而喻,是为谢谢妈赏赐了夜壶而呐喊的。
主会场的热闹排场自不必说,“中央文革”的特派员都到场助威。杜老三一说,四一说,竟和这位大人物排上了转折亲。儿女亲家多的好处便显示出来了,如同押宝似的,门门有彩,怎么能落空呢?天气又那么好,话题就更多了。会场风光,杜老几乎独占了。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同是夜壶,区别颇大。不但象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章,有金质、银质、铜质之分,而且在重量上有三千克、两千克、一千克的不同。中国人在封建社会生活了几千年,搞这一套可算十分娴熟顺手。危楼人刚才拼死拼活争夺的夜壶,不过是十五至二十克的大路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