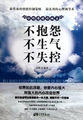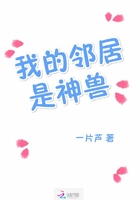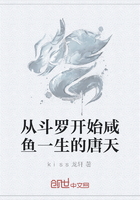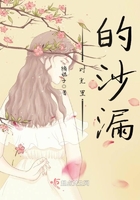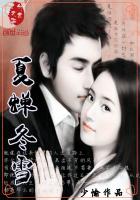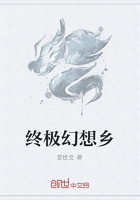攻读史书,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五法。
读史:丙申年购《二十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攻读史书:我在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我训诫道:“你为了买书而向别人借钱,我不惜一切地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圈点阅读一便,才算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从此以后,我每天都仔细读上十页,如果稍有间断,就是对父母不孝。
攻读史书,是曾国藩为了避免前车之鉴,吸取古人教训。
读书有方,身心兼治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在读书的同时,曾国藩还精于养身,他的养心法是身心兼治。他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的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养身之道十分留意。他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就是这个。”一个人只有身体与心理都健康,干大事才有足够的资本。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是现代的卫生学非常强调的。至于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则是健身与养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确实是一种达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径。曾国藩一生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他一生多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那段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他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究,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在这个时期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非常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曾国藩的道家思想始终都有所表露。他认为于名利之外,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曾国藩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曾国藩一生多变,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他人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人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朝廷的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人死。但是,后来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呢?而且许多人都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史书,希望能从这些历史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这次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以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曾国藩用道家的思维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工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顿时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以前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非常反感,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1858年6月,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他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
学,不见得有所成,但不学,必无所成。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如此循环往复,才会学有所成,终有所用。
曾国藩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林则徐“官办船炮局”设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切实践履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认真向西方学习而卓有成效的第一人,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勃然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19世纪60年代,地方以曾国藩为首、中央以奕为首发起的洋务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内忧外患”。“内忧”即太平天国运动,“外患”即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双重目的性——对内镇压农民革命,对外御侮自强。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曾国藩是有名的实务家,他拥有救世的务实态度。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心存忧患意识。林、魏如此,曾国藩也不例外。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在驱动力。
因为鸦片战争,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
李鸿章组织淮军,参与上海保卫战。新募淮军,一艘船用英国兵舰,由安庆运输经过南京,太平军却对它接连夹攻。上海之战、苏州之战,李鸿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洋枪军”,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胜,故有“常胜军”之誉。常胜军的洋枪洋炮,杀伤力大、射击力远,戈登以少击多,不在话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耳闻目睹这些事实,怎能没有奋发自强之念?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氏就形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人,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他主张“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因此他十分重视“自强”,自强又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他又说:“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列强)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最终达到“庶几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御侮自强之目的。
曾国藩因为洋务运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二是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五是会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刚夺取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徐寿的字)创建军械所于安庆。”安庆军械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不仅如此,军火生产引起“工作母机”的输入与仿造,进而逐渐形成机械工业,推动整个近代化的进程。曾氏后来派容闳出国采购“制器之器”,正是他从军火生产需要出发而迈出的近代化步伐。
军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进一步造出小火轮,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徐寿父子、华蘅芳等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数学物理知识,根据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外国轮船的观察,克服军械所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由华蘅芳负责计算,徐寿主持设计、建造,徐寿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氏亲自观看了轮机试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描述道:“窃喜洋人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厂在此基础上,华、徐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于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交水师蔡国祥营使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给它取名为“黄鹄”,曾氏登上轮船,行了八九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该船长二丈八九尺,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速度相当于每小时六公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这是光明的起点,曾氏要求“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当然,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要是模仿,还未能脱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开办技术学校,设翻译馆传播西学,派出留学生等,为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对于以后的民主、政治改革实在也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的。曾国藩深知时局的艰难,凡事都谨慎小心,事无巨细。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后评论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积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洋船、演习军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洋务运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运动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结尾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应该获得肯定和赞扬的。
脚踏实地,学自有得
自立于世,严于律己,始终努力不弃,方能终有所成。
机关算尽的琢磨不如脚踏实地地生活,这是成功者的警言。
曾国藩出身贫穷,一生为官清廉,深知财可帮人也可害人的道理,所以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
他为官一生,虽然没有很多遗产,但绝不是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未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他希望自己留给后人的都是有益无害的。
这也是曾家的传统。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自食其力。正所谓“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骄奢淫逸,即使身处富贵,也注定失败。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之时,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倚仗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化为乌有。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致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同沉)澜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任意花销,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严厉,却能警醒后人。
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且看多了官宦子弟骄奢淫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沟壑的下场。基于这种认识,他要求弟弟国潢设法将自己在家乡的田产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捐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需之用。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便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立勉励自己,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能够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他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他写道: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