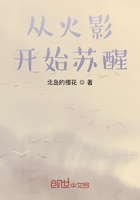中午,张杏菊顶着炎炎烈日,一担担地挑水,一把把地撒麦秸,一趟趟地拉石碾……直到黄昏,太阳西沉下去,硬是把那块被牛颠跳糟蹋的晒场地重新压整平坦了……“从乡下回来那天,张阿姨为我装了满布袋炒熟的花生和蚕豆。我心里害怕张阿姨会将我闯祸的事情告诉我妈妈,害怕德君受了委屈会到我妈那里去告状,去诉苦……结果我猜错了,张阿姨和德君压根没提那件事。”
张杏菊在梅儿面前直夸起肖义来:“你们家肖义真聪明,比我们家德君强多了,在乡下,什么农活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不像我们家德君,直笨死了。”
梅儿一边乐呵呵地笑,一边揭起肖义的老底来:“肖义那淘气劲儿我算是讨受够了。他敢将刚出壳的长虫当作泥鳅养在小瓶里,他敢爬树窜房去掏还没长全毛的黄嘴小麻雀,然后用火烧死,燎焦了塞进嘴里去吃,你家德君敢这样吗?你甭一个劲儿夸他。这趟跟你们到乡下去,没给你们闯祸,没惹你们生气,没有让你们太操心,我就算是烧高香了。肖义那个淘啊,我算是领教够了。哪比得上你们家德君文质彬彬,老老实实又安分守己。”
张杏菊笑笑说:“我们家德君好什么呀?不会说,不会道的,见了个生人脸会红的像个姑娘家,一点也没有男人的那种出息。赶不上你们家肖义一半儿的机灵劲儿。”
梅儿哭笑不得地攥住张杏菊的手:“你要是真看肖义好啊,拿去做儿子算啦。”
张杏菊佯装当真的说:“这话可是你说的,可别后悔。我就不信你舍得呀?”
“有什么舍不得的,就怕别人不敢要哩。”梅儿故作舍得地道。
张杏菊瞅着梅儿,露出一抹会心地笑:“梅姐,你可别得了金子还嫌贵啊……”
“结果妈妈和张阿姨的一阵笑声就让那件事儿平静地过去了。”肖义回忆着童年的往事,恋恋的,甜甜的,痴痴沉沉的样子。
刘红霞静静地望着依然发痴的肖义,好半晌才说出一句十分中肯的话来:“肖义,你还算有良心,没忘了这些美好的事情。你跟我说一句老实话,你留恋这些吗?还想回到从前的欢乐中去吗?”
肖义怔怔地看着刘红霞,没有一点勇气敢把自己心里的话告诉给她。
“我替你说了吧。”刘红霞很干脆地说出来:“其实你心里很想。你一直都在想。你无法忘记你曾经经历过的这些事情。这些美好的往事曾经构筑起你美好的往昔,在你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你无法忘却它,更无法从你的心里抹去它。只是你碍于情面不敢公然去正视它,去面对它,全被你那个怕‘丢人’的男子汉的‘自尊心’欺骗着,压抑着。加上平时你唯外婆是遵,外婆对你的感染,对你的影响太深。有时候,你偶尔会意识到外婆的某些做法不对,但你又必须死死地维护外婆的尊严。尤其在肖伯伯的态度上更能说明这一点:你一面赞成肖伯伯的热心肠,一面又去诋毁肖伯伯助人为乐的一些做法。这就是你最大的缺陷,也是你最大的可悲之处。其实肖伯伯一点都没变,还像从前热心和善良,真正改变的是你自己,而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问你,如果你妈妈还活着,你爸爸这样去做,你是不是觉得他应该?你会不会觉得一切都很正常?你会不会去赞成他这样的做法?
这就是你的误解。是你受外婆影响而对你爸以及张阿姨之间所产生的一种很深的误解。当这一切都弄明白之后,你不应该再让这种误解继续下去了。勇敢点吧,肖义!诚心诚意去向张阿姨认错,该赔礼赔礼,该道歉道歉。”
“这……”肖义面有难色地看着红霞。
“这没什么难为情的。我都替你分析过了,就算张阿姨恨你,也只是恨你的一时糊涂。听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里,我可以看得出来,张阿姨绝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而是一个完美的,宽宏大量的女人。你还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因为你是肖正春的儿子。肖伯伯曾经帮助过张阿姨,打狗看主人,冲这层关系,张阿姨也不会太为难你。再说了,你曾经是她喜欢过的孩子,你都没有忘记的那些往事,想必张阿姨更不会忘记。俗话说的好:‘大人’不计‘小人’过嘛,张阿姨会跟你计较这些吗?关键是看你自己诚不诚心了。”
“那我怎样去做才叫诚呢?”肖义疑惑不解地问红霞。
“你自己想去吧。”红霞一语双关地告诉肖义:“用你自己认为最有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诚。”
中午,张阁祖的夫人刘美荣系上围裙踅进厨房里,亲自掌厨,洗、斩、剁、颠、炒、煎、炖地特意为肖正春烹调了一桌拿手好菜。这使肖正春感觉到非常地不好意思。看了坐在左边的师兄张阁祖一眼,又抬眼看向端着最后一道菜肴步出厨房的刘美荣:“嫂子,又给您添麻烦了。瞧您,为了我忙里又忙外的……”
刘美荣手里端着最后一道烹制完毕的红烧鲫鱼,步到自家的红木餐桌旁,将手中飘香的红烧鱼搁放在餐桌上,双手叉腰佯装生气地说:“说什么哩,正春?你有些日子没上我们家来了,也学会说起客气话来了。梅儿活着的时候,我和阁祖上你们家去,梅儿不也是这么忙活吗?”
“那是应该的嘛。”肖正春摸摸下巴笑着说道。
刘美荣放下佯装的姿态,在丈夫张阁祖的身旁拉了凳子坐下,微笑的看着坐在丈夫右手边的肖正春:“那我就不应该啦?也不分分谁跟谁了,尽说客气话。你和阁祖有些日子没聚在一起了,难得今天你俩都有空,只有我没得空,为你们做不出什么像样好吃的饭菜来,只是家常便饭,正春,你可别挑剔哦。”
“嫂子,这些就够丰盛啦,若让我做,可做不出这么好的美味佳肴来。我光剩下享口福的份儿啦,就不跟您客气了。孩子们都还没回来,还是等等他们一块儿吃吧。”肖正春说着话,起身来到客厅,拧开了音响。
“孩子们中午都不回来吃,要到傍晚下了班才能回来,你就甭客气啦,饭菜都凉了,来,吃。”
几个人在优雅的《澎湖湾》的音乐中开始用餐。
张阁祖起身从酒柜里拿出一瓶精装的“古井贡”酒来说:“就着有菜,正春,咱俩少来一点儿。”
肖正春连着摆手:“嗳、嗳、嗳,我可不敢了……昨晚上可是被折腾怕了,这辈子恐怕再不敢沾酒啰。”
“那你就吃饭。”刘美荣将刚盛好的一碗米饭递过来,又夹起一些菜放进肖正春面前那只小碗里:“这是你最爱吃的梅菜烧肉,正春,你多吃点。”
“嫂子,你甭客气,我自己来。”
张阁祖为自己倒好了一杯酒:“想吃什么自己动手,又不是外人,随便点反而自在,越客气越让人感觉别扭,还是自然点儿好。”张阁祖说完,提起汤盆里的一只鸡腿独自撕咬起来。
刘美荣很不满地乜了丈夫一眼:“都像你这样倒好,天天吃喝也不腻。”
“这就叫福分。”张阁祖有些得意更有些陶醉地举起酒杯啜饮了一口。三个人同时开怀大笑起来。
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谁这么及时,正赶着吃饭的时候打电话来?”张阁祖放下筷子和鸡腿从旁边的桌子上抓过自己的手机瞅了一眼,忙递给肖正春:“是你们政委打来的,”
“是王戎吧?”刘美荣在一旁说道:“让他赶紧过来陪我们家阁祖喝两杯。”
肖正春放下碗筷,接过手机,又点下头:“政委吗?你可真够及时的,我这刚端起碗筷来,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电话那头:“老肖啊,你哪来那么好的口福啊?你这是在那说话呢?”
“你明知故问。我在阁祖家里。嫂夫人可是发话啦,让你马上赶过来赔陪阁祖干两杯。我告诉你,菜可是刚端上来的,还都是你最爱吃的几样菜,我给你报报:有清炖老母鸡,有梅菜烧肉,有红烧鲫鱼,有烧鹅,还有油炸的花生米和鱼香肉丝、酱牛肉,这些够意思吧?你说你过不过来吧?我们可都是诚心诚意在等着你。”
“我呀,还真抱歉了。夫人做了一大桌好吃的,这不,两个舅子也过来了,我总不能‘临阵脱逃’吧?要不你们都到我这边来吧,我这儿可比你们那丰富多啦。”
“你那边不能‘临阵脱逃’,我们这边也不敢随便‘过关卡’,我看还是‘各自为阵’吧。唉,我说,你找我有事儿吗?”
“你还真猜对了。老肖啊,全船的水手买了东西要到医院里去看望老太太和张杏菊……”
肖正春充满怒意地吼道:“简直乱弹琴。这一定又是你的主意。你想给我添乱是不是?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情?是什么很光彩的事情,值得你们去慰问?你这个政委算是白当了,什么该掺和,什么不该掺和你都分不清了?你究竟怎么回事儿?我可告诉你哦,立即阻止他们,一个也不许他们到医院里去。告诉他们,真要是想‘孝顺’,以后有的是机会,可眼下不是时候。我肖正春谢谢他们了……你叫我怎么说你吧,政委?我现在是怕沾上这事儿,唯恐躲不及。我这正合计着晚上要跟阁祖去走船,到外面去散散心。你可倒好,死皮赖脸硬要往里钻……”
“老肖,我这可是一片好心……”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我俩共事这么多年了,我还能怀疑你吗?可你这种好心会帮倒忙。你懂吗?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更不同于我们处理船上的事情。”
“行,行,行,我全听你的还不行吗?马上叫水手们都回去,谁也不许到医院去!其实我也感觉不妥,这才打电话过来跟你商量的。既然都说明白了,这事儿就这样了。不过,老肖,我可得提醒你:跟张阁祖走船,你可得提防着他点,他这人‘鬼’得很,别让他把咱独创的那套‘严、细、实’的管理经验从你嘴里给套了去……”
“这事嘛……你自己跟阁祖说吧。”肖正春有意回避,将手机转给了张阁祖。
张阁祖接过肖正春递过来的手机:“喂,是王戎吗?我是张阁祖。怎么的,你们肖船长跟我走躺船你不放心是怎么的?我成了老虎还是豺狼?会生吞活吃了你们肖船长?你要是不放心,把他领回去好了。我本来就不想带着他,是你们肖船长‘死皮赖脸’硬要跟着我……既然你亲自过问这件事,我可得当面锣、对面鼓地跟你把话说清楚:你抓紧过来把你们船长带走,我对他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望着张阁祖打电话时故意装腔作势的那种神态,肖正春和刘美荣在一旁都禁不住的笑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王戎的声音:“张船长,你可千万别误会。肖船长跟着别人,我不敢说‘放心’,跟着你,我是一百二十个放心。你俩是师兄弟,还有比这层关系更铁的吗?还有比跟着你出海更合适的吗?”
“既然这样,你算是同意喽?放心吧,王政委,你们肖船长跟着我,我不会亏待他的。”
“我可告诉你张船长,老肖跟你走时是个什么样子,你返航时还得交还给我个什么样子的。老肖要是瘦了一点,我可‘饶’不了你。”
“放心吧,我一定尽心尽意地盛情款待。不过我可得提醒你一句:你什么时候见老肖长胖过?哈哈哈,就这么说了……有时间咱们聚在一起好好聊聊。”
“一言为定,祝你们晚上走船顺利。”
“那我就说声‘谢谢’了。你跟你们肖船长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话都让你一个人抢着说完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就这样,再见。”
“再见。”
张阁祖合上手机,简直要笑弯了腰:“你们这个政委啊,什么都好,就是虚荣心太强。”
肖正春赞同地点点头:“有荣誉感固然是件好事情,但若把它看成是个人私有的‘财富’,那就大错特错了。就拿那套‘严、细、实’的管理经验来说吧,不错,那是我们‘海弋号’总结创造出来的。既然是一种好的经验,那就应该成为大家的财富。我们的责任就是共同提高,共同创造一种高质量的作业水平。谁也不敢保证‘海弋’号的经验就是天下第一流的,就是最好的!它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和补充。这种完善和补充完全靠吸取别人的先进经验和管理方法。所以说:‘海弋’号的经验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只是我们暂时做的好一点罢了。”
“嗬!真不亏是‘海弋’号的船长啊,水平就是不一样。要不然怎么让你当咱全局的龙头老大?”
“快吃,快吃,菜都凉了。”一旁的刘美荣催促道。然后端起盛装着老母鸡汤的汤盆站起身:“我去给你们热热汤。”说完端起汤煲走进了厨房。
夕阳浓浓地洒在海面上,把一切都染成了红色。
肖正春在张阁祖的陪伴下踏上了待航的“海神号”货轮。
“海神号”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粱大秋热情地迎上来握住肖正春的手:“肖船长,你可真是稀客呀,刚才接到张船长的电话,说你陪我们走这趟船,可把我乐坏了。平时我们就是想请也请不来你呀!”
“不用请,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肖正春调侃地说。大家听他这么说,全都跟着笑起来。
张阁祖朝粱大秋摆了摆手:“我看都是一家人,谁都不用客套了。”转过身来征询而又诚恳地看着肖正春:“正春啊,趁着‘海神号’所有水手都在甲板上,你就给我们讲一讲,介绍介绍你们‘海弋’号好的经验,也让我们学着点。”
“来,欢迎肖船长给我们讲几句。”粱大秋带头鼓起掌来。
肖正春跨前一步朝大家摆摆手:“刚才你们张船长说了:我们都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我也就不跟大家客气啦。刚才你们梁政委的一席话倒是提醒了我:他说我是个稀客,平时就是想请都请不来我。其实,我并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无意中将自己封闭起来了。——也就是那种保守吧!使我们之间缺乏沟通,缺乏了了解。缺乏了这两种东西也就等于缺乏了一种信任。为了打破这种保守,打破这种不信任,我们有必要经常沟通和了解。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整个‘海弋’号上都是一群极普通的人。这话虽然说出来了,那么就从我开始吧,也从今天开始吧。以后我们彼此经常都走动走动,交流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欢迎大家到我们‘海弋”号上去作客。
“我今天在这里说一句心里话,’海弋‘号不可能永远当第一,别人很快就会赶超上来。要说我们有什么好的经验,我可要’保守‘地告诉大家:那不叫经验,那只是我们采取的一些比较可行的办法,暂时取得了一些成功,我们管它叫做’严、细、实。‘。什么叫’严‘呢?就是严格内务。我相信一个人的穿衣打扮和他的形象思维密切相关。他个人的形象塑造起来了,那么整个一条船都会跟着亮起来。如果一个人,穿的邋里邋遢,衣领发黑,皮鞋上尽是灰尘——连自己都不想好好去收拾收拾,那么要塑造一条船的形象他更无心去收拾了。所以我们’海弋号‘的水手站出来的时候从头到脚都是干干净净的。服装要笔挺,裤子要挺直,皮鞋要锃亮,仪容要整洁,这些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一条规定被纳入每天的考核评比中。你没看,连我这个半大老头子的衣服都是笔挺的,皮鞋都是锃亮的,有时候还忘不了往头上去焗点油……何况年轻人,更愿意去刻意打扮了。美丽和整洁是一个人的权力和尊严,必须很好去维护。
”什么叫’细‘呢?那就是对工作一丝不苟,’海弋‘号上有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哪一项,哪一件都有严格的评分制度,实行层层负责制,给分制,人与人之间,岗位与岗位之间形成互控监督激励机制,并且和奖罚挂起钩来。干的出色的就应该奖励,干的差的就应该去罚他。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谁不想要个面子?谁愿意老是受处罚?挨了罚的回家跟老婆也没法交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自我激励的机制。这样相互促进就能带动相互提高,造就整体水平的提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大家,在我们’海弋‘号上找不到一处卫生死角,也找不到管理的死角。这就是’细‘出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