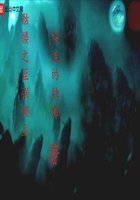第十四章 天边一丝水线(4)
“二位兄台,”那青年手拎个酒葫芦,一脚跨进仓来,爽朗地重新见礼:“适才忙乱,还不及请教大名呢!”
剧孟和白龙忙起身还礼,说了姓名。只觉这人长得平头正脸,龙眉凤目,左脸颊还有个浅酒涡,虽说带些女相,却是一副倜傥不羁的神气;方在诧异此人是谁?
那青年已喜孜孜拉住二人的手,“哎呀!想不到是二位兄长。‘赌神’大名如雷贯耳;‘分水犀’白兄,水里功夫更是了得。老天把兄长送来,真快活死了!”
他说着,冲舱口高喊:“喂,快拿干衣服来,让二位兄长换上。哦,恐怕早饿了,请先少用一点干粮,到了寒舍,再摆酒压惊!”
“还请教高姓大名。”剧孟和白龙连忙问道。
“在下符离王孟。”
“原来是江淮‘辣手醉侠’,久闻大名!”剧孟、白龙早就听说,此人武功高强,最嫉恶如仇。于落难之中,忽遇此人,剧孟和白龙自是高兴非常。
“小可平日贪杯,行为无状。”王孟笑着摆手,“这‘辣手醉侠’,是江湖朋友乱叫的,实在当不起!”又道,“既到了这里,可千万别见外,就如同到了家里一样。”三人又交谈一回,都觉相见恨晚。
原来,经过两天多漂流,已进入吴国境内;此地属符离集县界。王孟乃当地土著,祖辈传下淮河上的船帮行当,有一二百条渔船,兼营鱼牙生计,家中颇为富有。王孟自来任侠尚义,专喜济困扶危。今日清晨,听说黄河决口,洪水成灾,便招集了一些同道之交,备了几条舟船,打着救一个是一个的主意,在附近水面救助灾民。从早到晚,已救起百多人。
无移时,耳听船舷外水声“哗哗”,离岸已近;又顺岸边走了二三里,才到停泊之处,一同上岸。岸上是一片矿野,天早黑透,满天繁星闪烁。地面上余热还未退净。道旁水塘内,蛙声“咯咯”不绝;树上蝉鸣“伏天——伏天”,此起彼伏,汇成一片繁喧。
同船五七个灾民,都是刚救起不久,下船便被众人用担床抬走。王孟陪着剧、白二人,又步行了七八里路,才到王孟的家中。
当地不过几十户人家。王宅建在一座崖坡腰上,三面都是古柳高槐,依坡一座大院,内有几进房舍。进到一间宽敞的客厅,刚分宾主坐下,便听马嘶之声。
剧孟不由想起:“此次出行,本带着不少匹马,准备到南方贩出。谁知突遇洪水,只自己和白龙逃得性命,其余人怕都凶多吉少。”正暗自伤神,主人忽往外走去。跟着,便听主人和好些人在说话,似在查问先后所救灾民的食宿、医药是否安排停当;并有八、九匹马由房后而去;又有一女人声音,好像在说“从另一河面救上个少年”。
隔了片刻,王孟走进来道:“二兄住处在跨院,清静些,也凉快。饭就开在那里,恐怕早饿坏了!”
宾主三人随到跨院入席。几案上已摆好饭菜,一盆蒸鲂鱼,一盘素鲜笋,一碟拌白藕,一碗濯鹧鸪——美食美器,格外精致。还有几样腌制小菜,一大钵绿豆稀饭,一叠葱花脂油麦饼;一坛好酒,刚开了泥封,溢出淳香。
剧孟、白龙见此,不由肚腹咕咕叫得愈响。
王孟笑道:“听说二位兄长到了,拙荆怕下人做得腌臢,亲自做了几个菜。天气热,只备了一些清淡的。”说罢,王孟殷勤地为剧、白二人筛酒。
剧孟见他提起“内子”,便客气道:“弟妹怎不一起来用饭?”
王孟笑道:“方才‘虎子’,噢,我的一条狗儿,极通人性的。它从西边河面救上一个昏迷不醒的孩子,拙荆正在施救;过一会儿她就来……”
话音未落,就听院内一个清脆声音:“来了,来了!”伴着银铃般笑声,进来一位娇小女子。她不过二十四五岁,一张清水脸儿,秀目黑白分明,澄如秋水,耳鼻眉口无不滴粉搓酥。真个江南姝丽,秀骨天生。
这女子很是洒脱,立即上前见礼,脆生生笑道:“奴家拜见二位兄长;几样菜肴,不知对不对口味。”随即入席,先为客人盛粥、布菜,后为自己面前的空杯添了酒。
她,便是王孟的妻子王左氏,闺中小字“阿儿”。
王孟道:“二位兄长,请先用一点稀饭,压压火气,然后我们再喝酒。”
剧、白二人均觉主人考虑周到,各喝了一碗绿豆稀饭,就了一些小菜,精神也比适间好多了。
王孟这才举起酒杯,笑道:“准备仓促,不成敬意。我夫妇二人,为兄长洗尘压惊!”
剧、白二人至为感动,一齐举杯道:“落难之人,受此款待,有生难忘!”大家一起干了。
剧孟、白龙尝了各样菜肴,果然清淡可口,便脱口称赞,“弟妹烹饪,果然好手段!”
左阿听了脸现红霞,益发有些得意,瞥了王孟一眼,却道:“承蒙二位兄长谬奖,村妇粗手,哪得好滋味——如尚中吃,不过是二位哥哥饿了,又格外捧场呢!”
剧孟、白龙都羡慕道:“王老弟好福气,天天有此美味佳肴,真神仙也!”
王孟瞥了左阿一眼,笑道:“平日她才不动手呢,都是下人做饭;今日自不同,二位兄长来了,这才……”
剧孟、白龙听了“哈哈”大笑。他二人虽然都还没有成家,却也瞧科王孟与左阿感情极好。左阿聪慧爽快,王孟外稳内热;左阿抢话争胜,王孟言辞随和,有些惧内。二人结缡过日子,确是一对神仙眷属!
酒过三巡,又说了些闲话,气氛愈加亲热。
王孟端起一杯酒,满脸祈望:“剧兄、白兄,在下有句不知进退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我三人,萍水相逢,一见如故。在下斗胆欲与二位结拜,不知能否高攀?如肯俯允,请干此杯!”这几句,说得极是至诚。
左阿抢道:“也把我算上!”
剧孟看了白龙一眼,当即举杯笑道:“我早有此意,不知白弟如何?”一扬脖把酒干了,照照杯底。
白龙欣然同意,“那还用说!”一仰脖,也把酒干了。
左阿酒喝得急了些,连声咳嗽,脸也红了。众人看她,更是满脸生春,愈发艳丽。
“不过,”剧孟略加思忖道:“王孟弟,既要结拜,有些事要说在前面。我们这趟买卖,共出来四十多人,除了门人以外,内中亲如兄弟的共是八人,有阳翟薛况,济南瞷家兄弟,颍川灌夫,还有曾厚和倪猛。这次遭遇洪水,我和白弟逃得性命,其余人至今生死未卜。唉,倪猛还是个孩子。五年前,他全家遭人仇杀,我将他救起,实指望把他哺育成人,为父母报仇……”
说至此处,剧孟已是泪流满面。王孟甚为感动,知剧孟乃至情至性之人,忙道:“原该不忘旧人!今日我们三个,对,加上贱内——共是四人,先行叙齿。日后其余弟兄聚在一起,再次磕头结拜可好?”
“如此甚好!” 剧孟道,“在下痴长二十有六,就忝为大哥了!”
“在下虚度二十五岁;不知白兄,比在下是大是小?”
“在下只好屈居老三了,”白龙笑一笑,“二哥,我比大哥小五岁呢!”
左阿扑哧一笑,露出好看的贝齿,撒娇道:“哼,就是我小,先当四妹罢!” 她并不说年龄。
剧孟接道:“我知道,薛况二十二,灌夫十七,曾厚二十;倪猛最小,就是老幺——如果他们都活着,该是多好!”说至此处,剧孟不免黯然。
左阿忽道:“适间救得一少年,不知是否倪兄弟?他穿甚衣衫,长得何等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