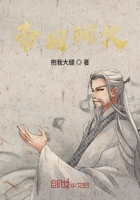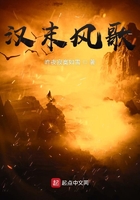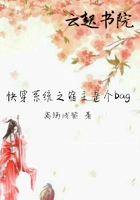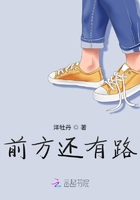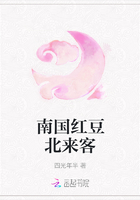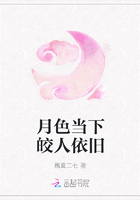杞敕停住脚步,站在了殿外青石铺就的路上。
“不对,这卷书,夫子还没为我断句!”后知后觉的杞敕,终于想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转了半个身子,正准备回去“提醒”夫子;似又想到什么,杞敕再次定住了脚步。
“也许,这也是夫子的考验?”杞敕暗自揣测,终究将头一甩,意气道:“不管了,总不能让他小瞧了我!”
“说不定,是夫子疏忽了,此刻正等着我回去?”杞敕犹自迟疑,终究迈开大步,风发道:“我就不信,没了他我连书都读不通了!”
“句读虽然困难,还是有迹可寻的,也就多费一些时间罢了。”杞敕给自己打着气,面容却犹带些愁苦。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
曰若稽古帝尧……”
回到自己的小亭子,杞敕并没有第一时间开始攻读这卷新书,而是继续诵读《尧典》。第一,杞敕觉得自己诵读《尧典》时,尚有许多不通透的地方;第二,杞敕要通过诵读《尧典》培养语感,理清《尧典》的行文脉络、掌握《尧典》的用词规则、句读特征。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杞敕正是准备用《尧典》来攻读这卷新书。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杞敕从“敬授民时”这一段中挑出这颇耐寻味、似曾相识、又不得其解的四句,反复咀嚼。
“日中、日永、宵中、日短……”
“仲春、仲夏、仲秋、仲冬……”
“仲,从人、从中,中又为声。最初应为‘指示’字‘中’,表示正中;后来用来表示兄弟里面排在中间的那一个,所以加了‘人’部。”杞敕根据杞老夫子传授的“六书”,解剖着一切可利用的信息。
“嗯,应该是了!”杞敕眉头紧锁,点着头道:“这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就是中春、中夏、中秋、中冬;一春之中是‘春分’,一夏之中是‘夏至’,一秋之中是‘秋分’,一冬之中是‘冬至’;地理课本中春分是三月二十一日、夏至是六月二十二日、秋分是九月二十三日、冬至是十二月二十二日!”
“‘日短’与‘仲冬’对应,也就是与‘冬至’对应;另外,日就是昼,昼就是日,‘日短’就是‘昼短’,一年之中,‘冬至’日昼最短了!”
“哈哈,宵就是夜,‘宵中’就是‘夜中’。‘日中’与‘宵中’说的就是‘春分’和‘秋分’日昼夜平分的现象;‘永’就是长,‘日永’说的就是‘夏至’日昼最长的现象!”终于揭开了这两组密码所隐藏的奥秘,杞敕兴致高昂。
“星鸟、星火、星虚、星昴这四者所指,应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四个特殊的日子所特有的征兆,也是古人判断这四个日子的依据;既然与星有关,鸟、火、虚、昴很可能指某些星象!”
“不过,老夫子还没有教我星象的知识,明天倒是可以问问准夫子。”
实际上,“敬授民时”这一段在整篇《尧典》中最是复杂、蕴含信息也最多。
例如,“鸟兽孳尾”、“鸟兽希革”、“鸟兽毛毨”、“鸟兽氄毛”,不足两百字的文段却四次提到“鸟兽”,说明帝尧的时代,虽然已有农耕,但狩猎依然是先民食物来源的重要一环。而且,狩猎不仅提供了食物,从“革”、“毛”来看,也是重要的衣物来源。
而下面这一段,则让杞敕迷惑了两世: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佥曰:“于!鲧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岳曰:“异哉!试可乃已。”
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之所以说迷惑两世,是杞敕前世阅读过《太史公书》。《太史公书》第一篇《五帝本纪》就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全录《尧典》其文。
迷惑的源头是:帝尧既然知道鲧为人“负命毁族”,为何会最后还是将“治理洪水”——这件最为重要的事交给了鲧。难道是因为群臣一致的举荐吗?
首先,帝尧对鲧的评价是“负命毁族”,遍查史料,找不到鲧治水之前有“负命毁族”之举。群臣的一致举荐,也从侧面证明鲧确实是有才能的,甚至是当时最有才能的人。也就是说,“负命毁族”不过是帝尧的托词,目的是不想让鲧接受这个“担子”。但世事难料,当这句托词成为了“事实”,也就成了印证帝尧先见之明的依据。
帝尧不想让鲧接受这个“担子”,或许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担心鲧功高盖主,也就是为了压制他;二是怕鲧完成不了这件差事,是在保护他。结果是“九年,绩用弗成”、“殛于羽山”,鲧确实完成不了这件差事、也因此被流放。
若依结果推断缘由,则帝尧是为了保护鲧。那么,帝尧为什么要保护鲧?
据《夏本纪》载:“鲧之父曰帝颛顼”;《五帝本纪》载:帝尧父为帝喾,“帝喾于颛顼为族子”。也就是说,帝喾是颛顼的亲堂侄,鲧于帝尧非叔即伯。
帝尧保护鲧,不仅因为血缘,更重要是的帝尧准备将帝位传给鲧。第一,鲧是当时最有才能的人,也就是黄帝一系最杰出的继承者;第二,帝尧也说了自己的儿子朱启明“嚣讼”,不堪大任。事实也说明即使不是鲧继承帝位,帝尧也没有将帝位传给儿子,或者说帝尧的儿子没能担起这个“担子”。
那么,“大臣们”为什么要“同心协力”地将这副担子安在鲧肩上呢?杞敕猜想:洪水太大,“怀山襄陵”,山与陵都岌岌可危,可见洪水已超出了当时人力物力的极限,没有人有把握可以治理好洪水,甚至没有人觉得洪水能够得到治理;这也是帝尧为鲧极力推脱这个差事的原因。
但洪水还是要治理的,即使是无用的治理,所以大臣们众口一词,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给了鲧。为什么是鲧,因为鲧的能力闻名诸侯;而且鲧是黄帝后裔,帝族身在其位,就有对天下的责任,这无可厚非。
前面也说过尧的嗣子朱启明,成事不足。“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尧年老之后,才“找到”“侧陋”的舜,这多少有些无奈。
舜将他的竞争对手鲧流放羽山,登上了帝位。
戏剧性的是,洪水退了。
治理洪水的功劳落到了时官——鲧的儿子——禹身上。鲧因为洪水被流放,无缘帝位,他的儿子禹却因为洪水捡了一个天大的功劳,之后登上帝位。
真可谓:命里有时终须有。
当然,这些推断都是杞敕从阴谋论的角度揣度他人。但,不是有人说过,“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他人”?
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是像“尚书”所夸“五帝禅让”呢,还是如“竹书”所污“舜囚尧,禹放舜”呢?这些都太久远了,难以考证。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杞敕唯谨守偏听则废、全听则明的原则。
在杞敕看来,第一:尧、舜、禹的功绩大概是有的;第二:禅让是不大可能的。
为什么肯定他们有功绩呢?太史公喜欢以先祖之功牵附后人国运,叙殷祖则至于契,曰“契佐禹治水有功”;述周祖则至于后稷,后稷在尧舜时为农师。证明在当时“浩浩怀山襄陵之洪水”时期,确实涌现了一批贤人:禹、皋陶、伯夷、契、后稷、益等,“平定洪水”、为人族立下了大功。所以,尧舜禹作为“抗灾”的领导者、乃至一线参与者,其功绩可以想见。
为什么说禅让不可能呢?根据《五帝本纪》,除黄帝外,其余四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都是黄帝的后裔。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帝尧是黄帝的玄孙,帝舜是黄帝的七世孙,大禹也是黄帝的玄孙。这种族内禅让,成色太差;此外,不妨借鉴“三国”时期的两次禅让“汉献帝禅让给曹丕、曹奂禅让给司马炎”,就可以理解禅让的实质——逼宫;何况在部落时代,一个“以武服人”最为极端的时代?“以德配位”之说犹为可笑。
此外,“以武服人”难道很见不得人吗?杞敕认为,在中央集权之前的年代——人类最漫长的一段时期,“以武服人”实乃铁律。成吉思汗难道是依靠修德行,让敌人将一顶顶王冠送到他头上的吗?以智谋和武力一统草原,难道有负他的威名吗?仁恕能够服人,勇武难道不行?德仅能让人心服口服,武更能让人的身体臣服!
“禅让”,有人给他们披上了这一层道德外衣,将他们本就自然的作为,粉饰地矫揉造作。有些人膜拜在这层绚丽的外衣下,成了外衣的信徒;有些人察觉了这“绚丽”的虚假,扒开了外衣,窥见了里衣的朴实;还有些人目睹别人扒开了假衣,却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看清楚里衣。于是,这些人迫不及待地羞恼了,像脱缰的疯狗一样,要将他们的里衣也撕下来,说,“他们是不穿衣服的人”。
杞敕自认为是幸运的,因为在先人扒开那“绚丽的外衣”后,自己有理智与耐心看清这“朴实的里衣”;所以没有与第一类人一道臣服于一件虚假的外衣,也没有与第三类人一道去羞辱他们的里衣。
那么伪造这件外衣的人呢?其心如何尚不可知,其行却着实令人生厌。
索性,杞敕不是道德家,也无意去考证这其中的曲折。无论手上这卷书是真是假,或者准确地说,有几分真、有几分假,都无妨于杞敕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所谓“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开卷有益”即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