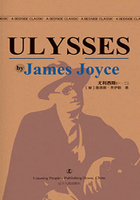近一个时期,毛泽东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均以中央或军委的名义,唯独给陈、粟的电报则全部署名“毛泽东”,并且必签上四个粗重的“A”,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华野西兵团渡河南下。由此,足见毛泽东的决心与焦急。
陕北葭县朱官寨1847年8月30日
“我没有病!”
一声怒吼从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传出来。
任弼时正朝窑洞走来,闻声急步进屋。
毛泽东怒气冲冲,面孔和脖子涨得通红。
保健医生手里拿着药物,站在一旁委屈得不知所措。
任弼时把跟镜摘下来擦着,示意医生悄悄退出去。
“史琳同志,”毛泽东头也不回地站在地图前,“给陈毅、粟裕的电报发出去没有?”
“已经发出了。我想,他们很快会有动作的。”任弼时戴上眼镜。
毛泽东“唔”了一声,余气来消:“华野迟迟不动,刘邓势必危难重重!你来看……”
毛泽东似乎使出举钢钎的气力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刚指向地图上的中原地域,笔却“叭”地落在地上。
任弼时抢先躬身捡起铅笔,递给毛泽东,心头倏地一阵酸楚。
油灯下,毛泽东的手肿得像个馒头。
撤离延安五个多月了,毛泽东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加之陕北今年罕见的天灾和频繁的战事,粮食物品奇缺,毛泽东和战士们一样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极度的疲劳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毛泽东浑身浮肿,十分虚弱。前几天,任弼时忍痛将自己的坐骑杀了,炖了几锅肉,那也只能暂解腹中之饥,解不了毛泽东心头的沉重思虑。
自从刘邓挥师南下,毛泽东无一天不在惦记他们。凡有刘邓电报来,无论白天夜晚,必亲自处理。为保证大军南下顺利,他令陈赓率部渡过黄河之后,又几次电催陈、粟南下豫皖苏钳制敌人,以减轻刘邓的压力。然而陈、粟至今未动。前不久,刘邓来电告急:国民党数十个旅形成堵截包围态势,企图将我围歼于进军途中。毛泽东忧心如焚,一连数日几乎是站在地图前度过的。刚才,他又一次吃力地拿起笔,给陈毅、粟裕拟了一封电文:
陈、粟:
二十九午电悉。
你们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最近几天又将注意力放在胶东,其实目前中心环节是在陇海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5军、57师,攻占一切薄弱据点直接援助刘、邓。我们对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20多天毫无积极行动,你们亦未严令督促,十分感觉焦急。为此问题,军委多次指示未见具体答复。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毛泽东
30日19时
措辞是严厉的。
近一个时期,毛泽东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均以中央或军委的名义,唯独给陈、粟的电报则全部署名“毛泽东”,并且必签上四个粗重的“A”,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华野西兵团渡河南下。由此,足见毛泽东的决心与焦急。
任弼时刚才说已发出的就是这封电报。任弼时转身去落实,毛泽东又回到地图前研究敌我形势。他想在地图上做标记,几次拿起铅笔又几次掉到地上。这时医生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于是他才恼怒起来。
“唔。我不该对医生发脾气。他也是好心。”毛泽东接过铅笔,摇摇头:“可他不该打扰我,他根本不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任弼时想安慰一下毛泽东,又知此种情势岂能一个“安”字了得,只好将说过的话又重复一遍:“主席,山东战场一直形势紧张,陈、粟迟迟未动必定是有困难。我想,他们接到这封电报。一定会拿出行动的。”
毛泽东的眉头依然没有松开:“但愿如此。”
周恩来走进窑洞,浓眉飞扬:“主席,刘邓传好消息来了!”
“哦?快念!”毛泽东迎上几步,却接过电报:“不,让我自己来看。”
各首长并报军委,……
(一)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任务。敌人追剿计划完全失败。今后任务,是全心全意的,义无返顾的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可能点。
(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过程,……我们应切戒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三)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把握,……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刘邓
未卅
毛泽东吸吮着嘴唇,眉头渐渐舒展开,灰肿的脸上也泛起红润。他慢慢地将电报递给任弼时,慢慢地伸手从兜里掏出香烟,慢慢地点燃火,深吸了一口,猛地吐出:
“我们终于熬出来了!”
周恩来深解毛泽东语中含意,接道:“是的。主席,自古谁得中原,谁得天下嘛!”
毛泽东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哈哈大笑。
周恩来说:“主席,刘邓进入大别山,各个战场都活了。不过蒋介石是不会甘心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他一定会拼上性命‘围剿’。”
毛泽东点点头:“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周恩来的目光透着沉重:“只是这样一来,刘邓会很困难,他们背得太重了。”
毛泽东移步到门口,撩开门帘,望了一眼满天的星斗:“夜黑了,星星才更亮。困难大,背得多,刘邓就更光荣。他们的行动是英勇的行动!”
毛泽东转回身:“恩来同志,请转告周师傅,说毛泽东饿了,快煮些黑豆送来。我要打通宵。”
“主席,连着几天你已经很疲劳。我们担心你的身体……”周恩来婉言劝阻。
毛泽东微皱眉头:“怎么?你也讲我的身体如何如何?刚才医生捣乱,说我患了帕金森氏综合症。我告诉他,我毛泽东是中国人,不得外国病。我没有病!”
那一夜,毛泽东窑洞里的油灯通宵未熄。
两天后,电波载着毛泽东亲手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传送到人民解放军的各个战场: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历史重重地记下了一笔: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开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河南光山北向店1947年8月31日
“过八路!过八路!”
黄鹂鸟从这个村飞到那个村,就这么叫着,叫得清脆嘹亮,叫得字正腔圆。
老人们捋着胡须说:“会飞的都是天神。前几年,‘直不岔’黑夜白日叫唤:‘打日本,杀敌、杀敌!’小日本不就投降啦?这一回;也错不了,‘过八路’,又要闹红了。’
“过八路!过八路!”
黄鹂鸟叫得更欢了,播撒下一串神奇的传说。
有人讲:“闹红的队伍是从黄河北边开来的。浩浩荡荡,有几十万人马,领头的姓刘名邓,那是个了不起的能人儿!只要一挥手,几十万兵马就能腾云驾雾,日行千里。”
说起刘邓大军连闯几大河,有一段完整的传说:
“过黄河,正逢烈日当空,波浪滔滔,水深足有千丈,河宽二三百里,眼瞅着没法子。只见刘邓吹了一口气,黄河上刹时彤云密布,转眼下起炕席大的雪片,把河面封得结结实实、平平坦坦,大队人马就从这条冰河上走过来了。
“到了汝河,前有白匪,后有追兵,河面上既无桥,也无船,那才叫千钧一发,难坏三军。刘邓沉得住气,不慌不忙从腰里掏出—个红绸包,取了一粒分水珠,往河里一丢,河水自然分成两堵墙,千军万马硬是人脚不沾泥,马蹄不带水,平平安安就过了汝河,连中央军的枪炮子弹都穿不透那两道水墙。
“队伍开到淮河更神。刘邓是个戴眼镜的人,他把眼镜摘下,往河一架,就成了座七彩桥。大军刚从桥上过完,中央军就追到河边。只见刘邓笑了一下,抽回眼镜架到鼻梁上,桥就不见于,把对岸的中央军气得干跺脚没办法……”
历代兴亡,总是伴随着许多神话般的民间传说。
传说是兴衰成败这一历史真实的预言与观照。
一首歌在大别山麓唱响:
刘邓大军真勇敢,
渡河反攻鲁西南大捷歼敌六七万。
蒋介石正在手忙脚又乱,
我们又挺进大别山。
艰苦行军20多天,
血战汝河胜利渡淮踏上大别山。
大别山好比一把剑,
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
毛主席领导如明灯,
刘邓首长亲自指挥就是指南。
同志们挺胸勇敢往前干,
解放全国胜利曙光在眼前。
曲子是《信天游》的调调,朗朗上口,刘邓大军的许多老同志至今唱起来仍然热血沸腾、珠泪涟涟。歌词是张际春在行军路上组织写的。他说这么重大的历史行动为什么不编个歌子唱—唱呢?于是就发动每个纵队都写。第l纵队的宣传干事邢岳挺灵光,膛着淮河流水,心里头一热,歌词顺口就涌出来了。
张际春听罢,击掌称好:“唱到战略进攻的点子上了,就定这首!”
渡过淮河,部队踏上迭次渐高的坡道,这首歌不胫而走,很快在10万大军中流传开来。上了大别山,总部通知在北向店做短期休整,歌声更是此起彼伏,唱得石破天惊。
随着一阵阵欢快的歌声,战士们仿佛把数十天的腥风血雨、枪林弹雨、凄风苦雨,连同中原的风尘、征战的疲劳、敌军的阻截,一起丢在淮河北岸了。
到了!终于到大别山了!
大别山的8月,虽说不上是最美的季节,然而对于来自冀鲁豫大平原的战士们,这里秀丽明媚的山光水色却令他们陶醉了。路边的池塘碧澄清澈,映着蓝的天、白的云,一群群鹅儿在水中嬉戏,拨开一池云。池塘边开满了各色各样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蓝的。远处,黛色的山峦依次铺开墨绿、翠绿、青黄。山的背阴处是茂密的松竹,山的阳面则是望不尽的梯田,就连山顶也是水田成片,泛着绿的涟漪。
见惯黄沙土丘的北方籍战士连发感慨。
但是,野战军的一大批中高级指挥员却是从这里走向革命的。有好事者企图列个名单:陈锡联、陈再道,郑国仲、陈鹤桥、肖永银……结果数不清道不尽。大别山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田间小路、崎岖山道,与他们有扯不断的情丝。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他们徘徊在残墙断壁、峭石悬崖旁,寻觅着“闹红”时留下的遗迹。掬一捧故乡红色的泥土;望一眼昔日亲手写下,虽几经风雨仍依稀可辨的大字标语——“打土豪,分田地”、“粉碎白匪围剿”、“红军必胜”……这些九死一生的汉子们头一次品尝到返乡泪水的苦涩与甘甜,一肚子话到了嘴边只剩下一句:
“大别山,我们终于回来了!”
野战军组织部部长陈鹤桥想到山上走走怀旧一番,刚出村口,见制图科的于乔和陈晓静捧着一大把鲜花,笑着从山顶跑下来。
休整了几天,姑娘们把自己收拾得换了个人似的,再不见过黄泛区和渡汝河、淮河时的狼狈。
陈晓静说:“陈部长,你看大别山的花多漂亮!”
陈鹤桥抽出一枝:“大别山到处是宝,好东西多得很。你们采那么多花干什么?”
陈晓静诡谧地眨眨眼睛:“我用它布置绘图室。于乔的那一把呀,要留着献给柴处长呢!”
“贫嘴!”于乔一下揪住陈晓静的耳朵,直到陈晓静哇哇告饶才松开手,她从衣兜里掏出一样东西:“陈部长,你说奇怪不奇怪,大别山的石头是红色的,你看……”
“是呀,陈部长,你是大别山人,你说这是为什么?”陈晓静也掏出一块红石头。
陈鹤桥的笑容消逝了:“你们问得好。大别山的石头是红色的,大别山的泥土也是红色的,因为这里面都是血,大别山人民的血!”
陈晓静感到脊背一阵瘪凉,手中的石块“啪”地落在地上:“真的?”
陈鹤桥捡起石块,抚摸着:“红军三进三出,每次转出紧接着就是国民党的‘清乡围剿’,烧光杀光,大别山就叫血给泡透了……留着它吧,记住,这是一笔血债!”
一个叫牛三保的战士扶着位瞎眼老妈妈朝这边走来,身后还跟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老人摸摸索索,斗路蹒珊。一路喋喋不休:“4连,4连指导员……”
走到陈鹤桥身边,牛三保扶住老人,说:“老妈妈,这位是我们的首长。”
“首长?……首长可是4连的?首长可是指导员?”老人挤巴着枯凹的双眼,紧紧拉住陈鹤桥的双手。
陈鹤桥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好实话实说:“老妈妈……我不是4连的人,也不是指导员。”
“那你们不是民国18年从这里出去的红军?”
“我就是那时的红军,如今又回来了。”
“那你不认识吴海?4连的指导员?”
“吴海?老妈妈,我们这儿有很多4连。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指导员叫吴海。”
“没有?不!不能啊……俺就那么一个儿子,俺吴海是红四军4连指导员,他走的时候才20岁呀!”
老人像个失望的孩子,“哇”地—声坐在地上痛哭。
于乔和陈晓静赶忙搀扶起老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老妈妈,您别难过。我们虽然不是吴海,可也和吴海一样,都是当年的红军,都是您的儿女。
陈鹤桥拉着老人的手:“老人家,现在咱红军有几百万啦。那时候吴海做4连指导员,现在咱有很多很多个4连,几千几万个吴海都回来了。您想叫吴海做啥,我们都能替您做。”
“不,俺啥也不要做,啥也不要……”老人呜咽着,满是皱纹的脸上挂着混浊的泪,半晌才憋过一口气来:“俺就要吴海回来……给俺报仇哇!……自从他走后,湾子里叫白匪民团闹惨啦,妇会的人叫那些禽兽们糟踏够了,又反绑着手投到池塘里啦!岭后松林里天天杀人,杀得没有数哇……吴海他爹也给砍死啦!我的眼珠子也叫畜牲们用竹筒子给……给拧掉啦……吴海!吴海!你要回来给娘、给你爹报仇啊……”
在场的人都忍不住了,于乔和陈晓静的手颤抖着,攥紧那块血红的石头。
陈鹤桥用衣袖擦擦泪:“老妈妈,别哭了。这仇咱们一定替你报!我正有件事要问问您,如今咱红军回来了,为什么村上除了老老小小都跑光了呢?”
老人颤颤巍巍撩开衣襟,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若与共产党照面,杀绝满门!
“这是上个月,保长逼着家家户户写下的呀。我老了,又是个瞎子,还怕啥?我是拼死在家等俺吴海,要把冤仇给他说说呀!”
陈鹤桥搀着老人说:“做得对!老妈妈,您不用怕,咱队伍多得很,往后还要往这边开,说不定您的吴海还会来呢!”
老人的腰板突然直起来,拉过身边的小女孩说:“好孩子,快,快去,去岭后叫你妈、你叔、你婶他们快回来。你就说,红军不走啦!”
小女孩呆立片刻,似乎明白了什么,一转身,像只小鹿朝山上跑去。
松林里回荡着银铃般的童音:
“红——军——不——走——啦——”
河南光山北向店1948年8月31日
茅草小屋里黑漆漆的,大白天也得点灯。
部队进入北向店后,刘伯承、邓小平就在这里住宿、办公。
刘伯承走到哪里也离不开地图,有时甚至把看地图当成一种休息消遣,无论多么紧张疲劳,只要往地图前一站,他就能气沉丹田,进入一种入定状态。似乎他面对着的不是花花绿绿、点点线线的图形,而是一片活的凸起的天地;他全身心走进去,跨过山川江河,步人广阔平原,越过小桥关隘,在山山水水之间跋涉,从满头乌发直走到一顶银丝……此刻,他正手擎一盏如豆的油灯,伫立在“大别山区形势图”前,构想着部队的进一步展开。
邓小平刚刚签署了一项作战命令,打开收音机想听听敌人的动态。他怕影响刘伯承,便把音量调到最小。
收音机里国民党的电台正在广播近几天的战事:
“……本月下旬,国军10万官兵于息县汝河、淮河一带追阻围歼共军,激战数日,战况空前,毙伤共匪无数,缴获武器颇多。目前,国军正在节节进击,共匪已作分股逃窜。据可靠消息来源,此役中,国军曾击毙一名身材高大且戴眼镜之匪徒,经多方证实,此人必系共匪头目刘伯承无疑……”
“哈!邓政委。”刘伯承眼睛不好,耳朵却很灵。他放下油灯,回头对邓小平笑道:“我这是第几次被击毙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