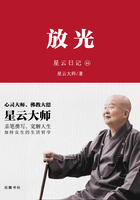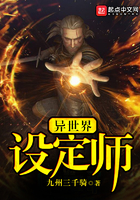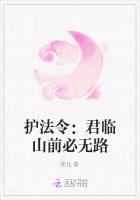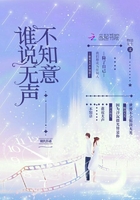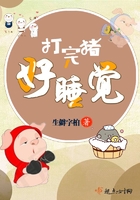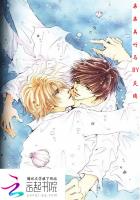就拿孙悟空来举例吧,《西游记》上说:
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四面更无树木遮阴,左右倒有芝兰相衬。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
这里讲得很清楚,孙悟空不过是一块吸取日月之精华的石头孕育而成的,虽然有点小能耐,但说到出身,不但和金蝉长老转世的唐僧没法比,就是他的师弟猪八戒和沙僧,也是天蓬元帅和卷帘将军转世,比起石猴的地位,那可高出不是一点。
妖精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信仰方面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关于妖精的认识,实际上是自然崇拜的一部分。古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有灵魂的,看成活物;活物只要修炼时间长了,当然会成精,孟子说得好:“人皆可以为尧舜。”既然人能够成为圣人,物为什么不可以成精呢?
所以,在古人眼里,精灵是无处不在的。《庄子·达生》上说:
沈有履,灶有髻;户内有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陪阿鲑蠪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
山川湖泊以至门前屋后,到处都有精灵出没。
《管子》也介绍了很多精灵,比《庄子》说得细,也更有趣。下面列举一些:
在断水的沼泽地里,时间长了就会生出一种奇怪的小人,名字叫庆忌。庆忌身高四寸,穿着黄衫、戴着黄帽子,骑着小马驹奔来奔去,只要能喊出他的名字,他就会听你的话,下水为你去捕鱼。
木之精叫做彭侯,长得像条黑狗,没有尾巴,可以杀了吃掉。
玉之精叫做岱委,长得像美女,穿着黑衣,只要用桃木匕首刺她,并且喊她的名字,就能抓住她。
水之精叫做罔象,长得像个小孩,黑皮肤,红眼睛,大耳朵,长爪子,也可以抓来吃了。
坟墓之精叫做狼鬼,喜欢向人挑衅,用桃木做的箭射他,并且脱下鞋子和他搏斗,肯定能抓住他。
……
妖精固然很多,但是“妖不胜德”,在儒生们看来,虽然草、木、鸟、兽都有性有灵,但是人得性之正而鸟兽得性之偏,鸟兽的灵渺小而人的灵广大;妖精先天就不如人,修炼的水平再高,也不能跟人平起平坐。一般情况下,人类对于抓住的精怪,是能吃的就吃掉,不能吃的至少也要杀掉,丝毫不考虑他们的修炼如何辛苦。
孔子可能是中国最早吃妖精的人。据说孔子在春秋各国狼狈奔走时,曾经遇到一个怪物,子路与他斗了很久,发现是条九尺长的鲤鱼。众人惊惧,倒是孔老二胆大,说:
“世上的万物,活得久了,往往要成精。这种怪物,杀了就杀了,也没什么稀奇。”
于是孔门七十二弟子就分吃了这条超级至尊鲤鱼精,个个吃得神清气爽,怀才不遇的郁闷一扫而空。既然圣人都敢吃,那普通老百姓还有什么忌讳,所以个个吃起妖精来,都是争先恐后。
至于官府,为了维护民之父母的窗口形象,虽然不主张吃妖精,但遵循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导,也根本就没把妖精当一回事。
春秋时,有一种叫做“爰居”的海鸟聚集在鲁国都城的东门外,三天没有散去,当时执掌鲁国政权的臧文仲是个没主意的人,马上下令国人都来祭祀海鸟。展禽(就是那位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劝说:
“祭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咱们的宪法上说要‘慎制祀’,不是什么玩意儿都有资格吃冷猪肉的。能给国家立功的,得过劳动奖章的,享受专家津贴的,再加上日月星辰和名山大川,这些才有资格上祭祀名单。几只海鸟对国家、社会毫无贡献,怎么受得起我们这样有身分的人叩头呢?”
不仅如此,在周代,还专门有一些官员收拾妖精,《周礼》中就记载了这么几条:
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凡驱蛊,则令之、比之。(《秋官司寇·庶氏》)
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驱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杀其神,则以牡午贯象齿而沈之,则其神死,渊为陵。(《秋官司寇·壶涿氏》)
庭氏,掌射国中之夭鸟。若不见其鸟兽,则以救日之弓与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则以大阴之弓与枉矢射之(《秋官司寇·庭氏》)
不过,这些官员的级别都比较低,除妖活动的规模也小得多。由此可见,官方对于精灵并不怎么在意。
在妖精面前,人类始终有根深蒂固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所以,对妖精的歧视非常严重。即便是修炼得比较好的狐狸,在人类面前也显得低人一等。比如有个故事说,一个品行不端的读书人晚上散步,看到河边有个漂亮MM,估计是个狐仙,他顿起色心,上前搭讪,而上手之后却又另觅新欢。狐仙找上门来论理,这家伙竟然说:
“老祖宗们是说过不能始乱终弃这样的训诫,但这些话只是用来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人和狐仙也就是互相玩玩,我们人类从不跟狐仙谈道德问题。”
人类之所以在妖精面前拥有优越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妖精尽管修炼水平高,但总多少保留了原来的形态特点。即便有些妖精能幻化为人形,一不小心,还不免露出马脚。
一个故事说,三国魏国的景初年间,阳城县一个县吏家里老是发生怪事。经常听到有人拍手互相呼叫,想找原因,又什么古怪都找不到。一天晚上,县吏的母亲晚上干活累了,上床打个盹。过了一会儿,她听到灶台边有人喊道:
“文约,怎么看不见你?”
脑袋下面有人答应说:
“我被枕住了,不能过去!你到我这儿来!”
到了天亮一看,原来是盛饭用的铲子躺在床边。于是把它们集中起来烧掉,妖精也就灭绝了。
又一个故事说,唐朝天宝年间,长安一个叫王薰的请了几位朋友喝酒,突然烛影下出现一只黑乎乎、毛茸茸的手,门外还有人说话:
“几位喝得很高兴嘛,能给我点肉吃吃吗?”
王薰吓得半死,赶紧拿了块红烧肉放在他掌中,于是手就缩回去了。过了一会,那手又伸出来讨肉。如此一来二去好几回,王薰和朋友的胆子逐渐大起来,而且觉得这妖精贪得无厌,烦。于是,当手再伸出来时,王薰手起刀落,一刀斩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黑手滚落在地,转眼变成一截驴蹄子。第二天,王薰等人沿着血迹寻找,在邻居家发现了一只少了条腿的驴子,于是就杀了他分而食之。
尽管修炼艰难,精怪还是在逐渐人化。早期的精怪,清一色的歪瓜劣枣,最好的也就是人首蛇身或人首马身什么的,像庆忌这样模样周正的极其罕见。到后来,精怪的修炼本事越来越高,幻化人形已经不是什么难事,有些在官宦人家住得比较长的精怪,还能吟诗谈风月。
有个叫做元无有的人外出春游,遇到大雨,在一间荒废的屋子里避雨,忽然发现屋子里有几个人在谈论风月,说是要做诗叙述自己生平,文辞极为雅致。分别是:
齐纨鲁缟如霜雪,嘹亮高声为子发。
家贫长夜清会时,辉煌灯烛我能持。
清冷之泉俟朝汲,桑绠相牵常出入。
爨薪贮水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
老元素来有点小资情调,也并不特别奇怪。那几位也没有发现元无有,一边吟诗,一边互相吹捧,说是阮籍的《咏怀》也不过如此。等到天亮,几位诗人没了踪影,元无有四处寻找,只在屋子里发现旧杵、烛台、水桶、破锅四样东西,在仔细回味那四位的诗,原来他们说的就是自己。
妖精问题,在中国并不是简单的信仰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人们认为精怪是对自然、社会的正常秩序背叛或超越的结果。所以有人认为,在特殊情况下,人也有变成妖精的可能。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阐发,人变成妖精的故事并不多见。早期人们认为精怪本身是自然、社会失序的特殊结果,它们并不会害人,最多只是灾害的先兆。比如《山海经》里介绍了很多异禽异兽,它们都老老实实地呆在山上、岛上,可是人要是多事到山上、岛上乱跑,见到它们就会出事。比如,令丘山上有一种鸟,叫做顒,长得像猫头鹰,人的脸,四只眼睛,只要有人看到它,就会天下大旱。鹿台山上有一种鸟叫做凫徯,样子像公鸡,长着一张人脸,只要有人看到他,就会爆发战争。
尽管社会对妖精的认识不断变化,但始终认为它们属于异端,至少也是异端的表现形式。清除异端,就意味着秩序的恢复。随着古代社会走向成熟,社会的精神控制也逐渐精致,消灭异端,也不是只有将妖精杀掉这一条途径。妖精们也可以通过道德的修养、身体的修炼,逐步改造自己,成为社会能够接受的新新妖精。比如狐狸,修炼之后可以成狐精,可以幻化为人形,再继续修炼,同时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名列仙籍,弄个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样,神、鬼、人、妖的转化通道就完全打通了。
捉鬼队
世界上有多少鬼?
关于这个问题,古人好像没怎么研究过。
从理论上说,鬼应该比人多,因为鬼不会死,而人会不断地死去加入到鬼魂的队伍中来。虽然有些鬼能升为神,但是再官僚主义、鬼浮于事,能够提干的鬼终究是少数,绝大多数的还是平民鬼。
有一个故事也许能从侧面反映鬼的数量。
宋朝有位姓史的中散大夫,年纪大了,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回到家乡临安。有一天,史大夫到街上闲逛,看到有一位卖烤鸭师傅,特别像自己当年雇佣的厨子王立。不过王立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死了。史老先生正奇怪,那位烤鸭师傅突然拜倒在他面前:
“老主子,没想到在这里遇见您。”还端上一只烤鸭要孝敬主子。
史老先生意识到自己真是遇见鬼了,好在这王立也不像有什么歹意,史老先生说:
“你已经是鬼了,怎么大白天的还在首都乱转悠?”
王立说:“您有所不知,现在临安城里,有三成的‘人’其实都是我辈,有国家公务员、有和尚、有道士、有商人、有妓女,反正各色‘人’等都有。他们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只是一般不害人,人也不能认出他们来。”
这么多的鬼和人杂处,不生出事端是不可能的。即便这些鬼老实本分,人也不会放过他们,因为按照古人的观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果是自家祖先,逢年过节的供点吃喝,烧点纸钱也没什么,其他的孤魂野鬼,就算杀了,良心上也不会受到什么谴责。毕竟是阴阳殊途。假如有些鬼整天吵吵嚷嚷,闹得凡人不得安生,对于这种惹事的鬼,人们更是要痛下杀手的。
杀鬼、驱鬼,按照朴实点的想法,人们首先想到鬼的天敌。比如《神异经》上说,有一个身高七丈的巨人,最喜欢吃鬼,每天早上要吃三千个鬼,晚上要吃三百个鬼。但是这个说法太过荒谬,如果照这样吃下去,全天下的鬼恐怕还不够他吃。而且,这位巨人似乎从不出去抓鬼,难道所有的鬼都会贱到排队去送死?
还有一种方法是吃药。传说有一种杀鬼药,类似现在的肠虫清,如果有人被鬼附体,吃这种药基本上能够解决。比如唐朝天宝年间,渤海地区有个姓高的书生,一直犯胸口疼,总也不能痊愈,就请来一位名医诊治。医生仔细瞧了瞧,说是有鬼躲在他胸口里,开了一帖药给他吃下去。高书生不久就觉得胸口有东西在乱动,然后吐出一个小人,开始只有一点点大,很快就长到几尺长。高书生本想抓住这个鬼质问,可是他马上就逃掉了。高书生的病也就好了。
医生毕竟不是对付鬼的专业人士,而且有这位名医本事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更实际的方法是请专业巫师来驱鬼、杀鬼。巫师捉鬼至少从商朝就开始了,在西周青铜器《禽簋》的铭文中就有对驱鬼仪式的介绍。
在所有的巫师中,最著名的就是周朝的皇家御用世袭巫师——方相氏。
汉赋里介绍了方相氏在皇宫里驱鬼的全程实况。
驱鬼是在冬天进行的,先要在宫门和城门口杀牛羊祭祀,以抵御阴气。选取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太监一百二十名,然后请一个巫师做带头大哥,这个巫师称为方相氏。
方相氏身披熊皮,头戴面具。这个面具也有讲究,是黄金打造的,有四个眼睛。方相氏身上穿着黑衣红裙子,一手拿着戈,一手拿着盾,率领这一百二十个小太监在宫殿里驱鬼。他们一边做出各种砍杀的动作,还要一边念叨:各种鬼怪们听好了,我们已经请来了你们的天敌,有十二天神,专门对付你们。抓到你们,要开肠破肚,零敲碎割,识相的就赶紧滚蛋,否则成了天神的口粮,可大大不妥。
这样在宫殿里边喊边砍,来回三趟,方相氏才举着火炬出来,门外有卫兵接着火炬,送出宫门,然后就像举行火炬接力仪式,一直送到河边,把火炬扔进水里,象征着鬼怪也被扔进水里流走。
碰到一些特殊情况,像国君去世,也需要驱鬼,方相氏就要在送葬的灵柩前开路,沿途驱逐恶鬼。到了墓地,方相氏还要进入墓道,攻击墓道里的各种鬼怪。
就普通人而言,不可能办得起规模这么盛大的活动。况且,以普通人家的条件,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鬼需要驱赶。何况像方相氏这种有级别、有职称的国家首席巫师,即便有钱也请不来。所以,一般家庭的驱鬼活动,都是采用的浓缩普及版,请本村的民办巫师来处理。如果碰到个别的没什么法力的鬼,不劳巫师出马,自己动手也能把鬼给收拾了。在秦简《日书》中,就记载了不少家庭驱鬼的仪式,都是既简便又实用。
以上的这些方法,或者需要金钱,或者需要专业知识,但人生也有涯,而鬼生也无涯,随着人们生活世界的不断丰富,鬼的种类越来越多,以上这些消耗时间和精力的方法不能与时俱进,逐渐被人们抛弃,而代之以门神。
门神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防止鬼怪骚扰,保护家庭平安。
最早的门神是神荼和郁垒。这哥俩住在东海的度朔山上,山上有一颗大桃树,在树的东北方有一个大洞,据说鬼魂都是从这里出入的。神荼和郁垒整天守在这棵树旁,碰到为非作歹的鬼,哥俩就抓起来去喂老虎。所以,除夕时分。人们经常在在门口立一个桃木做的假人,再画上神荼和郁垒的像,贴在大门上。有时候,还要画只老虎,在古人眼里,老虎是百兽之长,是阳物,也是鬼的天敌。
神荼和郁垒从汉代开始作为门神,把持了近千年,到唐宋时期,新的门神开始崛起,这就是钟馗。钟馗据说是唐玄宗时人,因为考武举人落第,没脸回乡,一怒自杀,唐玄宗觉得此人有骨气,是个爷们,就追认他为进士,赐袍子葬了他。钟馗为了表示感激,发愿为皇上除去天下的恶鬼。这个故事流传甚广,钟馗声誉渐起,取代了神荼和郁垒,成为新一代门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地区,又有新的门神不断涌现,著名的如秦琼、尉迟恭、岳飞、赵云、赵公明、孙膑、庞涓等。这时的门神,已经不仅仅是驱鬼的作用,而具有了浓郁的装饰意味。
依靠门神驱鬼,其实是被动的方法,虽然比请巫师捉鬼方便,但是效率显然不如巫师。尤其是临时出现的鬼怪骚扰,还是要请巫师出马。当然,佛教、道教盛行之后,道士、和尚驱鬼的也很多。而且由专业人士驱鬼,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互动色彩很强。所以尽管有门神,但是驱鬼的有效需求总是比较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