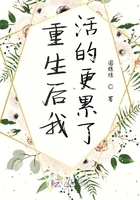“你都不想再问问你魏范哥的事么?”刘母终于耐不住困惑,痛心地问。
这话,就像是勾人魂魄的无常鬼,只在瞬间,就使刘意冷汗直冒、灵魂出窍。
“还有什么可问的呢?”刘意背着身,止住步;然而又有些热泪了。
“这叫什么话?他好歹也是带着你从小玩到大的,现在突然…突然就这么冒失地去了,你怎么能毫不表示关心呢?”说到这儿,刘母又不禁回想起刚刚在医院抱着魏范尸体哭得死去活来的黄阿姨及其一大家子人,眼圈也又红了。
“还有什么可关心的呢?”刘意的眼泪已止不住地滴落下。
“唉,你这孩子,”刘母摇摇头,长叹一声说,“我想你心里一定比我更难过吧?何必都要憋在心里呢?但魏范这孩子到底该有多不懂事?不过因为暂时没找着工作家里人说他两句罢了,心里竟就承受不住了!他也不想想他这一去还让他妈怎么活?这不彻底断了他们一大家的希望吗?”说到这儿,刘母也又流下泪来。
刘意沉默不语。在某个瞬间他便收住情绪,继续向卧室里赶。
“你还先站着罢。说完了别人也该谈谈你自己的事了。”刘母渐渐转换过情绪,一脸正色道。
刘意这才想起原来今天还有另一件大事需要自己去面对。
“是成绩的事吧?”他终于回转过头,笑着反问。
“哼,原来你也还记得!我早前查过了,才省8000名,差得让人简直说不出话!这…这跟你当年刘睿哥的前80名完全无法比拟!”刘母的愤怒隐藏在正当的比较中、威严的神色下。
“嗯,我知道。”刘意微点着头,语气淡漠到好像此事是发生在火星球上似的。
刘母原本还想稍克制住自己的怒火,跟刘意好好谈谈;可现今见着他又是这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便再忍控不住,直接指着他数落道:“你这是什么态度?无所谓?考得这么差还好意思无所谓?我看你真是不知所谓!你说你这样对得起我们十几年来给你的培育么?对得起器重你的那些老师和长辈么?对得起你自己这么些年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么?你…你自己说说看!”刘母气得直接将手上的浴巾丢掷于地,整个人也顺势退坐到身后的沙发上;眼中再度泛满泪光。
刘意似乎并不怎么急于答话。他弯腰捡起被弃在地上的洁白浴巾,轻轻抖尽其上的灰尘,并将它叠好放回至沙发上;然后,继续低头站在一旁,替刘母承担着自己的羞愧之情。
刘母见他这般谦恭,心中才略略感到宽慰。她虽继续诲人不倦,但语气已明显由怒转哀了:“唉,还该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你这让我今后在亲戚朋友面前怎么抬起头?我这…我这脸面也都让你给丢尽了!”
刘意听后,百感交集;然而一言不发。
刘母用手尽力撑住前额,连叹了几口气,又泪看了刘意一眼,最后,只得挥挥手。
刘意会意,掉头便走。
随后的时间则无可避免地印证了刘母先前的担忧:亲戚朋友们接踵而至的电话让刘母应接不暇:
有的直截了当:哎呀,看你平时在你儿子身上可是花费了不少功夫,刘意那孩子又是那么得聪明懂事,可怎么…怎么到最后就考出这么个差强人意的分数?真是可惜啊可惜!
有的绵里藏针:唉呀,我们为人父母的终究还是要实事求是些,那中华大学也是人人都能考上的?所以我说,像你儿子这种成绩已经算是不错啦,你还奢求什么?
有的实在奉承:嗯,不错不错。果然关键还得看是有什么样的父亲,所谓虎父无犬子嘛!哦,对了,嫂夫人千万记得要替我向你家的老刘招呼一声啊!我真有要紧事找他!
有的真心宽慰:呦,这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赶紧办桌酒席庆祝一番呐!我家那猴孩子就是当年不努力,所以连个大学都没考上,你儿子既然考上了,那还不该让大家伙都知道知道?
刘母时而与之同怒,时而被迫赔笑,脸色也是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但内心却终究只有一种万分抽象而又无比强烈的感受:脸面没完全撑起来。或者说,简直都有些丢掉的危险了。
不知何时,刘父已带着一身的酒气与一脸的倦容回来了。刘母侧倚在床头,正是满腔忿怨无处泄,恰逢迎面有人来,忙指着刘父,将战火挑起:
“你儿子都已经无可救药了,你还成天在外喝死酒!挣臭钱!看看他这次高考才几分?!”
刘父提提裤带,抖擞怒火,正准备像往常一样应战;忽然腰间手机响起,他也只得先接起电话。一听声音便知是刘伯。待刘伯知晓刘意的成绩后,只平淡地评价了句:不怎么行啊。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刘父挂掉电话后,只狠狠问:“小东西现在在哪儿?”
于是乎,就这样,战火被迫转移。刘意的卧室门被“砰”的一脚踢开,声响震耳;顶上灯被“啪”的一下按启,光亮刺眼。
人在寂静的黑夜里呆久了,乍一听闹声、一见强光,会是件很痛苦的事。此时的刘意,就像只畏声又畏光的小动物,蜷缩在角落,深埋于被单,极不情愿被打扰。
可再不情愿也不过就是你个人的意愿;而区区杳渺的个人意愿在强大的父母之命面前向来也算不得什么。刘父边叫嚷着边将刘意从睡梦中摇晃起。
“你…你给老子起来!我…我有话要问你!”刘父翻着眼,点着手,踉跄着脚步,错乱着思绪。
刘意不得不强行将眼睁开,迷朦中却只见:一个庞大的身躯,一张煞白的脸,一双杀人的眼。
一旁的刘母还在不停地说着些什么。
刘意瞬间感到某种恐惧。这是种无可摆脱的原始恐惧——就像在荒郊寒夜里独自奔走却又不慎坠入破落古寺中的湿滑圆井内一般,周围已遍是嶙峋白骨,井外还有成群嗜血残狼。除了在原地绝望地等待着无望的救援,还能怎样呢。
但这一次,不知是因为头晕脑涨还是下意识里觉得自己今天已经成年更或是因为魏范哥的自杀,竟导致刘意从来压抑着的情绪彻底爆发出来——和对待先前刘母的沉默态度不同,他对付此时刘父的就是:菊st Beat It。
“我不跟醉酒的人展开任何有内涵的对话!您现在连方向盘都把不住,还能指望把我教导到哪儿去?”刘意索性直起身说。
“你…你说什么?”刘父虽已产生些幻听,但还是讶异于自己所听到的这句话。他实在无法相信一向乖巧听话的儿子竟会放肆大胆到如此。
清醒的刘母也觉得自己似产生了某种幻觉。
“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您平时干嘛去了?太阳高高照时我看不见您,周末放假时我也看不见您,可一到深夜,一到我熟睡时,您便带着那标志性的酒臭味来找我谈话了,内容前言不搭后语,逻辑蛮横霸道无理,我还得昧着本心真心良心表示赞同理解支持?!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也是大人了,我有权拒绝您不当的教诲,更有权发出只属于我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