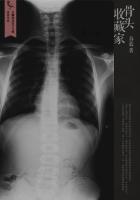二爷叹了口气说:“哎,自从听了白牡丹的《三拉房》《小二姐做梦》,你说气人不?我每天夜里就做起梦来,起初我没介意,可是梦越做越玄,现在我简直有点害怕啦。”
“什么梦,这吗可怕?”我不禁问道。
“那是在庙会的第四天夜里,我梦到你二婶成了演员啦,在戏台上演小二姐做梦,唱的可好啦,唱着唱着,却成了真的,你说奇怪不?新郎竟然是我。”
“呜哇号声的,就是走不到你二婶的家。你二婶在家等啊等啊,再后来就急的哭起来,听到你二婶的哭声,我也很着急,就吹促轿夫和吹鼓手快走,但是,就是走不到。情急之下我就急醒啦“哦,还真有点意思哩,后来呢?”我说。
二爷接着说:“从那天起,我便天天做梦。第二天的梦就更奇啦,我梦见你二婶一夜都没睡,起初在灯下纳鞋底,一针一针的纳,那针脚纳得那个密啊,就甭提啦,一直纳到半夜,才躺下睡觉,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后来就搂着小羔哭。"
“怎么?你梦见二婶纳鞋底啦?”我忽然想起上星期六小羔说的话,计算了一下时间,也许就在同一夜晚吧。
于是,就跺了一下二爷高兴的说:“还真的奇怪哩。”于是,我便把小羔的话告诉给二爷。二爷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我相信我的梦就是真的,所以我也更加痛苦和不安。”
“这还不算奇怪,还有更玄的哩,起初,你二婶搂着小羔一边哭,一边用手抚摸小羔的小光腚,摸着摸着小羔就睡着了。你二婶就自己抚摸起自己来,随着双手的抚摸和揉搓整个白嫩嫩的身体便上下蠕动起来,两只鼓膨膨的乳房也更加挺拔,随着急促的呼吸胸脯上下起伏着……”
“看到你二婶如火如焚的样子,我感到浑身发热,心里十分惊慌和羞愧,呀,怎么看起人家女人睡觉来啦,这么一惊也就醒啦。”
二爷不再说话,我却听得入了迷,笑着追问道:“还有呢?”
“第三天夜晚,是你大娘给我提亲,女方就是你二婶,明明你二婶心里很乐意,可就是不吐口。
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害怕。’
你大娘问她:‘怕什么?’她说:‘怕街坊邻居笑话。怕死鬼丈夫不答应,怕小羔长大了好说不好听。’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哭得那个伤心啊,就甭提啦,这些事就跟在眼前一样,我再也忍不住,也大哭起来,我哭啊哭啊,就哭醒啦……
醒来还抽泣成一个呢,我知道这也是真的,不信你去问问你二婶,她肯定是这样。”
后来,我叫我妈去问二婶,结果,真的是一模一样。在当时,我却有点不相信,心想:这不过是二爷的猜想罢了,于是就说:“找个人介绍介绍不行吗?她不一定不同意,因为寡妇改嫁,这几年已是十分平常的事啦。”
我接着说:“你这个梦不一定做得准,有人说做梦常常跟实际相反哩。找个人透透吧。”
“透透也白透,这个我清楚,别说你二婶没那个胆量。我也没那个胆量,你想想看,咱村谁敢打破过本村人跟本村人结婚这个风俗,更何况不是一辈,所以我对你二婶只能有那个情,决不能有那个意。”
“本村人怎么啦,又不同姓,婚姻法规定只要出五服就可以结婚。”我有点气愤的说。二爷不再说话。
我再也没有了困意,心里一直思考着二爷和二婶的事。
“你还听我讲梦不?”二爷见我好长时间不说话,这样问我。并说:“下面的梦才是我今天一定要讲的梦哩。”我说:“怎么不愿听,你讲啊。”
“下面的梦就更糟糕啦,真不好意思讲啦。”二爷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就停下来。
我说:“咱爷俩,被窝里说话,没外人,有啥不好意思的?”尽管是我们二人被窝里偷说话,显然二爷还是不好启口。
这样静了好长时间,二爷还是讲了出来:“唉,事到如今,也只好讲讲啦,你说气人不?我竟梦到你二婶夜里来找我,起初只是伏在我怀里哭诉她对我的思念之苦。
她说得好真挚好动人啊,她诉说她对我的敬佩与爱慕、她诉说她对我的思念和渴盼、她诉说她说不清的矛盾与悲哀,她诉说着……她诉说着……后来,她竟……”
二爷讲道这里就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