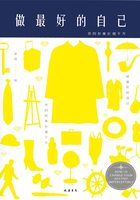《宫堡》这篇的好处还是在前半,写众人都赶来建筑宫堡的那几段,众人都是那样好意的彼此无猜嫌的,给了读者一个童话的世界。后半写王子锁了这宫堡,只留一老人与其幼小的一孙女看守,他自己则去到外面的天下世界为寻觅谁可以做他的新娘,到了老年单身归来与留守的昔年的小女孩——今日的老妇人,一同开了岁久生锈的锁,那钥匙都断了,又走回来,两人携手走进一小木屋里去了。一种荒愁阴郁之感,使人读完后解不开。可是写得异样的庄严266中国文学史话幻美,而这里正有着文章跌入艺术的陷阱的危险。
幸好后面《浑沌》一篇中有“重逢”的一节,补写这“王子一人骑马独自归来。他走遍了天下,才知道他心上一直恋爱着的是这智者的孙女。”她不是已变了老妇人,而是今年正十七岁。这样读者就顿时眼睛明亮起来,有现实的平正可喜。很当然的事,却能不俗化。简单的几笔,可是便人可以想了又想。我的学生说:“因为有了后面的一篇,前《宫堡》的本文乃成了像梦里的一样,很好玩了。”
第八篇《皮貌》,分为两则故事。第一则讲一个少女在月光下充满梦幻似的热情与理想。然后月光在她睡着的时候,把这少女的热情与理想像从她身上脱出的皮肤一般,亦像一件脱下的衣裳似的把来带走了,于是她就成为平凡的姑娘,结婚了为平凡的妇人,生有婴孩。现在窗前的月亮前又是那婴儿的梦幻似的光辉,照进来浸透了婴孩在嬉戏中把光辉也抹在母亲的脸上。
这则故事写的寓言怪奇而使人不觉其怪,只觉是平常,亦不觉其是寓言,而只觉是素朴的事实,这是非凡的笔力。庄子自说他的文章是寓言,盖能知寓言之理者,则知万物之造形,万物皆是大自然的寓言。然如诗人咏花是寓言,却要使读者满足于其咏的只是一株好花,此外不必去想那是比拟的什么。即是读之不费心机,而自然可有思省寻味无穷。(但如《红楼梦》亦有人要索隐,则不是曹雪芹之过了。)鹿桥的这则故事,便是自然得像一首诗。
第二则故事是法师把身上的表皮从一点伤口撕大,至于他的真我完全从表皮脱了出来,也可以又钻进去,皮貌有老衰,皮貌底下的真我没有老衰。这故事使人想起六朝时受印度影响的鹅笼书生一类的志异,但是不及前一则月光皮貌写的好。因为读时太觉其是在说一个哲学思想,而且写怪奇不可又带合理主义。从剃胡子的一点伤口渐渐撕开皮肤,那似乎想的太精巧合理了些。而如鹅笼书生的故事就好,因为它绝不使读者去想象那样的事可能不可能。
《花豹》与第九篇《鹞鹰》我特别喜欢,但是写评语时亦不特别多写,因为那样的文章是要读者一句一句读,自己去寻味它的好处。
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一点:鹿桥描写生命的动态的本领,如写小花豹赛跑的姿势,如写鹞鹰飞翔的姿势。
自黄帝以来中国民族本是有大行动力的民族,所以如《诗经》
与汉赋都是动的文学,《诗经》里写王师征伐的行军与阵容,写舞,写御车与射礼等行仪,写农作与建筑的有声有色,写牧人与牛羊的走动姿态,写梁与河中鲂鲤鳣鲔的活泼游泳,与汉赋里许多描写水的动态的单字与叠字,遇有描写山的,把山的静姿亦都写成了动态的许多形容字,真是轰轰烈烈。直到唐朝的文学亦还是这样的。而自宋朝起才偏于静的文学了。后来对此反动而有元明的杂曲,曲文学亦是行动的文学。
自宋儒主静,然而如文学,静的文学尚易工,动的文学才是难,亦更高贵,古来最高的诗人李陵、曹操、李白的都是动的文学,宋朝尚有苏轼辛稼轩的亦是动的文学。我这回才明白了元曲的真本领亦在其是动的文学。而现在则要数鹿桥的文学了。读他写的小花豹赛跑的姿势,与鹞鹰飞翔的姿势,每回读时使我又重新感叹欣羡。这才是中国文学的真本领,绝非西洋或印度可有。西洋亦有很会描写动作的,但与鹿桥的不能比。鹿桥写的如花豹与鹞鹰动态,都是情操,西洋文学则把动态只能写成物理学式的,是用的所谓自然主义的或写实主义的手法,不能写行动一一是情操。
第十篇《兽言》,讲一位学者到了山中离人迹处猩猩的世界,学会了猩猩的言语与行仪。那里的是智慧深邃而又幼稚好玩的世界,一派鹿桥式的清和。但也带点美国味。与美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中,鹿桥之外,我所知道的只有往时胡适之先生,他的为人亦是这样的清和。虽然两人学问思想很不相同。而后来那学者是别了猩猩又回到好残杀与制造是非的人类社会来了。他要打坏学校的所有功课,叫孩子们不要读书。连他自己在动手编的猩猩的语言学的原稿亦把来烧掉,让猩猩的世界的消息永远到不得世人的耳目。这里鹿桥对于文明与自然的看法,不是没有中国的,但大半是西洋的。
西洋人说的要重返自然,与老庄说的自然不同,老庄的是天机,天机亦可以生在文明社会里,西洋人说的则是道德,如鹿桥文章里猩猩社会的原始性的善,那不是天机而是道德观,非原始社会不能兼容。可是我们到底不能为要原始社会而破坏现代社会,所以就思想来说,《兽言》的思想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兽言》是单因鹿桥的文笔的力量实在好,故事的结束尤其有一种余韵。但是这故事里猩猩的语音语法的烧余残稿,使我想起埃及一块石上的刻字。
古时曾有过埃及帝国久已被人遗忘,在一块石上刻的埃及古史字已无人识,惟相传是神的文字,这真实比《兽言》的故事更深厚,《兽言》见得单薄。还有中国旧小说里的无字天书,亦比起来,《兽言》的结末的发想见得是小了。
鹿桥的文章有一种小孩似的天真。本来好的思想都是小孩似的单纯的,而且是不限于时代性的;但是同时也要晓得开创天下的艰难曲折。鹿桥的是童话世界里的道德观,过此则如那老婆罗门教太子的杀人剑活人剑,在分辨善恶时要失败了。
第十一篇《明还》是所有这些故事中最好的故事,鹿桥真是了不得。从开头讲一个小小孩与蚂蚱与小鸟玩,与萤火虫玩,就写的非常好,只有鹿桥才能写得出的那种好法。小小孩看见玩把戏的人耍大球,小小孩没有球,他就叫了月亮来做大球在屋里滚耍,这时外面就月蚀了。后来又叫太阳亦来做大球在屋里滚玩,这时外面就日蚀了。外面街上人的惊慌大乱,小小孩被母亲责骂的眼泪,都是这样的现实。小小孩的屋里两个大球,一个黄的,一个白的,那照得读故事的人亦睁不开眼的亮光!因小小孩被母亲责骂,那两个球就带着他从窗子飞出去,一直飞到天中央。外面就又是白天了,又恰好是正午。读完了使人只大睁着眼睛想要叫出一声“啊!”此外什么想法都不能有,可有的只是这样现实的,然而是无边无际的永远的惊喜。讲故事能讲到如此,就可以什么思想都不要了。
第十二篇《浑沌》,可以看出鹿桥的思想的全容。鹿桥的是儒家的正直的信念,而以婆罗门的瑜伽与三昧来使之深邃,又加上美国人的现实性与活泼。
美国我不喜,但美国也给了我们两位学者,胡适之与鹿桥以她的最好的一面。胡适之先生的错误很多,但他的做人的基调其实是儒家的,有他的大的地方与安定,若非这个,亦不会有他那成就的。胡适之是受的美国的影响于他不能说不好,不好的是他所崇奉的杜威哲学。鹿桥对于美国比胡适之晓得分辨,而比胡适之有对自272中国文学史话己的思想自觉。鹿桥亦有他的大与安定,否则亦不能有他的文学。
鹿桥更有他的深邃。而且有胡适之所没有的小孩的好玩,虽然胡适之亦是单纯的清洁的。
鹿桥文章里小孩的喜乐不是美国人的幼稚就能有,而是印度泰戈尔诗里才能有的。但中国的又异于此,中国的是造化小儿的顽皮。此外是日本的小孩,清纯、美艳,也顽皮,但与中国的还是各异。《浑沌》篇里的“洲岛”,讲神只们创造洲岛就像小孩在海滩玩沙子那样,玩完了走后就忘了。这近于造化小儿,但是没有造化小儿的坏,所以我说是泰戈尔诗里的。而我喜欢造化小儿的那种坏。
《浑沌》篇的开头两则,“心智”与“易卦”,都是印度的思想。印度思想无论是婆罗门的或佛教的,皆重在冥想与内观,所以有唯识论那些个分析心智。中国的则重在正观,易卦是观天地万物之象。鹿桥的是印度的,所以把易卦看做心智的六个窗口。但是大学者不论是哲学家或文学家,皆自然会追究到心智与内观外观的问题,鹿桥亦是在这里有他的学问的底力。他的大背景是浑沌,着力处是在“琴韵”的修明镜智。
《浑沌》篇里的“森林”、“重逢”、“天女”、“琴韵”
这几则是在前面我都有说过了。“药翁”也很好玩。这里只说一则“沙漠”,是讲一位老鹰师遭了可汗的不讲理,他为遵守训练大雕时,他自己所定对大雕的命令,不惜将身喂大雕撕食。这里又是鹿桥在描写大雕的飞翔,猎取获物的姿态时,表现了无比的笔下本领。而在思想上则这故事是显示了鹿桥对于他自己的生涯中的一种信念的坚执,到壮烈的程度。
《浑沌》篇末后的“太极”是大团圆,有点像西洋舞台上各式的演艺都完了,最后全员登场大大的热闹一阵子,向观众表示谢意。但这里是有着鹿桥的浑沌哲学的,借儒家的一句话是众善之所会归。然而这里使我想起亦还有《庄子·齐物论》里的,天地有成与毁而无成与毁、有是与非而无是与非的浑沌,世界之始可以亦在于现实的世界。
第十三篇《不成人子》,讲吉林省的荒野深山中有许多木石禽兽变的山魈,称为蹙犊子,他们都想修成人身,夜间遇有赶大车的经过时就都围拢来跑着追着问好,想要讨赶车的人的一句口气,当他是人,这一语之下他就得了人身了,少亦可进步了十年乃至百年二百年的修行。但若一语题破他是蹙犊子,他至今的修行就大半都被打落了。故事是一位赶车的老太太帮助好的山魈变成人,打落贪狠凶残的山魈叫他永远做蹙犊子,这里有着教育者鹿桥对后辈的慈禅与严正。不止作为教育者对晚辈,他对世人一概都是这样的慈禅与严正。鹿桥的便是这样的非常之正派的,而且是正面的文学。
正派而且正面的文学最是难写。果戈里写《死魂灵》第二部想从正面写一个真美善的年轻姑娘,结果失败,把原稿都烧了。托尔斯泰晚年有写正面的善的几篇短篇小说,还有是泰戈尔的诗也是正面的写法,再就是鹿桥的《未央歌》与《人子》了。但是三人的各异。托尔斯泰的是旧约的,泰戈尔的是吠陀的,鹿桥的是儒家的。
但鹿桥的还是他的动的文学得力,如写《不成人子》里小獾实在是可爱。又且句法用字好,不带一点文话,也没有刻意炼句炼字,看起来都是世俗的语法,惟是壮实干净,而什么都可以描写得。
但我对于最好的东西,也是又敬重,又真心为之欢喜,而想要叛逆。读完这篇,不禁要想那赶大车的老太太,如果她看错了蹙犊子的善恶会是怎样的结果呢?黄老的说法是,错误了亦可以成为好的。
法海和尚的错,他不承认白蛇娘娘的修得了人身,演出水漫金山。洪太尉错放了被锁镇在伏魔殿的天罡地煞,演出梁山泊宋江等一百单八人搅乱时势。世上的凡人与天上的仙人都会犯错误,而中国音乐的工尺谱里有犯调,如胡琴的工尺调里有二犯,这都是使人想到人事之外尚有天意为大。
结语前年深秋,我陪鹿桥访保田先生于京都嵯峨野落柿舍,遂同车至保田邸受款待,欢谈至夜深,保田邸在三尾町冈上,辞别时夜雨中街潦灯影中主人亲自送客至交叉路口叫出租车。
保田与重郎是数百年来不多见的日本文人。他但凡一出手,没有不是美得绝俗,但凡与他有关系的山川人物器皿亦顿时都成了是美得绝俗的。可是又大又威严。但我不赞成专为诗人或文章家,而是应当为天下士,志在拨乱开新,建设礼乐,文章是余事,故其文章乃亦无人能及。最大的歌人是明治天皇,但他从不以歌人自居。
我如此地反对保田的以隐遁诗人自期。我而且说了,日本的美不如中国的在美与不美之际。我曾在保田家作客,讲到这些,翌日保田道:“昨晚我不寐,把你的话来思省了。”后来他还是不受我的影响。而我亦因而更明白了我自己的信念。
我以为鹿桥的生活安稳亦是好的,写写文章当然亦是好的,只要是异于西洋的分业化的文学家。鹿桥的《未央歌》与《人子》
不触及现实的时势,这都没有关系,即如苏轼的诗赋,亦几乎是不涉现实的政治这些事的。但苏轼的诗赋里无论写的什么都是士的情操,这点我要特别指出。而学西洋的分业之一种的文学家则最好亦不过是职工的,优伶的。保田与鹿桥当然异于分业的文学家,保田是神官的,鹿桥是婆罗门僧的,但皆不是士。
还有一点我要指出,文章必要有场,可比磁场,素粒子场的场。又可比雨花台的石子好看,是浸在盆水里。中国的文章便如《警世通言》、《金台传》那样的小说,背景都有个礼乐的人世,而如李白的诗则更有个大自然,文章的场是在人世与大自然之际。
保田的文章倒是有着这个的。鹿桥的却是有大自然(浑沌)为场,而无人世,这乃是婆罗门的。西洋亦没有人世,而且不能直接涉及大自然,西洋文学的场是粗恶的社会加上神意;神意之于大自然是间接的,西洋文学的场不好。
第三点我要说的是,凡是大文学必有其民族的家世为根底。今年暑期中我把泰戈尔的诗再读读,这回才感到了他那柔和鲜洁里其实有着威力,那是亚利安人的吠陀精神的生于今天。托尔斯泰的文学是天主教的,加上斯拉夫民族的,再加上现代化,但他最晚年的作品是把现代化舍弃了,写永恒的无年代性的真理。而日本文学又有日本民族的家世根底。
日本昭和三文人:尾崎士郎、川端康成、保田与重郎,三人最友善,互相敬重,而三人各异。保田的文学的根底,是日本神道的(《古事记》里的),加上奈良王朝的(飞鸟时代的),加上现代化。尾崎的文学根底是日本神道的,加上战国的(源平时代的),加上现代化。川端的文学的根底是日本平安时代王朝的(《源氏物语》里的),加上江户时代大阪商人的(西鹤文学里的),再加上现代化。
日本之有神道,可比中国之有黄老,是其民族精神的原动力,川端文学上溯至平安朝止,不及于神代纪,故不及尾崎与保田,惟于西洋人是川端文学容易懂。而尾崎与保田则甲乙难定。日本人爱两人的文学者,到得热情崇拜的程度,久久不衰,如日本最大的印刷企业大日本印会社的社长是保田崇拜者,其妻则是尾崎崇拜者。
川端诺贝尔奖更得人敬,然而不得人崇拜。因为尾崎的与保田的文学打动了日本民族的魂魄深处,所以读者爱其人,至于愿为之生,愿为之死。
于是来看鹿桥的文学的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