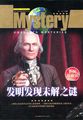引子
《中国法制观察周报》主编周浩然有个外号——“周母鸡”,这是外面的人送给周浩然的。他在《中国法制观察周报》这一亩三分地上呼风唤雨,折腾得下面鸡飞狗跳,脾气上来谁都不买账。但到了外面,绝对是一护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主儿。兄弟单位、业内同行谁要是在他面前提起《中国法制观察周报》一个“不”
字,那就等于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周浩然从来不介意把自己尖酸刻薄的好口才展示给外人,不驳得对方哑口无言,偃旗息鼓不算完。这一点上,他还真就像一只老母鸡,护着《中国法制观察周报》一群小鸡崽们四处咯咯啼。
听说周大主编对这外号还挺认同,曾经在报社开年会聚餐,酒酣耳热之际,提着一瓶燕京啤酒,挽着袖子,拍着胸口说:“说我护犊子,我还就护了,哪有自己的兄弟自己不爱的,连这点都做不到,那就别干新闻!”
但是,在一些稿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见报时,面对下面的弟兄们的邪火,周浩然在很多时候也只能充当起“受气筒”,因为在新闻战线上滚了那么多年的他明白,一口气憋在心里出不了是什么滋味。
比如有一次,江天养从国内一个旅游城市暗访归来。那是一个以峰峦迭起、山清水秀著称的国际知名风景区,由于开发较晚,很多设施和制度上就不可能那么规范,但最主要的,是那个地方导游市场的无序竞争和旅游诈骗的全面开花,已经影响整个旅游城市在国际上的声誉。
这个消息来自一名自称是《中国法制观察周报》忠实读者的青年,他来到报社说有重大新闻要提供。一般这种事情都是值班编辑处理,刚好那天江天养结束一个访问回到社里,闲着没事也就坐在一边听,像这样的情况只要他遇上都不会放过,因为里面说不准就有极具价值的暗访线索,但听到后面,江天养和值班编辑都乐了。
事情说起来么复杂的,这个叫小马的年轻人是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因公到那个城市出差,业务谈好以后还有空余时间,顺便就想到风景区玩两天,入住在景区内一家小酒店。到了晚上,他架不住当地导游的热情建议,便去酒店的足疗部做足部保健。然而,在那个灯光幽暗的小房间里,足疗服务员将门插上,转过身来时,却不是规规矩矩地上前给客人做足疗,而是三下五除二就将自己剥了个精光,然后就像女妖见了唐僧似的扑了过去。没错,小马在跟江天养他们的讲述中就是这么描述的,他当时感觉自己就是那束手就擒的倒霉和尚,还在两人纠缠之余,门忽然被撞开,几个手持砍刀的精壮汉子走了进来。
那天晚上,小马经历了人生中最恐怖的一夜,也算是见识到了传说中的“仙人跳”。他被那几个汉子暴打一顿后绑在床上,脖子上架着一柄寒光闪闪的砍刀,浑身上下被搜了个遍,随身带的钱被搜光不说,连银行卡也被人逼问出密码去提款机上提空了。当然,要说那些人全无人性也不尽然,人家走时还丢给他几百块钱车票钱,同时附上一句阴冷的当地话。小马依稀听了个大概,那意思就是——“我们这边有关系,没有摆不平的事儿,老实点。”
在那些人走后好久,小马才从惊吓中回过神来,他跌跌撞撞地跑出酒店,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但是,当地派出所民警那种漠不关心和推诿的态度更让小马不知所措,他们甚至干脆就直接说是因为他自己不检点才惹来的祸,没把他当嫖客抓就算是客气了。如果说前面小马遭受的只是身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恐慌,那么,后来的遭遇更让他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绝望。
“那里的山水是多么的灵秀,那里的人却为什么这样狞狂?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小马最后用一句很富哲理的话结束了他的倾述。当然,他到《中国法制观察周报》这里来可不是为了讲故事,他是来恳请《中国法制观察周报》的记者们对这种黑暗的现象进行调查和披露。
送走了来人,周浩然在办公室里听取了汇报。这个事情严格说起来并没有太大的暗访价值,这种事情在见惯了大场面的《中国法制观察周报》记者眼里根本不算什么,还真够不上出访条件。但基于这当口正好是国家旅游局在整顿各景区旅游市场,周浩然围着办公桌转了几圈,还是把活儿派给了江天养。
没一个星期,江天养就把这件事情办好了。他有个大学同学在那个城市所在省份的公安厅工作,江天养下了飞机没有急着去景区,而是给他的同学打了个电话,随后老同学就把他引荐给了当地公安局。紧接着,江天养以游客身份住进了小马曾经遭受敲诈的酒店。那天晚上,他也踏进了那间幽暗的小房间,只不过这一次,那些敲诈惯了游客的当地混混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从进入房间到被公安局的干警按住,整个过程,都被江天养的微型摄影机给拍了下来。
再接下来,在整个抓捕过程中一直精诚合作的记者和干警们随后就产生了分歧。当江天养将拍摄好的证据和写好的稿件发给社里的同时,当地政府的公关团,也已经走进了《中国法制观察周报》的大门。他们是来请《中国法制观察周报》
给他们的风景区做推广的,广告费用预算100万元。等江天养回京的时候,在报亭里看到的《中国法制观察周报》上就明晃晃地印着曾经视察过那里的一位前国家领导人的手书。
江天养拿着报纸一踏进主编办公室,就见周浩然正笑眯眯地望着对面的他,那模样像极了寺庙里的弥勒佛,只是眼前这尊佛陀好歹还沾着点人间的活气,因为他嘴里叼着一支烟。
江天养冲周浩然晃晃手里的报纸,随手朝办公桌上一丢,淡淡地说:“老大,你毙稿子我没意见,但小的我跑了这么多天,担惊受怕的,您总得给个交代吧?”
周浩然抽了口烟,把烟头朝烟灰缸里一塞,这才摊开手说:“这次是咱们‘母老板’一力拍板,把最近的支出给我看了,老实说,今年咱们报社已经拉了不少清单。我是顶不住了,你可以什么都不管,我得为报社上下一百来号人的吃喝拉撒负责,你呀,这次就安静点吧。”
周浩然说完,又燃起一支烟来,烟雾袅袅中他那张脸浮现出几丝落寞。一时间,江天养也沉默了,两位浮沉新闻界多年的媒体精英同时陷入一阵深深的思索中。
隔了好久,江天养这才站起身来,总结似的说:“好吧,咱们大家都理解万岁,那没事的话我先走了,刚下飞机还没来得及回家呢我!”
“你小子说话可得算话,你不是背地里又想弄什么幺蛾子吧?”周浩然狐疑地望着江天养。
“哪跟哪啊,头儿,你尽管放心,这又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儿,我操那么多闲心干吗?”江天养似笑非笑地说。
周浩然瞅了瞅江天养,微微一哂,“行吧,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反正,现在稿子撤了,广告也见报了,你想要怎么折腾也不关我的事了,去吧去吧!”
江天养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回了周浩然一句:“不算还怎么着?头儿都发话了,我想怎么折腾也没用。”也不等周浩然回答,又自顾自说,“我社里还有点事儿,回见啊!”说完紧了紧身上的电脑包,撒腿走了。
这就是江天养的脾气,要是真这么轻巧放过这件事情,他就不是江天养了。
这一点,相信周浩然也很清楚,不然也不会说出那么意味深长的话。
江天养到办公区一角找到正埋头做事的白小宁,拍了拍她的头,然后将一袋东西放在明显被吓了一跳的女子前面。
“给你的,正宗的农家腊肉,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东西么?”江天养斜靠在办公桌边,望着从惊魂状态中回来的白小宁。
“你还真什么时候都神出鬼没的,谢啦!”白小宁放下手里的活,接过袋子隔着闻了一下,脸上露出一股舒心的表情。
“真香!好久没吃到这个了。”白小宁赞叹一声,歪起头看了看江天养,微微笑着说:“刚忙完,看来很闲啊,要不今天晚上到我家去,我做……腊肉吃?”
她停顿了一下,把本来想说的“我做腊肉给你吃!”硬塞回肚里。
“不用了,我想一个人清静下……手里有点事情,做完就回家了。”江天养轻轻避开白小宁那双明媚的大眼睛,他看得出那里面隐藏着的一丝炽热的情感。
白小宁哦了一声,低下头继续做事,但几许失望的情绪还是带了出来。江天养在她旁边杵了半天,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忽然想起自己该干吗,忙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放在白小宁办公桌的一角,这么站着就开始敲敲打打。
“你……干吗?”白小宁刚有些负气,没理江天养,但现在看他弄个不停,又不由问了出来。
江天养出手如风,一边敲击键盘一边回答说:“这次稿子不是给毙了吗?没关系,咱们自己想办法。”
白小宁凑到近前,看清楚江天养电脑上正在打的字,不由又好气又好笑,点着他的头直叫:“亏你想得出来!”
原来,江天养注册了一个马甲,以一个旅游爱好者的身份在天涯社区旅游版块上发帖子,标题为——“我的旅游惊魂经历,听说标题要长啊啊啊啊啊”。
“没错,”江天养脸上浮起一丝诡笑,“套用一句话就是,没人给我说法,那我就自己讨说法。”
“你也不怕头儿到时候找你麻烦?”白小宁凑过脑袋一边读着帖子一边说。
“等他反应过来再说吧,而且,你以为他真不清楚我后面干的这些……勾当?
这种事情可不是第一回了。”江天养将采访稿件粘贴进论坛发文栏,又噼噼啪啪地改了些文字。经过一番改头换面,这篇暗访的稿子就彻底变成了一个控诉旅游风景区弊病的经历帖。
两人正聊着,江天养的MSN忽然闪过一条邮件讯息,他顺手点开,新邮件上却只有三个字——我想你!
江天养定住身形,他不用看地址也知道发件人是谁,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对他说。
白小宁也看到了那封邮件,沉默了一阵子,她轻轻问江天养:“你们……还好么?”
江天养此时心情十分复杂,他不知道该不该告诉白小宁,他和杨淼的关系现在已经十分的危险,杨淼已经催了他好多次让他赶紧办理出国手续,否则就要分手了。停了下,他还是扬起一副笑脸说:“好着呢,这丫头天天腻着我,过段时间她回国,还是你陪她吧。还有,我说你呀,赶紧找人嫁了吧,也别这么不着四六地过啦,现在虽然说剩女当道,但可没听说哪个剩女想当尼姑的。”
说完,江天养提起笔记本电脑就跑,对身后传来的白小宁的娇斥只当没听见,就这么一溜烟人就已经到了外面。
“江XX,你去死,姑奶奶还没到没人要的地步!”白小宁咬牙切齿,握着拳头朝江天养消失的方向大声叫着,随即又有些气馁地坐到椅子上。
江天养终于答应了杨淼的要求,开始着手办理自己出国的手续了。
虽然,杨淼的最后通牒简单到只有电子邮件里“要么要我,要么要你的工作”
这一句话,但这九个字对于江天养来说,需要作的抉择却是无比痛苦。
曾经有人形象地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四个字——生离死别。死别我们谁都避免不了,唯有生离,我们尽量不要让这两个字发生在自己身上。
江天养最终选择了杨淼,这也使得他一时忙碌起来,白天努力地交接着手里的工作,晚上还要死记硬背地复习着那些曾经熟悉但已经陌生的英语单词。
对于江天养要辞职的消息,周浩然早有耳闻,但是他始终不和江天养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更不给江天养施加任何的压力。抛开人各有志这种老腔调不说,在周浩然看来,尽管失去江天养这样得心应手的一员干将很令人惋惜,但想想人家能够到大洋彼岸和心上人生活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归宿,毕竟谁也不能和工作过一辈子。
于是,就在槐花盛开的五月,某一天,江天养终于正式坐在周浩然的办公桌前,把一份《辞职申请》摆到了桌子上。
两人默默地抽着烟,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良久之后,周浩然先打破了沉寂,笑着说:“一直以为我得先签字把老秦放了,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先释放的居然是你。”
江天养也呵呵地笑起来:“说实话,我还真有点割舍不下。”
周浩然凝视江天养问:“割舍不下什么?”
“您知道,我大学学的是法律,并且大学毕业当年就通过了国家律师资格考试,顺利地取得了律师资格。”江天养把手中的香烟熄灭在烟灰缸里,随后又点上一支,“当时我之所以选择到报社工作,主要是考虑到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律师行业养老不养小,我太年轻,恐怕给人打一场离婚官司都不会有当事人信任我,所以我很有自知之明地选择了先不进入律师行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在报社这样的单位多接触一些人,特别是在《中国法制观察周报》,我有机会接触到全国各地的省、市、县、区的司法机关的负责人或者是业务骨干,我希望和这些人结成朋友,当我有一天人到中年,能够执业当律师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我的人脉关系网,我可以利用这个关系网去为我的律师职业生涯拓宽道路,让我在那个行业里左右逢源。但是在这里干了九年,我突然发现我已经潜移默化地忘记了我来报社的初衷,甚至忘记了我最初的目的只是来这里混资历、培养人脉的,我天生就是块干记者的材料,而报社注定就是我最好的归宿,现在就要离开这里,我感觉到心里空落落的。”
周浩然笑了:“我还记得你刚进入到报社的那年是23岁吧?”
江天养点了点头:“没错,我22岁大学毕业,23岁参加的律师资格考试,也就是后来的国家司法考试。”
周浩然说:“还记得你进入报社的面试吗?那时我是主考官,我当时就对你的简历产生了兴趣,还特地安排人上网查了你的资料,果然你已经取得律师资格。
所以我就在你面试的时候问过你,为什么不当律师要当记者。”
江天养腼腆地笑笑:“对,是的。当时我还假模假样地说:我要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
周浩然用手一指江天养笑道:“我当时就看出来你小子口不对心,我就知道你小子是个投机分子,跑到我的报社来积累社会经验来了,今天可是你自己承认的吧!”
“那您当初为什么还要用我?”江天养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周浩然收起了笑容,望着江天养静静地说:“我也是从你那个岁数过来的人,我知道第一份工作对于一个年轻人是多么的重要。特别是像你当时那样,刚刚走出校门,对于整个社会的认知还都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下,你的第一份工作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你周围的整个世界的看法和认识。”
江天养一时没听明白周浩然所说的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疑惑地看着他。
周浩然继续说:“你当时也有机会去当一名律师,因为你毕竟已经取得了律师资格。但是如果你进入律师事务所里,恐怕就等于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你是为你的当事人服务的,而且那种服务也不是白服务,必须是你的当事人向你支付了律师费用,你才会去为他们维护他们的利益。说白了,你是在为钱服务,于是你的思维里,钱是你最大的雇主,所谓道义、良知、法律都充其量是一个说辞,真正驱使你每天早上爬起来上班的原动力事实上是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