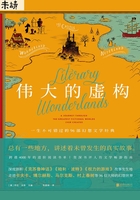袍哥,旧时四川帮会组织,势力波及西南及长江上游。据考证,袍哥的称呼是根据《诗经》上“岂日无衣,与子同袍”之含义生发出来的。袍哥们自己却说是从“三国”故事来的:关云长不得已降曹,曹操赐与金帛,他一概不受,只取了一领锦袍,却常穿在里面,外面还要罩上一件旧袍。他解释说是旧袍系刘备所赠,不敢以新忘旧。所以这个封建会门组织的老名称叫汉留,含义就是从汉朝遗留下来的精神气节。
初期的袍哥组织,不像后来那样低级复杂。清朝末年还曾与革命发生了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袍哥就没有四川的革命。辛女革命前夕,成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保路运动”,全省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进而发展成了一支庞大的“同志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四川最后一任总督赵尔丰的统治。
当时“同志会”和“同志军”里的骨干人物竟有川西袍哥的总舵把子侯保斋,“同志军”的主力也是袍界中人。而社会上的知名维新人士、革命党的头面人物向楚、杨沧白、张澜等人都加入了袍哥。四川军政府的首席都督尹昌衡甚至自称是袍哥总舵把子。
清朝倒台,新政权巩固之后,官方脱离了袍界,袍哥重新回归半非法状态,地痞流氓、地头蛇势力、土豪劣绅大量加入,这个组织从此就变得鱼龙混杂,泥沙不分。
袍哥以讲“五伦八德”的旧传统作号召。最初的形式是一个地方作接待站,称为堆子,悬灯结彩,迎宾送客。后来事情多了,堆子逐渐扩大,固定下来,改称码头,又叫公口、堂口、社、山。
码头各有专名,分仁、义、礼、智,信五堂。发展最大的是仁、义、礼三堂。仁字袍哥,大多数是有功名、地位、身份的社会名流,礼、义两堂是浪迹四方的布衣白了。如商贾掮客、职业刀客一类。袍哥有个流行口号:“仁字讲顶子,礼字讲银子,义字讲刀子。”每个码头的组织分为十排,每一个首脑人物称做堂大爷或当家大爷,另有一位只拥有虚名的“闲大爷”,多为自我掩护的角色而已。接待南来北往搞“公关”的称管事五爷,权力只逊于当家大爷,所谓“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就是指这种情况。
袍哥分清水和浑水两种。清水袍哥是合法身份,浑水袍哥是非法身份,杀人越货,聚散无常,有的甚至啸聚山林,拥有常设土匪武装。清水和浑水看起来是两家人,各有各的活动方式,其实两老之间互为关联,互相转化。清水一旦行囊羞涩,便会高执黑幡,去干抢劫、贩大烟,当刀客的勾当,浑水若发了财,便会洗手不干,一心”从良”。于是买田置地,占个码头公口充当善人,成为社会贤达。有的清水上层人物暗使眼色,浑水立刻派出刀客枪手去为之刺杀仇家,而浑水犯了案,躲进有地位有名望的清水的深宅大院里,官府也只好装聋作哑。其实清浑实在无法分清。
刘文彩派给刘文辉的那位管事袍哥便属于浑水袍哥。
不一会儿,周管事被管家风风火火地叫了来。
“幺爸,您老叫我。”周管事恭恭敬敬地走上前,依照乡俗,呼唤道。
‘周老弟”刘文辉挥挥手,示意他坐下:“鲜管家给你说了吧,刚才军统把我的卫士连长抓走了,你看……”
“那还了得。”周管事霍地站起身,眼睛睁得铜钱般大,“我找几个弟兄把他杂种些毛了。”
“不急!不急!”刘文辉仲了手向下按了按,示意他坐下,然后笑道,“老弟,我知道你有办法,你先派几个人把卫士连长关押的地方打探清楚,我们再想办法。”
其实,刘文辉心中明白,这是徐远举在和他暗中较劲。自从周管事从大邑来后,便带着民众自卫队针对公馆对面的特务狠下了两手毒招。
一日,两个特务奉命监视刘公馆,一个上午鬼头鬼脑问东问西,搞得路人皆知,待至中午,他们从屋里钻出,在临街的杂货摊上买烟,正讨价还价的时候,突然“啪!啪!啪!”几声清脆的枪声响后,两个特务来不及哼一声,便横尸街头。
徐远举得报,亲自带人勘察现场,忙活一阵,不得要领。没办法,徐远举心中恨恨的,嘴上只得打着哈哈劝刘文辉注意安全。
几日后,军统重新派来了两个特务。不料,第二天下午,又被一彪形大汉用新式卡宾枪射杀在茶楼里。人们围上前一看,两名血肉模糊的特务身上,居然还附着一张文字,上写:“与川人为敌,如此下场。”
徐远举气得牙齿咬得格格直响。
王陵基坐不住了,带上一帮人跑来方正街,煞有介事地视察布置了一番,还把一名亲信派来充任保安团驻方正街连的连长。
次日,那位连长正拥被做梦,香甜地睡着回笼觉,突然,“轰隆”一声,一颗手榴弹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扔进窗户,爆炸声响过,那位连长灰飞烟灭,尸骨全无。
徐远举、王陵基明白,这是“多宝道人”刘文辉在和他们斗法。但苦于无证据,刘文辉又是封疆大吏,只得咽下这枚苦果,暗暗找茬寻机报复。
刘文辉的卫士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军统蓄意抓走的。
再说邓锡侯自那夜从刘公馆回去后,司机捂着火辣辣的脸向他诉说了挨打的委曲,他怒不可竭。
“自乾,说句不该说的话,打狗还得看主人,龟儿子徐远举这个狗特务打了我的司机,如此胆大妄为,岂有此理!”
“晋康兄,你有所不知,我的卫士连长都被他们抓走下。”
“哟!真是欺人太甚。”
“莫怕。孙悟空逃不过如来佛的掌心。晋康兄,你等着看好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想与我刘文辉斗法,徐远举王陵基还嫩了点。”
“那是不是叫张岳军打个招呼,放人,赔礼道歉。”邓锡侯在电话的那一端惴惴不安地问道。
“何必去搬他那尊菩萨。”刘文辉轻松接口道:“劳师动众,我们自己把事情闹大,正好到老蒋那里去讨说法。”
此时,蒋介石、张群正呆在成都,准备与刘文辉等共商四川的防务大计。
刘文辉果然把事闹大了。
第三天晚上,周管事派人探听到,卫士连长被关押在北郊不远的王陵基保安团的一个连队里。
入夜,寒风习习,夜幕低垂。周管事带着20多名荷枪实弹的卫士,还有他手下的几十名袍哥大爷,提着刀棍、长枪,神不知鬼不觉地闯进了保安团连部。
卫士连长被关在该连的禁闭室里,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
周管事带人冲进连部后,首先抓住了正在麻将桌上专心砌牌的保安连连长,然后用刀抵住其胸,严词逼问卫士连长关押的地方。那连长战战兢兢地被他们挟持着,俯首就范,让人打开禁闭室,卫士连长这才被周管事等人架着救了出去。
保安连长待他们走过后,回头一看,整个连队被砸得稀巴烂,电话线被剪断,手下的兵了大都表情漠然,根本未做什么反抗和准备。
王陵基得到情况后,气得暴跳如雷,他找来徐远举,密谋一番,决定到蒋介石那里去告刘文辉的“御状”。
(八)
蒋介石面对御状却不置可否。这大大出乎王陵基、徐远举二人的意外。
“总裁!”徐远举站起身,畏畏缩缩说道:“据远举侦知,刘文辉确有异志。”
蒋介石将眼皮抬了抬,复又垂下,伸手将一杯晶莹剔透的水送到唇边,轻轻呷了口,脸上毫无表情。
徐远举硕大的鹰勾鼻子过分突兀于前,以期待的眼神望着他,期于着某种鼓励以便将话题张展开来。
偏偏蒋介石一脸老僧坐定的隐忍之情,静若止水,不作任何表态。场面顿时显得有些尴尬。
陆军上将,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坐不住了,他望着显得笨拙的徐远举,皱了皱眉,然后扶扶眼镜,挪着肥胖的身躯凝重地说道:“总裁!卑职以为徐站长反映的情况确乎重要。”
“方舟兄。”蒋介石掏出白手绢轻轻拭了拭嘴角,这才开口道:“你们有什么证据。”
受此鼓励,王陵基精神为之一振,脸上的神情显得更加凝重了,他傲岸地瞥了一眼尴尬一旁的徐远举,大声说道:“在刘文辉24军大本营雅安,有一个中共地下电台活动了很长时间,系共党与之联系的主要渠道。”
“这事嘛,雨农生前曾与我提及过。”蒋介石一脸平静地望着他,“只是……没什么确实证据。”
雨农是原军统头子戴笠的字,原本为蒋介石倚重的特工头子,生前身后恶名昭著。君以此始,必以此终。1946年,戴笠乘飞机由北平飞回南京,拟与他人争夺警察总署署长一职。由于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与之交恶,在机上置于炸弹。当飞机冒雨飞至南京戴山时,机毁人亡。一个终生从事绑架、暗杀,策反,耍尽卑劣手段的人最终在其惯用的手段中死于非命,真是绝妙讽刺。
戴笠死后,蒋介石极其哀之,亲书“戴雨农将军之墓”,并执拂送葬,将其葬于南京中山陵侧。
当年,为了查清雅安中共的地下电台,戴笠曾亲赴雅安,但费尽心机,最终一无所获。对此,蒋介石也就不了了之。
“总裁”,徐远举似乎受了感染,兴致顿时提高了,“上半年,我们军统派驻在刘文辉部24军的政训处长了国保就发现了共党的地下电台,而且活动迹象非常明显。可惜,功亏一篑,刘文辉察觉后,把我们军统的了国保赶出了雅安。”
“刘文辉目无法纪,目无总裁。”王陵基如唱双簧一般,“前日祟宁事变,他挑起事端。这次愈加胆大妄为,居然派兵从我保安团抢走了我们抓来的赤色分子。”
徐远举耸着肩,更是满腹委曲:“我们派在刘文辉公馆对面的同志,公然被人暗杀在茶馆,店铺等公众场合,更有甚老,方舟兄保安团的连长清晨大早,居然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窗外扔进一颗手榴弹,当场被炸死。种种迹象表明,上述同志之死皆为刘文辉所为。”
“有这等事体?”蒋介石眉毛一挑,看得出他满腹疑惑。
乎心而论,他与刘文辉根本不是同一船上的人,俩人从1927年表面合作开始,便恩怨集结。换言之,他从来对刘文辉就是猜疑排挤,恨不能一劳永逸地一举解决掉刘文辉。只不过碍于时局变化,历史成因,刘文辉顽强的生存手段,蒋介石终究奈何不得他分毫。
但从客观上讲,蒋介石作为20世纪最擅长玩弄政治手段的人物。当初,他能够从名利上击败各军阀集团,将他们勉强捏合在一块,其擅权专政,驭人之术可谓从封建帝王而来,运用得娴熟自如。面对刘文辉这类的封疆大吏,从历次交道中,蒋介石是深知其斗争手段的。
因此,尽管王陵基,徐远举言之凿凿,令人不可不信,可蒋介石表面上却表现得波澜不惊。
“总裁,”王陵基趋步上前,压低声音道:“不能听之任之,依方舟设想,不如让胡长官……”
蒋介石紧盯着他,一言下发。
王陵基吞咽了一口唾沫,迟疑了一下,单刀直人地说道:“刘文辉本人已从雅安回到成都,其公馆仅驻有一个卫士连。既然他心存异志,而总裁于他可谓仁至义尽,不如干脆……”
“对!总裁,方舟兄的主意高妙,远举以为,让胡长官效法杜光亭(聿明)长官,派兵解决了他。彻底根除将来后患。”
蒋介石还是不作表态,他目光逡巡了一下。转而示目一直低坐在不远处的张群。
张群嘴角正露出一丝令人不易察觉的笑纹。这次到成都,蒋介石轻车简从,行事低调,但唯独没有少了张群,依然将他一道拉上,随时陪侍于侧。
别人不明白,人称“华阳相国”的张群明白,蒋氏成都之行,最重要的内容,便是给川康国民党残余势力打气加压,组织所谓的成都会战,期于作最后的困兽之斗。
“我觉得还是慎重的好。”张群望着蒋介石,语气平静。
蒋介石眼神顿时变得柔和了,对王陵基、徐远举,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作为一国之主,他是深谙帝王之术的,党内派别倾轧、相互牵制,不至于一团和气。尾大不掉,导致驾驭不了。而平时,各派水火不容,纷争不堪时,他再作为权威仲裁老出现,相互调和,如同竞技场上的裁判一样,自然权威至高无上了。
用武力解决刘文辉,固然易如反掌,但要冒很大的风险。而困难当头,重要的是稳定川康上层的实力派人物,给他们打气加压,方才能绑上最后的战车。
张群淡淡一句话正合蒋氏心意,于是,蒋介石又收回眼神,鼓励了一番王陵基、徐远举,便挥挥手,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刘自乾的事,我明白了,你们要相信中央。”
王陵基、徐远举面面相觑。蒋介石皱着眉挥挥手,俩人回过神,快怏而去。
“岳军,”蒋介石总是这样称张群,“你以为该如何行事?”
“蒋先生,”张群也是这般称呼蒋介石,几十年风雨不改,“万不可用武力再来个第二次五华山事件。”
五华山是昆明市区的制高点,历为云南省地方政府驻地。1945年,蒋介石指示杜聿明用武力逼迫龙云下台,交出云南权杖。龙云形同绑票一般被挟持到重庆做了个有名无实的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