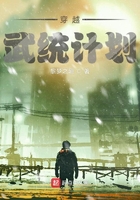父亲身为医生,总是衣冠整洁,保持着高雅的风度。病人来求医,无论贵贱,他一样看待。有的穷苦百姓交不起费用,他还常常解囊相助。克悠至今还记得,小时她家里挂满了“妙手回春”之类的赠匾。父亲常说,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这是世间最慈善、最人道的职业。解放后,父亲被选为山西省政协党委。
克悠从小便浸染在父亲这种人道主义的温情里,上中学生时,她给报馆投稿,用了一个笔名叫“梦欢”。孙克悠对我们说,这笔名隐喻了她在青年时代对现实的种种不满,也深含着她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梦想,同时也能从中透视出她的浪漫情怀。
目睹了战争中的鲜血和死亡,她更加厌恶了残暴、仇杀和冷酷。这一切都使她成了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的攻击对象,成了“温情主义”、“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
1956年,时任哈尔滨市委学习室第二主任兼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和干部处长的孙克悠,被输送到中央党校学习。那是一个多好的学习和深造机会呀,没想到,或许因为上级分派下来的“右派”名额还没填满,或许因为孙克悠太有棱角太“温情”,为一位挨整的同志仗义执言,或许因为中央党校的“右派”名额尚未填满,1957年,中央党校竟把这位哈尔滨送去临时学习的干部打成“右派”。
战争年代,她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呀!
1940年,从女大毕业的孙克悠被派到王震将军率领的359旅驻地绥德警备区。在那里,她像一股清泉汇入黄河,走进人民中间。学会一口地道的陕北话,与老大娘小姐妹亲热地坐在炕头纺线拉话儿,一道下地拔草挖野菜,走东村串西乡办冬学,教贫苦百姓识字,动员妇女参政。那里的婆姨风风火火,都出来为抗战、为根据地做事情。大男子主义的丈夫要是干涉,婆姨们就会说,“毛主席说咱妇女顶半边天哩”!抗战胜利后,她被派往交城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华国锋是县委书记,李立功是组织部长。华国锋原名苏铸,出生于一个穷苦皮匠家庭,l938年加入抗战决死队。在领导交城抗敌斗争时,他与李立功走遍交城山川城镇,熟悉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并同那里的父老乡亲结下鱼水般的亲情。孙克悠与他们下乡时,常常惊叹他们对每条羊肠小道都了如指掌,能直呼每个村干部和民兵的乳名,谈起这些乡亲的家庭情况,华国锋和李立功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交城人民奋起抗敌,剪电线,炸炮楼,八乡四野摆开了地雷阵,炸得敌军胆战心惊,寸步难行。交城因此被中共中央誉为“地雷战之乡”。在保卫军事重地古交镇的战斗中,一天拂晓,奋战了一个月未脱衣服睡觉的孙克悠刚躺下歇息,忽听村外枪声大作,她一跃而起,提枪跑出门外,正遇华国锋拎着驳壳枪组织人员突围。
你带人向西山方向撤!那里有一条山缝,敌人不知道,华国锋大声说。
那你……
快撤!他不由分说。
华国锋率领一批精兵强将沉着应战,孙克悠带一部分人,凭借晨雾掩护和地形熟悉,冲出三面山头敌军机枪的封锁扫射,终于安全突围。翌日与华国锋会合时,孙克悠看到他衣上血迹斑斑,好几位战友再也没有回来……
死都死过了,一腔热血的孙克悠还怕什么打击迫害!
她怒目圆睁,拍着桌子与把她打成“右派”的人物对吵。可政治运动只讲批斗不讲理,对方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你对抗运动,态度恶劣!”又一顶“帽子”把孙克悠的问题由“一般右派”升级为“极右”。同年底,整她的急先锋张某,得意洋洋带着她的档案袋,把她押送回哈尔滨。孙克悠怎么也想不通,脑袋都要炸了。她曾为革命、为这个新中国浴血奋战过,如今怎么突然成了“反革命”?
一夜之间,她沉入生命的谷底,开始了艰辛的劳改历程。那年她37岁,正是人生最成熟、精力最充沛的黄金时代。
那时她想到了伟大的黄河。
那奔腾澎湃、冲决万里的气魄,那不到大海死不休的意志,那金属熔液般柔韧顽强的波涛,那傲视生命、置生死于度外的艄公……
好吧,看谁笑到最后,看谁是枯枝败叶!
丈夫高铁也是久经战火考验的革命者,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我们曾对哈工大的发展史做过专门调查。所有那些离退休的老同事回忆起工大的发展,众口一词,都说高铁是把哈工大推上国家一流大学发展里程的重要人物。是他不拘一格广揽人才、为哈工大后来进入黄金时期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是他开创了这所高等学府三代“八百壮士”励精图治的校风、使得哈工大终于成为今日中国的科学技术高峰之一。
高铁对妻子深表同情和理解。他故作轻松地安慰妻子说,不要总想自己冤不冤了,就当你上战场打了一次败仗吧。
我冤就冤在这次是上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战场,而且我被误伤了,孙克悠实在想不通。
高铁郑重地说,上了打敌人的战场,死了是光荣。上了自己人的战场,死了可不是光荣,所以你得好好给我活着!
这个延安的女儿、黄河的女儿当然不会倒下。她被发配到工厂当工人“劳动改造”并被停发工资。劳动她不怕,在陕北她就一身土一身汗地同乡亲们一起干活了;改造,共产党人一生都在改造自己。那么好吧,这并不是屈辱,与人民在一起从来不是屈辱!
孙克悠悲壮地走向工厂……
当时她家住在哈工大专为苏联专家准备的宿舍楼里。为外交礼议和照顾国际影响,尽管克悠的处境十分艰难,每遇那些专家,她总要报以校长夫人的高雅的微笑。专家到家里来做客,她则要拿出一副欢快的样子,忙前忙后,端茶送烟,招待饭菜,尽家庭主妇的职责。她和丈夫及4个孩子每每出门,一定要保持衣着整洁,风度优雅。这对内心充满痛苦的孙克悠来说,真是难死了。于是,每天清晨,苏联专家和校园里的人见到孙克悠时,她总是那样衣冠楚楚,气宇轩昂,烫着一头波浪式秀发,手中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挎包。人们哪里知道,包里装的是工作服,这位校长夫人是去工厂“劳改”呵!
最初,工厂的工人听说要下来一位“大右派”到车间里“劳改”,都好奇地等着看新鲜,以为此人一定是个大腹便便的男人,没了精气神儿。一见来人竟是个女的,而且精神抖擞,衣着鲜丽,烫着乌黑的卷发,工人们禁不住个个瞠目结舌。
孙克悠麻利地换上带来的工装,在隆隆的机器声中辛勤地劳作着。一天下来,她已与工人打成一片了。她家的保姆,高铁当年的警卫员,包括她在“劳改”期间结交的一些工人,后来都成了她一家数十年始终不渝的生死之交。孙克悠说,她一生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衣着,就像小鸟爱护自己的羽毛一样爱自己的仪表。她认为那是女人的尊严,是一个女人精神不倒的标志,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
女大的同学们都说,在延安,孙克悠穿的是最漂亮的。那么土、那么肥大的灰军装,一到孙克悠身上,不知怎么就显得灵秀了。
1977年,孙克悠随丈夫高铁调北京工作。经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和老上级王震过问,孙克悠的“历史问题”终得解决。日月如梭,此时她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还有一点余热,做什么?
孙克悠选择了中纪委,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最后的生命之光,投向所有蒙冤受屈的生者和死者!她在大半生里惨遭迫害,大好年华付诸东流,这教训太沉痛了。
在胡耀邦领导下,中纪委首先全力以赴查处被“四人帮”迫害的中央领导人的大案,相继成立了几个小组。孙克悠任中纪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瞿秋白专案组组长,负责复查瞿秋白是否“叛徒”的问题及其被捕就义的真实情况。
为还给瞿秋白一个历史的真实和正确的评价,孙克悠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出发了。她走访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陆定一对孙克悠深情地说,秋白同志是我的老师,在“八七”会议前后,革命正经历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秋白同志当时挺身而出,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历经一年多的周密调查、广泛取证,大量事实证明瞿秋白是中共早期杰出的主要领导人,是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具有独特才华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孙克悠执笔的《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为蒙冤多年的瞿秋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继尔,孙克悠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将瞿秋白的光辉形象重现人间,她感到无限欣慰。后来,孙克悠又接下几个大案要案,继续着她的新征程。1982年,孙克悠主动申请离休。
她依然常常想到那条伟大的母亲河——黄河。那奔腾澎湃、永不回头的力与美,那难道不是延安人的精神象征么!
吕璜:祸从天降——公安战线第一大冤案
南下,南下,南下。
陈泊(又名布鲁),这位“延安的福尔摩斯”、神勇的独手侦察英雄,一路干得生龙活虎。他就像打扫战场的“清洁工”,大军过后,他率部下开进去,把旧时代留下的残渣余孽、军警匪特,一古脑儿扫地出门,扫出个太平世界,他又拔腿走了。
1949年lO月14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拿下南国重镇广州。中葆央委派叶剑英担任华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和广州市委书记,这位儒帅早已预料到解放后的广州将面临复杂的敌情,特别需要熟悉地方情况和语言的干部来工作,于是亲自点将,把广东出生的陈泊从江西省要来。
时年40岁的陈泊,出任广东省及广州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此时陈泊的妻子吕璜因南下途中孩子患病,留在上海。
广州是中共解放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几乎把所有积怨和仇恨都倾泻到这里。大批的潜伏特务、土匪、港澳当局清除的盗匪歹徒、旧政府留下的军警宪特流散人员,一时间把广州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愈乱愈显出陈泊的胆略与本色。他与副局长陈坤(原香港分局情报工作负责人)都是广东人,熟悉省情市情。在省市委的支持下,他们调集大批干部,充实公安队伍,迅速接管了国民党旧警察局,清除了千余名旧警人员。接着大刀阔斧,横扫散布在社会各个阴暗角落里的污泥浊水,仅仅一年有余,堪称硕果累累。
共侦破300余起匪特案件,案犯达1000余人。
缴获电台20余部,短枪300余支,机枪20余挺。
破获了国民党特务图谋炸毁市军管会案,台湾中统机关派遣特务潜伏组案,逮捕电台组长等6人,并使电台为我所用。
策反了白崇禧所辖“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名士兵和水手全部起义投诚。
通过关系,将李宗仁逃美带去的三万美金弄回广州。
叶剑英对陈泊的工作深为满意,他在写给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长)的一封信中称赞说:“广州市社会治安迅速平定,是与布鲁的名字分不开的。”
不曾想祸从天降。1951年1月24日深夜,陈泊与陈坤正在睡梦中,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闯入他们的临时住所,两人被逮捕了。
这就是解放初期震惊全国公安战线的“两陈案”,也是共和国历史上公安战线第一个大冤案。两人被迅速押往北京公安部,据说罪名为“英国特务”。之后的20天内,广东省公安厅抓起700余人,广州市公安局抓起300余人。“两陈案”前后使上千人受到无辜株连。有的致死,有的终生残废,更多的人从此跌入漫长而苦涩的政治厄运。
两年后,最初的“英国特务”罪名不见了,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罪,判刑lO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对陈坤(1952年10月在狱中病故)以“包庇反革命罪”判刑8年。陈泊听了判决书,抱头呆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像疯了一样,双手握拳举过头顶,嘶声高喊“冤枉呵!”
无人理睬。
其实,大量事实表明(见蒋巍所著的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福尔摩斯》,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这时公安部办案人员已经知道陈泊、陈坤是被冤屈了,但此案是他们一手抓出来的,他们不敢也不肯改正此案,而且决意压制陈泊,绝不能让陈泊发出一点喊冤的声音!于是,在陈泊10年服刑期满后,公安部怕他到处告状,仍然不放他回家,又严重违法(那时很难说有什么“法”),强行把他押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监督劳动”。自此,这位为保卫延安、保卫新生的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我党第一代侦察专家,先后在单人牢房和劳改农场苦熬了20多年。1972年2月25日,陈泊在他的劳改地——湖北沙洋农场医院含冤病逝,终年63岁。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72年辞世,整整走过46年人生历程,前23年是为革命出生入死,后23年是在牢狱的煎熬中了结残生。叶剑英对“两陈案”大为不解并且十分不满,他曾对公安部办案人员说,陈泊的历史我是知道的,他从南洋回国后表现一直很好,是很优秀的公安干部。
公安部办案人员的回答相当蛮横:你只能证明陈泊回国后的一段,不能证明他在南洋的一段!
叶剑叶愤然说,他为了弄炸药,把手都搞掉了,这还会有问题吗?
办案人员说,新中国建国之初,敌情复杂,举步维艰,蒋介石撤退之前埋伏了不少“定时炸弹”,你怎么能证明他不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
就在二陈被捕不久,陈泊的妻子吕璜、陈坤的妻子高华,被同时押送公安部。她们带着各自的孩子,住进前门外一个破旧的骡马小店,听候发落。1951年7月,吕璜调入全国妇联“控制使用”。自此,夫妇二人咫尺天涯、隔墙相望的苦难日子开始了。
1952年秋,一辆吉普车急驰而来,在骡马小店门前停住。
车上跳下一个神情冷峻的年轻人,匆匆进店找到陈坤的妻子高华,要她立即跟他到监狱去,说陈坤病了。高华胆战心惊地抱裹好刚刚两个多月的婴儿,让吕璜帮着照料一下两个大孩子,便上车走了。两个小时以后高华回来了,一进屋就扑倒在床铺上失声恸哭。
吕璜问她怎么回事?高华呜咽着说,陈坤让那些人折磨得快死了,现在双目紧闭,呼吸急迫,怎么叫都没反应。高华推他的左脸,脸就歪向右边,推他的右脸,脸就歪向左边,看来挺不多长时间了。
吕璜心里一阵发抖。陈泊的身体还不如陈坤,陈坤给搞成这样子,陈泊还有好吗……吕璜不敢往下想了。
第二天,公安部两个干部又骑着自行车来找高华,要她去医院。高华愤怒地拒绝,但不行,非去不可。吕璜一见这阵势,就知道陈坤已经死了。这是监狱的规矩,犯人死了一定要家属到场,以证明犯人是有病死的,属正常死亡。果然,高华见到的已是躺在太平间里的冤魂了。高华抱着怀中的孩子痛哭不止,公安部派两个人把尸体抬进门外的一付棺材匣子,然后用板车拉到监狱外面的一处空地,草草挖了个坑,把人埋了。
30年后,“两陈案”平反,当初埋葬陈坤的地方已是高楼林立,连方向都摸不准了,只好将陈坤生前用过的一支钢笔放进骨灰盒,安葬在广州银河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