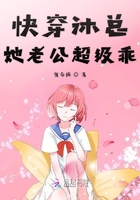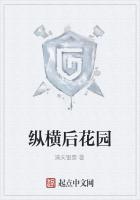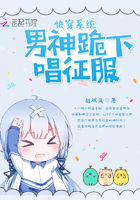在美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案例教学法虽然被看成是学术性与实践性的最佳结合点,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教学方法实际上是模拟法律家运用法律的过程。运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讲授法律家和法庭获得结论所运用的方法,培养学生的法律推理能力和像律师一样的思考能力。作为弥补案例教学法的缺陷而出现的法律诊所教学,更体现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后法学教育实践性导向强化的趋势。伯纳德·施瓦茨在《美国法律史》一书中指出了这种倾向。他说,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重新兴起了赋予法学教育更多实践内容的要求,主要分为两个方向:其一,增加“技术性”课程。其二,更重要的是“临床诊断”式法学教育的发展。法学教育改革的意图,是为满足这个变动着的社会对律师需要而作出努力的一部分。总之,美国建立起了与众不同的法学院模式。这种制度模式所体现的主要理念是:法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分离,报考法学院的学生通常要求已获得某个学院或大学的学士学位。学制为三年,或者在职兼读四年。在学习期间需要修满大约90学分,毕业时取得法律初级学位——J.D 学位。获得该学位后就可以从事法律职业。在职业素养价值观的导向下,通过特有的案例教学法、诊所法律教学方法,美国的法学教育实现了知识教育与技能训练同步的教育目标。美国的法学院也因其以培养法律职业人才(即律师和法官)所应具有的思维与操作技能为追求,而成为举世公认的法学实用教育或职业教育的典范。因此,法律技能的训练是美国法学院的重要内容,法学院承担起法律技能培训的全部任务。
二、知识教育与技能训练分段模式
分段模式,是指就法律人养成教育来说,分为两个阶段:侧重知识教学的学院教育和侧重技能训练的学院后教育。在学生接受法学教育期间,主要对学生进行系统化的知识教育;在接受学院教育后,专门设立了职业上岗前的培训制度,集中对学生进行法律技能训练,例如德国、日本和英国。
德国传统上的法学教育,是一种取自“国家法律家”的样式。也就是说,从进大学攻读法律专业的第一天起,到从事典型的法律职业(法官、律师、检察官、公证人)之日止,法学教育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由国家严加规制,并以僵化的考试制度统制之:在德国,作为理论教育部分的为期4至5年的本科法律专业学习,是以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为终结的,随之是实务性的“司法研修生”教育,亦即在不同阶段,分别在法院、律师事务所、行政机关或企业进行研修。至于实务教育部分,同样以国家司法考试为终结即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通过第二次司法考试的法律家,获得了“法官任职资格,”也直接获得了从事有关司法职业和执业律师的资格。大学毕业生欲从事法律职业,必须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进入预备期,在州高等法院院长的统一管理下,接受两年左右的法律职业训练,在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后,才可申请各种法律职位。“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普鲁士实施了以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为宗旨而设置的、由理论和实践两个阶段组成的法学教育模式。这种一般所称的大学教育和实践教育相分离的‘分段模式’,不只经历了魏玛共和国时期,而且——不考虑一些特性——也经受住了纳粹时代的考验,迄今还在德国保留着自己的基本特征。”日本的法律人养成教育也采用分段模式,即大学法学教育与司法研修相结合的制度。依据日本法律的规定,所有的法律职业者在开始其职业之前,都必须经过司法研修的训练。始于1947年的司法研修制度,目的是使研修生能够掌握以法庭实务为核心的基本技能和法律职业伦理观念和职业意识。从而培养研修者的高深的专业知识、完整的生活常识,掌握法律的理论和实务,具备与担任裁判官、检察官、辩护士相匹配的品位和能力。因此,日本的司法研修所将这一制度的特征概括为:1.展开法律实务教育;2.重视法曹伦理教育;3.对应社会机制;4.强调实务修习的重要性。研修所承担对于任职前的训练,分阶段来进行。首先是在研修所内的初始训练,时间是四个月;然后是实务研修,时间是十六个月,其中在地区法院八个月,在地区检察厅和地区律师协会分别为四个月;实务研修之后,还有四个月的所内后期训练。最后,研修者要参加最高法院安排的结业考试,凡考试合格者,才可从事法律实务。另外,英国的法律人养成教育也是分阶段进行。在英国,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学制三年的大学法学教育,由大学法学院(系)来承担;第二阶段是职业训练,由律师学院负责安排和承训,时间是一年;第三阶段是实习(又称为学徒阶段),由律师事务所承训,时间因拟任的律师的种类的不同而不同。
法学教育对法律技能培养的途径
法律职业对其从业者的法律技能的内在要求使得无论哪一种法律人养成模式,都不能回避法律技能培养这一重要问题。法学教育作为法律人养成教育中的基础性阶段,也必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法学教育是否应该担当法律技能训练的任务?是不是采用分段模式国家的法学教育对法律技能训练没有意义或可以完全忽略其意义?在诸如美国完全由法学院来完成技能训练任务的国家怎样才能更充分地完成该项任务?这些问题是当下各国法学教育改革的重点问题之一。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既无法律技能培训的专门机构,在法学教育中又缺乏对法律技能培训理念与方法的国度,面对法律职业化的浪潮,如何应对法律职业化对学生法律技能的需求?对诸如此类问题的考察,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当前法学教育改革的趋势来看,无论是德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法律技能培养的问题一直是教育改革的焦点,更是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法学教育对法律技能的价值除了为技能的形成提供知识基础外,最重要的是通过恰当的教学形式强化学生对法律技能的掌握。根据教学过程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实践中进行这一标准,可以将各国通行的法学教学形式概括为两类:课堂教学形式和实践教学形式。课堂教学是传统的、主流的教学形式,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教学形式,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传统上都是以课堂教学的形式来进行的。实践教学形式是在课堂外通过学生参与法律实践活动进行教学的形式,诊所教学是最典型的形式。对法律技能的培养来说,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形式都具有价值,正如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律教授托马斯·D.摩根所言:对于一个课程的价值来说,在技能和理论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
一、课堂教学对法律技能的价值
首先,课堂教学为法律技能的形成提供了知识基础。课堂教学是正规法学教育区别于师徒传授的非正规法学教育的标志之一。课堂教学对法律技能的影响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课堂教学为法律技能的形成提供系统的理论知识基础。法律技能是一种与日常生活技能不同的专业性技能,它只有在系统地占有法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不掌握法律专业知识就不可能形成法律技能。而课堂教学是系统地掌握法律知识和原理的最佳途径。我们看到,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就是通过课堂而传授法律系统理论知识的典型,也就是说法学教育的核心任务是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基本法律原理和知识。在此基础上,或者说在法学教育之后再集中训练法律技能。而课堂教学所传授的系统的理论知识对于技能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是法律技能形成的间接知识基础。
另一方面,课堂教学亦可以为法律技能的形成提供经验知识基础。课堂教学的内容既可以是理论型知识,也可以是经验型(技术性)知识。经验型知识是直接促使法律技能形成的直接知识来源。技能来源于知识,尤其来源于经验知识。普通法系特别是美国法学教育的课堂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例证。美国法学院的课堂教学的独特性始于自1870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对法学教育的改革。兰德尔指出:第一,法律是一门科学;第二关于那门科学的全部有用的材料都包括在出版的书籍中。而这种书籍就是已经判决的判例汇编。但是,兰德尔的关于法律科学以及法律科学家的想法很快就被人们所抛弃或者修正,独具特色的案例教学方式,从那时起就一直成为法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主导方式。案例教学法促成了以经验型知识为课堂主要教学内容的传统。围绕着判例的讨论而展开的课堂教学活动,是一个通过选择法院判决意见并运用批判性分析的方式来学习法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模拟的诉讼程序去感受处理案件的经验。
另外,课堂教学还通过讨论课的形式来训练学生日后从事法律实践有关的技巧,例如法律写作或法律研究(培养迅速检索法律资料和整理法律问题的能力、也培养开展实务的职业规范能力)、民事程序课堂实践训练、争议解决的选择方式学习训练、多方协商训练、法律教学思考、证据演习等等。
总之,就目前课堂教学的两种模式——系统的理论知识教学和典型案例教学来说,都能够为法律技能的形成奠定知识基础。
二、实践教学对法律技能的价值
实践教学形式是训练法律技能的直接途径。技能属于一种直接经验。如果说知识的学习属于“知什么”的范畴,那么技能的学习则属于“知如何”的范畴。技能的学习只能通过观察、模仿、练习和实践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摸索,在做中学,在不断练习中才能达至精熟。实践教学形式将课程内容融入实践过程,为学生提供了获得法律技能的实践空间。法律诊所教学是其典型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