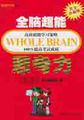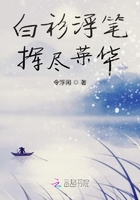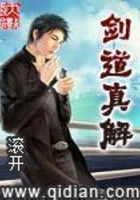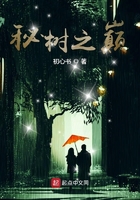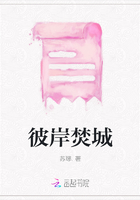“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否则社会所赖以取得的新的发现和明智判断的‘涓细的智慧溪流’将会干涸。”法学自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一直是受到人们倾心关注的智识领域,并且在法律知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也出现了理智分析、鉴别和阐述法律知识的法科大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以大学作为承载机构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遍及世界各地,并且成为打造法律精英,推动法学兴盛发达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了各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我国,随着社会法治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法学教育的重要性也日益为人们所瞩目。考究各种现象的缘由,法学教育自身的巨大价值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书以法学教育的价值为研究视界,以高素质法律人的培养为线索,探讨了法学教育的传授、整合和创新法律知识,训练和提升法律技能,养成和改善法律思维方式,培育法律职业道德,培植法律信仰等方面的价值。其中知识的传递、整合与创新是培养法律人的前提性职能,因而是法学教育的基础性价值;训练法律技能和培养法律思维方式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法律专业人才的操作性价值;培育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学教育所应具有的人文性价值;培植法律信仰、塑造法治人格则是法学教育在实现其基础性价值、操作性价值、人文性价值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或应当发挥出来的综合性和终极性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法学教育在价值实现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参照提出了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进路就在于寻求全面实现法学教育价值的有效机制。
一、法学教育的历史与现实:法学教育价值存在的必然性
(一)法学教育生成的历史必然性
作为人类教育现象之网上的一个纽结,法学教育的界限埋嵌于历史发展之中。研究法学教育的价值首先就要从法学教育生成的历史必然性中去寻找。目前学界,人们毫无争议地将法学教育的最早起点定位于12世纪左右出现的以波伦亚为代表的一批中古大学。法学教育之所以能发端于黑暗的中世纪,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快速发展,追根溯源在于主体(个人、职业、社会)的需要。换句话说,法学教育的“合法性”存在于主体的需求之中。
首先,从人的认识能力的角度来考察,法学教育的出现是人们的学习能力与法律知识发展不成比例的结果。西班牙教育家奥尔特加·加塞特提出了著名的“教育的经济原理”,他运用经济领域的供求或物质稀少会引发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来教育,认为教育出现的原因在于人们要获得的知识与学习能力不成比例。他说:“人类为了能够满怀信心、自由自在和卓有成效地生活必须知道很多事情,但儿童和青年的学习能力都非常有限,这就是原因所在。假如童年期和青年期的时间分别都是持续一百年,或是儿童和青少年都具有无限的智慧和注意力,那么就不会有教学活动存在。”“缺乏学习能力是教育的基本原理。由于学习者不会学习,就必须要为教学作好恰如其分的准备。”笔者认为,这一教育原理也可以用来说明法学教育生成的必然性:当法律知识发展到超出一般人的学习、理解能力的时候,法学教育便产生了。
在以习惯法为社会主要行为规则的时代,人们对于规则的理解和学习完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来完成,因为习惯法与社会生活实践是融为一体的。习惯法形成于社会生活中人们交往的事实,特定社会的人们对这些规则心知肚明,心照不宣。据达维德考察,欧洲在13世纪以前,构成法律体系的成分主要具有习惯的性质。所以罗马法的汇编,即使是简化的版本,在此时也显得太深奥、太复杂了。当11世纪人们在意大利的一家图书馆发现了古罗马法的手抄稿时,人们理解方面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由于罗马法的深奥程度超过了常人的理解力,因此,当时学习罗马法的人都是受过文科教育(即学习了语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的人,即接受过文科教育是从事法律学习的一个先决条件。早期法科大学便在人们对深奥的罗马法的学习需要中诞生了。
在近代,法学教育获得了蓬勃发展。从人的认识方面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律的专业化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法律知识成为专门化的知识系统,成为不经过专业学习就无法深刻领悟的领域;另一方面,随着法律的社会化,法律所涉及的领域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知识在知识量上获得了巨大的增长,人们要把握远远超出学习能力的大量法律知识,就必须进行专业学习。因此,法学教育就成为满足认识能力有限的人们学习法律专业知识需要的必要手段。
其次,从法律职业的角度来看,法学教育的生成是适应法律职业发展的需要。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之一是法律的施行被委托给一群特别的人们,他们或多或少在专职的职业基础上从事法律活动。这便是与西方法律自治传统密切相连的法律职业专门化的倾向。法律职业是一种这样的职业:它要求法律职业者要精通法律知识、熟悉法律操作技能、要有法律智慧、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和有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的法律品格。法律职业对其从业者内在的精英品质的要求,必然推动专门的以打造法律精英品质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的出现。法学教育就是伴随法律职业化的脚步生成与发展的专门化的教育机构。伯尔曼曾指出:“法律职业者,无论是像在英国或美国那样具有特色地称做法律家,还是像在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那样称做法学家,都在一种具有高级学问的独立的机构中接受专门的培训,这种学问被认为是法律学问,这种机构具有自己的职业文献作品,具有自己的职业学校或其他培训场所。”因此,法学院通常被看成是法律职业的守门人。对于那些被允许进入法学院的人来说,法学院是法律职业的入场式——所有法律人都要经历的仪式,职业共同体的基点。
最后,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看,法学教育的生成是为满足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在中世纪的中后期,商品经济渐渐萌生并在一些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南欧诸国的很多城市如波伦亚、萨莱诺、蒙特利尔、那不勒斯等地成为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商品交换需要统一的法律规则,统一的罗马法因此而得以复兴。罗马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仅需要能解读罗马法的法学家,更需要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法律讼争的法官和律师,这是激发早期法科大学于波伦亚等商业发达城市生成的经济原因。从政治方面来分析,早期法科大学也是世俗政权与教会争夺统治权,实现政治统一的需要。以君主为代表的世俗政权,为了集中王权,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需要一种统一的法律支持,而含有君主拥有绝对权力的罗马法则能够满足君主的需要。政治上对罗马法需要的结果同样也必然促成法学教育的产生。“国王们为了更方便地支持那些以根据权威与先例为借口的战争,就借助于目的在于造就法学家的那些学校,国王们需要用法律学家来反对教士。”
(二)法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必然性
当代社会,法学教育置身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潮流之中,其发展壮大获得了充分的外在条件;法学教育又面临着社会法治化、法律的社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的发展态势,其发展获得了必要的外在条件。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典型的经济形态和政治模式。我国也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内在地需要法律,这种紧密的关系体现在“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和“民主政治就是法治政治”的经典命题之中。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商品交换的规则、交换结果的确认和交换过程中出现的纠纷都需要法律的调整,据此我们可以说没有法律就没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是也必须是法治经济。法律是现代社会政治的一种常规形式,因为无论何种政体的政治统治,都必须采用合法的形式有规则、有秩序地进行,法律和政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法律的内在关联性,决定了法律在社会治理手段中的至上地位,同样也决定了以培育法律人才、推进法律革新和进步为使命的法学教育的存在、发展和在社会中的地位。美国学者罗伯特·斯蒂文斯深刻揭示了法学教育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美国的法学院被认为不仅是法律职业权力的中心,而且也是塑造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的重要力量。在我国,法学教育因其担负着为当今法治事业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的重任而取得了法治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反过来说,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法学教育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是法学教育存在发展的充分外在条件。
社会法治化、法律的社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态势。这一发展态势直接影响并将继续影响法学教育的发展。
首先,法律的社会化、职业化意味着:一方面法律取得了社会中的至上地位,表明了全部的社会关系被置于法律调控之下。因而法律知识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法学达至人类历史发展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另一方面,法律规则的普遍化又使得学习法律成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将不得不像学习劳动技能、生活经验、道德规范那样学习法律。但是在法律知识暴增的今天,受人的认识能力所限,人们要系统掌握法律知识原理只能接受专门的专业教育;任何个人要选择法律职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也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法学教育。所以在当代,人们对法律知识的需求更加热切。这也是人们常常慨叹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院系是众多学子孜孜以求的热门专业的理由之一。
其次,社会法治化、法律职业化也意味着:社会不仅需要知法、懂法的民众,更需要精通法律精神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这种需要表现在人才的量和质两个方面。从量的方面来讲,法治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它需要法律精英充实到法律职业,推动法律制度的良性、高效运作;它还需要精熟法律之人充实到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这种需求量是巨大的。从质的方面来讲,当代社会对法律职业人才的素质要求是全面的,包括了知识、技能、思维方式、职业道德和法律信仰等多方面的内容。这种需求是高标准的。高标准的法律人才的社会需要,将法学教育置于法律领域的基础地位,担负起培养满足社会所需法律精英人才的根本性任务。
再次,社会法治化、法律科学化还意味着法律制度需要科学的、理性的法学理论作为智力支持。具有发展、创新法律知识功能的法学教育责无旁贷。韦伯曾经这样论述法学教育与法律制度的关系:“培训法律专家的法律学术机构与法律制度有着复杂的和辩证的关系,因为一方面这种学术描述该种制度,另一方面法律制度通过学术专著、文章和教室里的阐述,变得概念化和系统化并由此得到改造,如果不这样,法律制度将彼此分立,不能被组织起来。换言之,法律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等,而且还包括法律学者对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所作的阐述。”另外,法律科学化还需要有献身法律研究事业的人才,法学本科教育作为法学专业教育的基础,无疑还承担着培养深化法学研究后续人才的基础性工作。
回眸历史,历史向我们叙述了法学教育生成的历史必然性;检视今天,今天证成了法学教育是在满足诸种主体的需求中向前发展的事实。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法学教育的存在,不仅在历史上有意义,而且在当下社会中其意义更为凸显。
二、法学教育的属性与结构:法学教育价值存在的可能性
“一个机构越是富于包摄或完整性,就越是对其成员有影响力。法学院(系)像其他的社会机构一样,具有‘包摄的倾向’”,“换言之,就是捕捉其成员的时间和兴趣的能力。”法学教育通过其承载的机构——法学院独有的教与学的机制,使学生学着像法律人那样看待世界,学着运用法律技巧解决实际问题最终使学生取得了专业态度和身份即完成了专业的社会化的过程。因此,法学教育价值存在的可能性在于法学教育本身的属性与结构。
(一)法学教育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