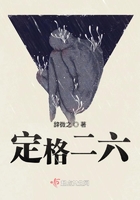现在。我走进了这所花园式的学校,却还是找不到生的方向,感觉又回到了小学、中学,那种学习方法,那种授课方式,简直让人窒息。学校一味强调要我们记住自己是落榜生,争取拿到那张文凭,这当然会引起我的反感。我们又不是弱智,用一张卷子划分人的档次我不服,我从不以落榜者自卑,这世界原本就有许多路,我不是死走一条路不放的人。而作为学校强调文凭的说法更让我气愤,我不否认文凭的重要性,但文凭若脱离了能力的轨道,那么文凭只是一张白纸而已。班主任挽留我的理由是3年后我能拿到一张文凭,我说那又能说明什么?他说能证明你受过3年高等教育,我说仅此而已!我告诉他,你的要求我做不到,你不准去图书馆我做不到,你让我一天到晚坐在教室里我做不到!即使我留下,你的许多规定我都做不到,你也管不住我。在学校的广告宣传上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当今社会。英语、计算机、汽车驾驶是多么重要。否则就算有那张大专文凭,也只是一个新时代里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不会写字的文盲。可学校倒好,听说明年我们这届要过听力和口语关,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却故弄玄虚把同学们吓得倒吸气;计算机呢,是基础,而且稍有一点深入的老师又说不讲了,就那么点东西,学过之后你也不能说没学会;而汽车驾驶呢,也只能演习不能实际上路,近似开卷的考试好拿文凭,可人的通病是,对轻易到手的东西不懂得珍惜。那张文凭廉价地给我,我不会稀罕。
也许是我想得太多了,也许是我看得太深太远对外界太敏感了,也许是我犯糊涂了。但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因为我的视觉和敏锐,我习惯于倾听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和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只不过是为自己在未来争得生存权。
我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虽然有一段时间会表现得很乖很听话,但只要有个引子,叛逆的人格迟早会再现。在一所又所学校中,我被迫压抑自己的智慧和天赋,去迎合学校的教育,也在一天一天中迷失着自己。现在,我作出了20年来最狂妄的决定:不想把生命完全交给学校,我要炒学校的鱿鱼;也不想再做好孩子,其实我早就不是好孩子了,只是现在正式宣告而已。我的记忆力很好,但在题海战术中已很疲惫,思维也越来越僵章化,所以我现在决不会轻易为空洞无物的理论及说教浪费脑应试细胞。教此次我退学的意义也不仅仅是针对现所在学校,可以看月做是向旧的应试教育的挑战,我知道这对我会付出沉重的代氅价,但我依然选择离开。我不在乎这封信公之于众,但请您辜不要写我现在学校的名称和我的姓名,这个年代不需要英雄,我也不想借此出名,只是有些事实需要有人来听听。
我想先找个工作,但我会继续学习,学真正应该学的东西。我知道迟早还会再进学校,但我不想再进入这类学校了。目前仅有那么几所重点大学在搞试点,而我写不出标准答案,自然没有这个福分。如果有人知道比较容易进又符合素质教育的学校请转告我。
不管我以后做什么,我都愿为我所钟爱的事业儿童教育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此致
晓晖
走进逃学生的精神世界
一位叫秦树洪的记者曾在一篇题为《逃离校园的中学生》的报道中这样描述逃校学生的生活。
小海他们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之一角,更多的孩子在重重压力下根本就冒不出来。我们的学校太不尊重孩子的个性和自尊,更不要说权利了。不愿朗读为什么就是胆小鬼?抽象画为什么就无权展出?老师对学生的批评、责骂为何如此慷慨,欣赏、夸赞为何如此悭吝?
是让孩子适应陈腐的教育制度,从而抹煞他们的天赋,还是让教育适应孩子们,从而培育出跨世纪的人才?这的确是一个跨世纪的话题。
我怕学校,怕老师,怕所有的同学
我们不会生活,也不想知道怎么去生活;你别告诉我,我根本就不想生活。滚到、滚到、滚到一边去。酒吧的天花板不高,此刻风雨不透的鼓点淹没了小海的歌词,一堆乱七八糟的声音刺破屋顶,直窜夜空。
小海今年刚满18岁,搞摇滚已近两年。16岁那年,高一读到一半,小海就再也不想上学了。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初中到高中,他受教育的地方,说出名字来,都是首都最有名气也最令人羡慕的学校。乐队里,只有他写歌词,至今已有十几首面世。小海说他的歌都来自生活经历,属于触景生情。
小海自己组建的朋克乐队名气不够大,一般每个周末在酒吧演出几乎没有收入,他们几个人的生活主要靠家里。有一天晚上,酒吧老板一共给了乐队3个人50元演出费,这已经让他们感到兴奋。小海知道18周岁意味着什么,他希望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小海刚从学校退学时,虽然也喜欢音乐,接触摇滚乐队,但还是天天回家的。后来他白天睡觉,晚上有时和乐队的伙伴们排练,回家的时间逐步后延,有时夜晚十一二点,有时快到天亮才回家。
小海住在奶奶宽敞的房子里,看他每天昼伏夜出的样子,奶奶免不了担心和唠叨。小海和奶奶的关系开始变坏。现在,小海有时连续几天不回家住,每天给妈妈打个电话。跟那些或长发飘飘、或戴耳环、或染黄发红发的摇滚乐手不同,小海没有任何奇装异服。舞台下,小海更多的是沉默。他那双有些发直的眼睛,总让我觉得里面藏着很多痛苦。我怕学校,怕老师,怕所有的同学。
在学校我根本体会不到学习知识的快乐
我从小学开始就讨厌学校,80%的老师都要找我麻烦,尤其是班主任。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朗读比赛,有一个司学朗诵得最好,得了小红花,老师问我们:大家想不想比他更好?想读得更好的同学举手。全班同学就我没举手,因为我不喜欢朗读。老师说:就小海是个胆小鬼。我真不明白,不想朗读怎么就是胆小鬼了?五年级时,我跟教师顶嘴,被停了两天课。我和老师说,我有错,你给我处分都司以,但你不能停我的课呀。可有的老师就是不跟你好好讲遭理,他跟你耗着。
我的人际关系总是不好。初中时老被同学打,别人看见也不管,老师也看不见。上初一初二的时候,班级排位子不是按高矮个排,而是按学习成绩排。我其实都不想参加中考,那是一种没人性的考试。但是我意志不坚定,最后又好好学习,去参加考试了。
上高中我在S学校。我们高一新生一入学,就开了好多会,非说高一很难,三年高中要两年完成,说必须得考上大学。好像考不上大学就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了似的。当时我就很反感,我们都知道学习紧张,你就别另外再说紧呀,搞得大家学习都很被动。本来是想激励学生,但并没有收到这个效果。
开始我还认真了一段时间,那两月挺上进的。我刚上高一时,每天放学回家先歇一小时,6点开始写作业,除了中间吃饭,一直要写到10点,有时还要更晚点儿。早上6点起床跑步,有运动会时,我早上5点多就起来跑。到冬天的时候更紧了,晚上作业写到十一二点,仍然写不完,就早上3点起来写一个半小时,然后再睡会儿,起来去上学。这样我坚持了两个月,发现也没有多大进步。后来我也觉得没劲儿了。就这样学,一共8门课,第一次月考时我及格了2门,第二次及格了4门,期末时我8门只及格了1门。
学习不好有我自己的原因。初三时我坐第一排,到高中给排到六七排,我眼睛视力不好,又不习惯离老师那么远听课,上课时老走神儿。有时想听课,可5分钟后就走神儿了,再想听就听不懂了。
在S学校我其实也没特别好好学,好好学也学不好。这教育制度有问题。
我就是心里烦,在学校根本没体会到学习知识的快乐。外边都说我们学校各种设施如何如何好,但有些地方根本不让普通同学进。像体育馆,只有体育队运动员能进,所以也没觉着学校特别好。
现在我回头想想S学校,觉着特没意思。我有时就想,要是有塑料炸弹,就炸了它。学校里有的老师也没人性,都是误人子弟。
高一第二学期我一天都没去,我没有任何义务考大学。以后我有了工作,能赚钱给家里,就是尽责任了。我正在一所职业学校读高中取证,学语文、数学、地理、政治、历史5门课,一星期3次课,一次两小时,明年1月毕业。有一次我没完成作业,是因为题都懒得抄。第2天我逃学了,第3天只好躲在地铁里写作业。地铁里的人都特别忙,不会注意我。
我们乐队的吉他手肖力是河北的,初中就不上了,上了一个夜校,现在他在B大学附近租了一门地下室住着。厉来的鼓手余辉也是我们S学校的,现在已经出国学习了。健初中太能闹了。有个老师说:要是还把他留在学校,我裁辞职。
谁来帮助这些从学校流失到社会上的孩子?
小海在家里与奶奶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奶奶仍然用自己的方式挂念着孙子,为孙子的现状和前途担忧。这位在品争年代参加革命的高级干部不明白:这孩子怎么会到这一地步?奶奶说:我现在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头疼创就是这第三代。我在家里很难与他交谈,他有话跟朋友说,不跟我说。我一跟他说话他就捂耳朵,说:你不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吗?
奶奶问:谁来帮助这些从学校流失到社会上的孩子?她说:现在有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上不起学,我们搞了希望工程,但是城市里有条件上学的孩子却辍了学,谁来管呢?这些孩子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志向,没有希望,没有灵魂,他们其实最贫困、最脆弱。他们最容易让人看不起。
小海的妈妈是一名普通机关干部,文革中和许多同学一道在山西农村插队。
儿行千里母担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曾经寄予了父母很多希望的儿子小海,还在身边就开始让妈妈日夜操心了。小海晚上不回家睡,当妈的就一夜一夜睡不好,有时就坐在小海的床边等。
妈妈说小海像现在这样在社会上晃,我也不是很情愿。但也不能强拦着他,我只能是引导他交一些好的朋友。刚开始我看见他那些头发长的朋友,特别担心,怕他进了那种不好的圈子。但我如果还想对他有些约束,就不仅是他的母亲,还得是他的朋友。我不能排斥他的朋友,要用真诚对待他的朋友。我有时候问小海,他们从哪儿来啊?家庭状况怎么样啊?小海说,他们都是挺朴实的人。在这个圈子里他觉得平等,谁都可以是领导。
确实,他那些朋友的父母大多是老三届,家庭也都是非常正统的。他们也不是那种干违法事情的孩子,像吸毒、性乱交什么的。这些孩子的特点就是都喜欢摇滚乐。他们现在搞的音乐和我们理解的音乐不同,但社会都不否定,我们凭什么否定?
我现在最怕他和吸毒的混在一起,接触毒品就是接触死亡。我们不敢去他演出的酒吧,怕激化矛盾。其实孩子不是不愿学习,从S学校出来以后,他在一所外语大学读了半年外语,又读了3个月的《走遍美国》,还拿了中级调酒师的证书。我也并不想让他拿回什么,而是让他和社会有接触,尽管这种接触有风险。开玩笑地说,是想让他上高尔基的社会大学。我为什么把小海放出去,不把他圈在家里?因为他将来还是要离开家,还是要接触社会。现在和我们那时不同,那时一为国家,二为集体,现在都为个人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