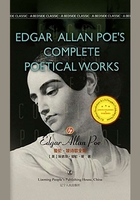No.5 贾桃花
如果根宝早回来一个月,我就不会嫁给何初明。
何初明是不错,长得比根宝斯文,又有着手艺,自己开按摩诊所。
“跟了他,你轻松又体面进城去当太太,只要伺候好初明,其余万事不用操心……”媒人吴婶说。
“你等根宝要等到什么时候?你知道他小子有没说上城里媳妇,我看他不见得靠得住。你也不小了,过年就叫二十三了……到哪里去找何初明这样模样又好又有手艺,性子又温和的男人?”还是吴婶说。
“可他是个瞎子啊……”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嘁,桃花,不是我说你,你可别怪婶子我说话直,他不是瞎子,能轮到现在挨着你?你是个老实勤快姑娘不假,可论模样,他是瞎子看不见你,桃花你可不瞎,这样的俊男人,天天伺候着,也怪美气……应了吧,这就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气……”还是吴婶说。
何初明压根就没说一句话。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脸露微笑。那微笑,也不见得是渴望的微笑,即使吴婶说破了嘴,我若还是不答应,我估计,他也会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微笑着。我在心里叹了口气,竟然就答应了。
凭良心说,何初明对我真不错。他是结婚的第三天晚上,才摸过来和我圆的房。我想起谈恋爱时和根宝,心里有些着慌,还好,他看不到,心里反过来,又有些庆幸。
我在床单上加了块四方形的小布垫,这是我们那的规矩。完事以后,我悄悄端起何初明的茶杯,往上面泼了些水。
“初明……”我捧着那块小布垫,将他的手摸上去。他并不愿意摸。我很清楚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头似碰非碰地触到小布垫上泼了水的湿处,一触即分。我在瞬间,觉得有些耻辱。我想,何初明一定有同感。受辱和施辱,同在。
“你也累了,早点睡吧。”他眼睛望向窗户的地方,对我说。我在窗户的对面。我将那块小布垫从窗口抛了出去。
根宝来寻我时,何初明正在里屋的按摩间工作。根宝清秀的脸和瘦长的身影,象梦一样出现在我眼前。我忍不住轻轻脱口而出,“根宝……”
根宝没有等我话音落下,便上来用嘴堵住了我。哦,根宝,我的根宝。我的身体,由始至终插了一面忠贞又背叛的旗帜,现在它醒来了,在猎猎风中,妖艳招展,但我的心,因为内疚,哗哗流泪。我一边和根宝热烈拥吻,一边伸手指了指按摩间的方向,那里,连着客厅的,是一扇不透明的推拉玻璃门。根宝一刻也不停地吻着我,将我的手按了下去,又移动身体,和我换了个方位,他的背影,遮挡着我的目光,我看不见那扇推拉门。
根宝一把将我抱起,要往我和初明的卧室去。我不肯,但我又渴望。根宝好像变成哑巴,他一句话也不说,又拖着我,走向了厕所。厕所距离按摩间更远一些,中间隔着客厅。我竟然不再挣扎和拒绝。根宝褪下我的裤子,将我反身摁在马桶上,他从我的身体后面,一声不吭地,长驱直入。我的耻辱和欣喜混在一起。拒绝不了,动弹不得。
“是谁?”问话的是正在动作的根宝。这是他与我见面以来,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我魂飞天外。
那个来按摩的女人,为什么会在一次按摩服务的中途忍不住要上厕所呢?是什么原因,使她膀胱的忍耐度如此狭窄有限呢?她穿过客厅,奔向厕所。她隔着一扇不透明的毛玻璃,看到了根宝和我。
“她受了刺激和惊吓,返回去时,在客厅中央不知绊了什么,跌倒了。”根宝在和我做爱时,也保持着敏锐的听力。他真有点象福尔摩斯,分析得头头是道。
女人什么也没说。她重新爬到按摩床上去。我认识她,何初明将她错认成他初恋的女朋友柳小樱。她又来了。根宝和我匆匆完事,他一语不发,镇定撤离。我忐忑不安,端了一杯茶进去。
“初明,你喝口茶。”我说。顺便瞟了一眼按摩床上的女人。她闭着眼睛。
“花儿,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随便在我工作的时候自说自话端茶过来,这里有客人。”何初明非常不悦。但他还是停下手来,我听到他低低地对那躺着的女人说,“对不起”,我赶紧掀开茶杯盖子,将茶递到他嘴唇边。
“花儿,你怎么,一身骚气?”何初明喝了茶以后,毫不客气地对我说。
NO.6许根宝
我原来在村里是做代课老师的。去了城里以后,先是去做了餐厅厨房的配菜生。大厨很信任我,将算账之类的活儿也交给我。我们包厨一共是六个人。我学得认认真真,干得兢兢业业,但那个看起来最信任我的大厨,却分给我最少的钱。比做一个餐厅服务员的钱还少。我问他为什么?他还是一脸老实相地回答我,“不为什么,就是看你不太顺眼。”我把清清楚楚的账本交给他,然后卷了铺盖走人。
然后我混入民工一路。每天等候在天桥,蹲在地上,低着头。身边竖着一块好像卖身的牌子,上书二字“刮白”,偶尔,我也象练习书法一样,换成“木工”。我很努力。手掌起了泡,我也并没有怜惜自己,但我的同行们还是很惬意地嘲笑了我。它硬是有一个起泡的过程,你叫我有什么办法?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妄想过得到这些所谓同行前辈们的关照和指引,后来,这种妄想,混在我手上的血泡中,成为永恒的阴影,所谓“泡影”。
人生路,崎岖漫长,我原本,真的想做个努力前行的快乐少年郎,赚自己的血汗钱,娶我如花的新娘。但那只是原本。
那天来天桥挑小工的是个女人。雇主来的时候,大家都一窝蜂涌上前推销自己。我看见前辈们涌上去了七八个,知道又轮不到自己,索性干脆蹲着不再争取。我那天情绪不好。我象女人每月来例假前会折腾一阵一样,时不时地会情绪不好。我已经好久不见桃花。我想回去。但是我拿什么面目回去。可是那个女人点了几个人头之后,很温和地冲我招招手,“弟弟,来,还有你。”我楞了一下,抬起头,手拢在袖子里蹲着,并没起身。
“来来,弟弟,别看了,就是你,你也来……”我不知女人为何叫我弟弟,但这个称呼,简直就象一壶意外遭遇的暖意,差点将我冷冻的心,熏出点点泪意。
我在那个女人家里拼死老命干。有个前辈,叼着劣质烟卷嘲笑我,“根宝,悠着点吧,你当这是干啥?这是干活,你干得再卖力,结账时,该咋算,还是咋算……”
我爬高爬低,拿着油漆刷子蘸着涂料在墙上刷。我果然 就眼前一黑,一个跟斗栽倒下去。
其实我就是犯了低血糖。我醒来的时候,半躺在这个雇主女人的怀里,她拿着勺子,在喂我喝白糖水。同行前辈不知咋的都走了。
“我叫他们今天散了。”女人说。
“可活儿还没做完。”我说。
“明儿再做,今天放假休息。哎哟,来,弟弟,我搀你起来,到沙发上躺会……我去买两条鱼给你熬汤。”女人说。
“不不不,大姐,那怎么好意思,太过意不去。你家里 ,你看,刚弄好房间,厅里还乱着,哪能还麻烦你照顾我?”我说。
“呆着吧弟弟,我一看就知你不是干这个的料,但没的叫人心疼。”女人一边说,一边回房间去,我眼见她取了钱包站在房门口,打开,抽出两张一百,就又合拢了钱包,就那么站在房门口,踮起脚尖,将钱包往床上一扔。然后女人就出门买鱼去了。
人性的光辉与人性的黑暗,往往同在。我喝干了白糖水 ,然后偷了女人的钱包离开。那里面有八百块钱。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做民工,我成了小偷,专偷女人。
我渴望通过偷这条捷径,快点存钱,然后快点回到桃花身边。“衣锦还乡,洞房花烛”,我一直是个诗意的小偷。
我存够了两万块钱,回了家。但桃花已经嫁了人。嫁到城里,做了太太。丈夫开家推拿按摩诊所。她的丈夫是个瞎子,一个英俊的瞎子。
我常常偷偷跑去看桃花。如果她幸福,我就躲得远远。我依旧在城里,以偷为生,还是专偷女人。这个推拿按摩诊所,有两个比较固定的女人来光顾。一个看上去,象是琼瑶小说的女主人公,好像一直在做梦,虽然她其实已经有点老了。她倒是和按摩的瞎子很登对。我亲眼看着瞎子带着泡妞的表情和她套近乎。她依旧带着梦游的表情,但她很冷淡地拒绝了瞎子。另一个看上去象江青,是个一本正经的女干部。但就是她,在按摩床上,被那个瞎子捣鼓了最不正经的事情。她一下都没拒绝,应该还有所鼓励。我突然非常嫉恨瞎子。要是我也搞瞎了自己,不是也可以开一个这么美气的推拿按摩诊所?
那天,我看见瞎子又在捣鼓按摩床上那个女人。我没有看到桃花的幸福。我也舍不得搞瞎自己。所以,我就闯进去搞了桃花。她本来就是我的。
可是我看错了。这次那个被瞎子在按摩床上捣鼓的女人 ,不是那个江青似的干部,而是琼瑶小说的女主角。这是我已经搞完了桃花,跑到外面来仔细观察发现的。这个梦游的女人,她到底是忍不住。就象她被他捣鼓的,忍不住要在按摩的中途,上一趟要命的厕所。
那天晚上,那个女人仍然带着梦游的表情离开。我躲在按摩诊所对面的灌木丛里。我听见瞎子说,“小樱”。女人抬起头,看着瞎子,半天才说,“南良,可是我现在叫柳明月”。瞎子继续肉麻地说,“你永远是我的小樱”。
我搞不懂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叫瞎子“南良”,我问过吴婶,她告诉我桃花的丈夫叫“何初明”。
我又跟踪了那个女人,象上次一样。快到五十六路公交站头,女人忽然回过头来,眼神犀利,状若女鬼。她声音低低,但是气贯长虹地问我,“说,为什么一直跟踪我?”
“喏,我是还你的钱包和钥匙。”我只好停住脚步,把本属于女人的东西还给她。
她紧蹙双眉,呼吸急促。半天不接我递过去的钱包和一串钥匙。
“喂喂,拿着呀,你钱包里一共一千三百块钱,我动也没动,你点点……”我说。
“一千三,你说只有一千三?”女人好像忽然还了魂,讨价还价似地问道。
“嘁,不是一千三,你还以为是多少?要是一万三,我肯定不会还了……”我说。
女人点了钱,慌里慌张将钱包和钥匙放进背包。正好五十六路车来了,她慌里慌张跳了上去。她跳上去以后,忽然从窗口丢下一句很大声的“谢谢。”
夜色还是很黑,我看不清她的脸,我想她一定是脸红耳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