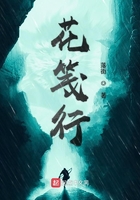在承受的人生的种种苦痛时,我选择沉默,恨不能将自己肉身碎了,让所有惦记的朋友,找不到我的消息;在享受一丝丝的人生奢侈时,我却又好了伤疤忘了痛,我选择卖弄。
十一月,初冬时分的午后。阳光好得象新一代君王的恩宠,任你如何俏皮,甚至咋着胆子略略放肆,他都包容性很好地微笑着,温暖着。其实,我不在君王的怀抱里,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我在娘家的阳台上。
阳台旧到已近三十年的历史。历史中,有一个六岁的剪着齐耳短发的小女孩的身影和眼神。她在这阳台上,从懵懂,长成豆蔻,然后揣着有关阳台的回忆,从豆蔻,跋涉到了沧桑。她在这阳台上迎接过春夏秋冬的四季朝阳,她在这阳台上仰看过月落乌啼的满天星光,最是那黄昏时分,万盏人间灯火将亮未亮,蒙蒙夜色将暗未暗。炊烟在树梢的孤影里缓缓流动,倦鸟在灰青的天际啾啾而鸣。落日,是一个橙色的琥珀圆盘,它将女孩在阳台上埋头读书写字的剪影收进去,收进一片渐落的橙色光芒里去,做成一枚不朽的回忆。
时年流转,世事轮换。能在娘家的阳台上,重温读书写字的旧梦,我原本想也不敢想。有那么多旧的故事,任回忆不老,却是无路回去。三十五年的飘零肉身,天涯处处,有时哄着自己忘了回忆,有时裹着自己断了温情,而一旦时空隧道,开一扇恩赐之门,我便穿着追云逐月的溜冰鞋,一路飞奔一路紧追,只因不舍。
我现在就在娘家的阳台上写这篇《这样的人生奢侈》。旧的儿时的小桌子,小凳子,早已不适合现在我的尺码,但我执意要用,就用这不适合的尺寸,去还原心底苦苦索要的奢侈。而岁月流逝了,时代也进步了。当年那个六岁的小女孩,现在是一个人到中年,有点蠢笨和放肆的妇人,她不再使用铅笔盒作文簿。她开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戴着耳机,酷狗里反复播放着一首女鬼唱的“誓言幻作烟云字,费尽千般相思……”的歌曲。她年老的母亲在阳台内的房间里午睡,她便小心翼翼地带上阳台的门,窗户开了小小的一丝缝,刚好可以穿过电脑取电的充电器。阳光照耀着逐渐失去风华的筋骨,无限舒畅,她却又害怕那舒畅的阳光,肆虐了她并不再特别年青和姣好的颜容。世事的四角俱全十全十美,其实,就在一串又一串的智慧谦让和委曲求全里,她将她那件颜色鲜艳的薄呢外套,豪迈地顶在头上。阳光依旧酣畅温暖着,而脸上的皮肤,也被巧妙地保护着。其实,那还是儿时的记忆。将外套罩在头上晒太阳,是二哥哥的绝招。
二哥哥常常歪在一张旧得似乎立刻要散架报废的藤椅上晒太阳,就在阳台上,这一样的十一月的小阳春天气。他总是将他藏青色或是黑色的外套,得意洋洋地罩着头脸,一副无限满足惬意状。她的外套,六岁小女孩的外套,多半是粉红的,或是嫩黄的,宝蓝的,但二哥哥说,女孩子是不可以将外套罩在头上晒太阳的。她问,“为什么?”他答,“不为什么。”
而她今天终于这么干了,将鲜艳的外套罩在头脸之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码字,还一边听音乐。她突然觉得享受了人生的无限奢侈,忍不住要深情卖弄一下。她的二哥哥,当然现在还是她的二哥哥,他成了一个辛苦的中年男人,艰辛隐忍里,又有着微微的傲气,那傲气,多半竟是和性别有关。那艰辛,也更多地和性别有关。他今天正组织了他的客人,在外奔忙。
于是,她决定要认真写这篇《这样的人生奢侈》,晚上二哥哥回来的时候,她要给他看。她还要告诉他,她在阳台上,写连载小说了,她会认真地请教他,咨询他,就象小时候,他和她在阳台上,齐心协力帮母亲绕毛线团。
阳光移过来了一片。我一边敲击着键盘,一边带着一种微微醉醺的情绪,《红楼梦》里的豪情女侠湘云,小时候,是个说话口齿不清的爱八哥儿,她老是一叠连声地追着宝玉“爱哥哥”,“爱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