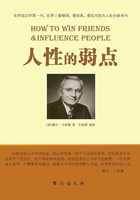“咱女人一辈子活的不容易,你也是当娘的人了,婶子这话一说你就明白,我闺女生下来就傻,十几岁了也没明白过……”
说到这里苏婶子自己也是一阵糊涂,傻丫原来一直是傻乎乎的,吃饭连饥饱都不懂,现在的闺女还算是个傻子么?
“不管怎么说吧,婶子知道你是看不上她的,觉着我家傻丫配不上你家识文断字的岚笙。”
“婶子,您快别说这话了,那时候是我见识短,才会和夏至闹成那样……”一听苏婶子提起了旧事,闵青兰更觉得的惭愧,一时间思前想后的,她满脑子都是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为了她和周存孝手头宽裕点儿,月月都去贪弟弟的那点儿廪膳费……真是越想越不堪!
“是啊,旧事儿咱都不提了。可有一样儿,婶子得和你说说,以后和傻丫别老拧吧着,她现在是你闵家的人,我这个当娘的管不了太多,倒是你这个当大姑子的要多担待了!”
“婶子,我知道了!”闵青兰被苏婶子的一番话说得无地自容,只能红着脸垂着头应了。
“娘……”苏夏至一直静静地听着这一世她生身母亲说的话,泪水慢慢地盈满了眼眶。
从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刻起,她便认为自己是一个孤魂野鬼,娘不疼哥哥不爱的……
乃至后来她口上虽然叫着他们‘娘’‘哥哥’,可到底没动过几分真心。
只是本能的维持着彼此之间的那么一点点联系。
曾经以为,他们这样的人,几辈近亲成家,人早就淡漠的忘了血脉亲情。
孤独惯了的人,总是分外的渴望温暖。
所以苏夏至在大大咧咧的性格下面隐藏着一颗分外纤细的心!
那是她作为女子最为柔软的一部分,她把它小心的藏好,从不展现在外人面前。
直到她遇到了秀才,然后凭着一股傻×似的热情拼了老命的去追逐,那时,她都不懂自己为何会如此执着的去做这件事。
现在她明白了!
原来,她一直都害怕孤独,害怕寒冷!
原来,被她隐藏的最深的那部分柔软才是最初的苏夏至!
原来,她一直都在渴望着温暖……
因为对感情的执着,她收获了闵岚笙全部的热情。
因为骨子里的善良慈悲,她同样收获了母亲的亲情与哥哥的爱护,他们都是她这一世割不断的血脉至亲!
日子是过出来的,人心是暖出来的。
如今的日子,如今的丈夫,如今的母亲和哥哥……她还求什么呢?
苏夏至走过去,用力的抱住了老娘的肩膀,像个小孩子一样把头靠在娘的后背上轻轻地叫道:“娘……”声音哽咽。
苏婶子被闺女这么一抱,只觉的后背上跟趴了一只狗熊似的,弄得她浑身的不自在!
自从老头子去世以后,她有多久没和人这么亲近的呆过了?过了一会儿,见闺女还没有起来的意思,苏婶子摇晃了一下身子,回头对着她说道:“闺女,快做饭去吧,今儿为了给幸福贤婿送行,我们都没吃早饭呢,娘都饿的前心贴后背了……真背不动你了!”
“……”一腔温柔的趴在老娘背上撒娇的苏夏至被苏婶子搂头盖脸地泼了一盆子冷水,算是彻底醒了。在杨巧莲和闵青兰止不住的笑声里,她面无表情的滚去了厨房做饭,觉着自己的感情是用错了地方,完全对牛弹了琴!
过了晌午,把式叔回来送信,告诉苏夏至闵岚笙已经坐上管府里派的走长途的马车进了京,同行的还有几名一起赶考的举子,让她不必担心。
苏婶子在闺女家里待了半天,终是放不下家里的一百多只鸡,又准备离去。
把这一家老老小小的安排上了把式叔的骡车,苏夏至看着车子再次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倒是没了早晨秀才离开时的失落。
用手轻轻的按在了自己的肚子上,苏夏至想感受下孩子的存在,哪知她才一愣神,六婶子就大呼小叫的跑了过来:“秀才家的,你这是咋了?是身子不舒服吗?婶子扶你进去吧……”
“呵呵,没事!”苏夏至对着六婶子咧嘴一笑,扶着她的手臂往台阶下走去:“咱到学堂的院子去看看,我觉着那厨房还得盘个灶才行。”
你来我往,这就是日子,感慨多了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累,苏夏至对自己说:还是该干嘛干嘛吧……
从菩提庵请回《普门品》,小厮和安逸就开始没日没夜的抄写,除了年三十晚上两个人一起包了顿羊肉馅的饺子,平日吃饭都是简简单单的煮一个菜再蒸几个杂粮饼子。
苏夏至虽然又给了小厮一两银子,但主子现在的身子只能靠吃药调理着,所以尽管手里有钱,小厮也是绞尽脑汁地算计着省钱。
节前他给主子添置了一件缎面的棉袍子。
那几天连着下雪,他们两个又买不起太多的柴火,屋里连个火盆也没有,小厮怕把主子给冻出病来,便咬牙给他加了一件棉衣。
就为这事儿安逸和他发上了脾气,足足的闹了一天,人和疯子一样的,让小厮又急又气又心疼!
因为单单只给自己买了棉衣,安逸是死活不肯穿,逼着小厮自己穿上,要么就再买一件。
小厮舍不得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只能哄着他好歹穿了袍子。
哪知主子是犯了疯病了,非但不穿上那件袍子,还开始脱身上穿的衣衫,并哆嗦着问他:“你到底听不听爷的话了?是不是现在你归了闵家爷就管不了你了!”
看着只穿着里衣的主子一边说话一边直抹清鼻涕,小厮心里都快急死了,再听见他混不讲理的话,小厮心里也气他不懂事,因此说话也重了些:“爷都知道我现在是归了闵家了,就别再说这话,现在身子是您自己的,您要糟践谁拦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