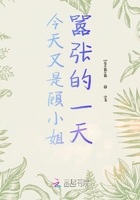1 来到纽约
托洛茨基来到了纽约。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自动化的神奇而又平凡的城市,它的街道是立体化美学原则的成就,而它的道德哲学则是金元哲学。纽约给托洛茨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最充分地表现了现代精神。
关于托洛茨基在美国的生活,传说极多。托洛茨基不过只在挪威路过一下,善于创造发明的当地新闻界就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个洗鳕鱼的工人,而今托洛茨基在纽约度过了两个月,故而新闻界又迫使托洛茨基干了许多职业,而且一行比一行离奇。如果把报纸为托洛茨基描述的各种奇遇写成一本书,也许会成为比托洛茨基此刻所写的这本更为引人入胜的传记。
可是托洛茨基不得不使他的美国读者失望。他在美国的职业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职业。他写文章,办报纸,在工人集会上讲演。他还用很多时间在纽约的一个图书馆勤奋地研究美国的经济状况。美国战备期间的出口增长数字使他很吃惊,也是对他的极好的启示。事实上,正是它们不仅决定了美国的参战,而且决定了美国在战后的和平中的决定性作用。托洛茨基当时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作过许多报告。从这时起“美国和欧洲”问题就一直是托洛茨基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就是现在,托洛茨基仍在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并希望能就此写一本书。
到纽约的第二天,托洛茨基就在俄文报纸《新世界》上发表文章说:“我是怀着革命必将胜利的坚强信心离开腥风血雨的欧洲的。我跨上这个古老的新大陆,并没有抱任何‘民主’的幻想。”
10天以后,托洛茨基在“国际”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说道:“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是欧洲的经济正从根本上崩溃,而美国正在大发其财。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欧洲人,我羡慕地望着纽约,并且不安地问自己:欧洲能支持得住吗?它不会变成一个基地?世界经济和文化中心会不会移到这里,移到美国来?”
托洛茨基一家在一个工人住宅区租了一套房子,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置了一些家具。每月租金18美元的这套房子配备有欧洲人闻所未闻的舒适的设备:除了电灯,还有煤气灶、浴缸、电话、物品升降机和垃圾滑道等。这一切立刻使孩子们对纽约产生了很大的好感。他们一度简直对电话着了迷,因为这个神奇的玩意儿,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都没有过。这幢房子的看门人是个黑人。托洛茨基妻子把3个月的房租预付给了他,但并未拿到收据,因为房东前一天刚把收据拿去查账了。两天以后他们搬来公寓,却听说那个黑人带了好几户人家的房租跑了。除了房租以外,他们还托他保管他们的一些东西呢,他们急得不知怎么好。这是个不好的开端。后来发现东西没有丢。当他们打开装器皿的木箱子时,发现他们的房租钱被用纸端端正正的包着放在里面,这真使他们太感意外了。原来那看门人只拿走了开了收据的房客的钱,他掠夺的对象是房东,不愿意房客遭受损失。说实在的,这真是个绝妙的人。托洛茨基和妻子深深为他的关心所感动,一直感激地回忆着他。这件小奇遇托洛茨基觉得具有很大的代表意义,它仿佛在托洛茨基面前掀开了美国“黑人”问题的一角。
德国人宣布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这造成了美国东部的许多车站、码头上各种军需物资堆积如山,铁路也被堵塞了。消费品的价格顿时飞涨。托洛茨基曾看见这个最富有的城市的几千名妇女和母亲走上街头,愤怒地掀翻货摊,捣毁消费品商店。战后全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托洛茨基问别人,也问自己。
2月3日,终于宣布了人们等待已久的与德国断交。沙文主义的乐曲日益响亮。和平主义者的高音和社会主义者的假声并没有破坏整个乐曲的协调。不过,这一切托洛茨基在欧洲都见过,美国的护国主义运动对托洛茨基来说只是旧影重现。托洛茨基在俄文报纸上指出了它的发展过程,思考着人类在吸取教训方面的愚钝。
美国社会党在思想方面甚至大大落后于欧洲的社会爱国主义。但是,当时还持“中立”立场的美国报界对“发疯”的欧洲的高傲态度仍然在美国社会党的舆论中反映了出来,像希尔奎特这样的人并不反对扮演社会党的美国大叔的角色,关键时到欧洲去调停第二国际各党彼此的嫉恨。现在,托洛茨基一想起美国社会党的那些领袖们就觉得好笑。他们都是移民,年轻时在欧洲发挥过某种作用,而现在,在争取成功的混乱斗争中,早把从欧洲带来的那些理论前提丢失殆尽。
托洛茨基来纽约不几天就参加了俄文日报《新世界》编辑部的工作。这份报纸成了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宣传中心。在社会党属下的各个民族联合会中都有一些懂得俄语的工作人员,俄罗斯联合会中也有许多人都会说英语。在这种情况下,《新世界》思想就逐步传播到美国工人群众中去。社会党里的达官显贵们为此大为恐慌。于是他们在各小组密谋策划反对欧洲移民的活动,说他们昨天才来到美国的土地上,还不了解美国人的心理,就企图把自己的荒诞的方法强加于美国工人。斗争相当激烈地开展起来。在俄罗斯联合会里,那些“久经考验”和“功勋卓著”的市侩们很快就靠边站;在德国联合会中,《人民日报》总编辑、老施留特尔,希尔奎特的战友,渐渐失去影响,让位给赞同托洛茨基伙伴们观点的年轻编辑劳勒;拉脱维亚人完全同托洛茨基伙伴们站在一起;芬兰联合会倾向于托洛茨基伙伴们。此外,托洛茨基伙伴们还越来越成功地打入势力很大的犹太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占有一幢14层大楼,出版一份发行量为20万份的《前进报》,不过这是一份充满多愁善感的小市民报纸。整个社会党,包括托洛茨基这些革命派在内,与美国工人的联系少,影响也不大,而党的英文报纸《呼声报》又以空泛的和平中立态度作为宗旨,于是托洛茨基伙伴们决定办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周刊。筹备工作全力以赴地开展起来,但是,正在这时——俄国革命爆发了。
新闻电讯突然神秘地中断了两三天,这使大家迷惑不解,接着,传来了彼得堡发生动乱的消息,虽然是些模糊不清和十分混乱的消息。纽约的各族工人都为之兴奋不已。人们期待着,但又不敢希望着什么。美国的报界不知所措。新闻记者、采访人员、报刊新闻栏编辑和常驻记者等等从四面八方涌向《新世界》编辑部探听消息。托洛茨基伙伴们的报纸一度成为纽约新闻界的中心。从社会党各报纸编辑部和组织打来的电话一直未中断过。
“电讯说,彼得堡组织了古契科夫——米留科夫内阁,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明天将有一个米留科夫——克伦斯基内阁。”
“这样!那么以后呢?”
“以后——以后由我们组阁。”
“啊!”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不下数十次。几乎所有同托洛茨基谈话的人都把托洛茨基的话当作开玩笑。在一次有“最值得尊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小型会议,托洛茨基宣读了一篇报告,论证在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这个报告产生的效果,就如同一次石头砸进了挤满自负和迟钝的青蛙的水塘里。
在纽约各区先后召开了空前规模和热烈的群众大会。冬宫上空飘扬着红旗的消息到处都引起一阵兴奋的欢呼。不单是俄国移民,连他们的大多不懂俄语的孩子也来参加大会,分享革命带来的欢乐。
托洛茨基在家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可是家里的生活仍然十分丰富多彩。妻子负责安排好这个小巢。孩子们也有了自己的新朋友。M医生的司机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医生太太常带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孩子们乘车去兜风,对他们很亲切。可是她是一个凡人,而司机却是个魔术师,是个超人。他一挥手,汽车就听从他的摆布。跟他坐在一起是最大的幸福。当他们来到糖果点心店时,孩子们会扯着母亲的衣角,抱怨地问:
“为什么司机不进来?”
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在维也纳大部分时间住在工人住宅区内,所以孩子们除了俄语和德语外,也能说一口地道的维也纳的方言。在苏黎世的学校里他们又不得不改学苏黎世方言,因为苏黎世方言在那里是低年级教学语言,而德语是作为外国语来学的。到了巴黎,孩子们又一下子转向法语。仅仅几个月他们就完全掌握了它。看到他们能流利地用法语会话,托洛茨基常常很羡慕。他们在西班牙和那艘西班牙轮船上,总共度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也足以使他们掌握了许多最必需的词汇和成语。最后,他们到了纽约,他们在纽约的小学里上了两个月的课,又大致上掌握了英语。二月革命后,他们在彼得格勒的学校上了学。但是学校里生活不正常,因而外国语从他们记忆中消失得比他们掌握得还快。可是他们说的俄语带有一股外国腔。托洛茨基常常惊奇地发现,他们拼凑的俄语句子就像直接从法语翻译过来一样,然而他们已不会用法语来组织这个句子了。他们在国外的漂泊经历如同写在一张羊皮纸上,就这样擦擦写写地铭刻在孩子们幼小的脑海中。
当托洛茨基从报社打电话回家告诉妻子彼得堡发生革命的消息时,托洛茨基的小儿子正患着白喉,躺在床上。他当时才9岁,但是他已经坚信,革命就是大赦,就是可以回到俄国,就是许多别的好事。他一下子爬了起来,在床上又是蹦又是跳,欢庆革命的到来。看来他似乎是复原了。他们急于想乘第一班船回去。为护照和签证奔走于各个领事馆之间。动身之前,医生准许刚刚康复的孩子出去散散步。妻子同意他出去玩半个钟头,接着就忙于整理行装——她干这样的事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可是孩子没有回来。当时托洛茨基在编辑部上班。托洛茨基妻子心急如焚地等候了3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个电话。先是一个陌生男人在说话,接着就是谢廖沙的声音:“我在这儿!”“这儿”就是指纽约另一端的一个警察局。原来孩子想利用这第一次散步的机会弄清楚一个久久苦恼着他的问题:纽约到底有没有第一街,(他们当时好像是住在第一六四街)?他迷了路,就向路人打听,人家把他带到了警察局。幸好他记得他们家的电话号码。妻子和大儿子在一个小时内赶到警察局,那儿的人像等待盼望已久的客人一样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谢廖沙满脸通红,正在同一个警察下跳棋。警察们一起看着他,弄得他非常难为情,为了掩饰这种窘态,他和他的新朋友一起拼命地咀嚼暗黑色的美国口香糖。他到现在还记得在纽约住所的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