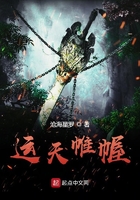“娘,我饿!”“等一会儿,你爸还没有回来。”母亲说。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总是习惯性地向路上张望一下。她在看父亲。路上没有人影,只有风在溜达。父亲这个时候在哪呢?在地里。
繁重的农活像一座小山,长年累月地压在父亲瘦削的肩上。一季季的庄稼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父亲的头发黑了变白,却不见白了变黑。
母亲说等一会儿,就得等一会儿。这个一会儿有长有短。长的时候,我的肚子会咕噜噜的唱大戏;短的时候,小板凳还没有摆齐,父亲的声音就来了:“我回来了。”
每次,父亲回来都会对母亲说:“下次不要等了。孩子饿。”可是,母亲总是不听。有一次,我当着父亲的面提意见:“爸,我都快饿死了,娘就是不开饭。”父亲瞅了一眼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摸着我的头,说:“好好好,不给她饭吃。谁听话,谁就有饭吃。”那天的午饭母亲做了什么,已经忘记,依稀记得母亲真的没有端碗,一个人躲在房里。那顿饭,我吃得最香了。饭间,父亲端着碗进去看母亲,再出来的时候,饭就没有了。上中学的大姐给父亲又盛了一碗。上小学的我莫名地看看父亲,父亲的饭量增加了?平日里,他只吃一碗饭的。
等饭中,母亲的手上总有针线在穿梭,我们破烂的衣角,总是齐整地码着母亲缝补的补丁。我们的家庭作业也是在等饭的空隙里完成。母亲会喊我们姐弟四人轮流去喊父亲。每一次的派遣,我们的心里都会陡生喜悦。父亲见我们,总是“好好好”的答应着。我一路小跑,回去报告母亲后,不由得觉得更饿了。
等我大了,我有时候会和父亲一起留在地里。中午的阳光舔着咸咸的汗水。我似乎可以闻到母亲的饭香。想回家吃饭,但父亲却没有回家的意思。为了证明自己也是男子汉,只好硬撑着。盛夏的中午,地里下了火,我和父亲没有灭火器,只有豆粒大的汗珠。这样的劳作,父亲习惯了,我却不习惯。就在自己快要崩溃的时候,父亲却轻松地抛来一句:“走,回家。”
到家后,我才觉得男人在家里的分量。洗脸水已经打好了,干干净净的,大红的花朵在盆底笑盈盈的,毛巾舒软地浸在水中。小板凳已经摆好了,筷子也上了饭桌。只待我和父亲洗了手,洗了脸,往桌子旁一坐,那些不知被母亲重复温热过多少次的饭菜,带着亲切的温度,从厨房里出来,等着我和父亲检阅。
一年,又一年,等饭中,母亲的步子逐渐蹒跚,父亲的腰板弯曲如桥。是子女的成长催生了父母额头的皱纹。如今的母亲,依旧在锅台边忙碌,她要等的人不光是父亲,还有我们这些成家后飞离屋檐的鸟雀。“妈,我们周六回家。”这样的一个电话,其实,就是预约了一次最难割舍的等候。
一顿饭,需要一家人在一起吃,才有味道。贫穷的日子里,每一顿饭都是家宴。母亲不会说出这么有味道的话。她只是觉得,一个家,一张桌子,一家人,一个人都不少的围坐在一起,那才是完整的一个家。少年时,我们等父亲,等的是一种感恩,是一种孝敬。现在,父母等子女,等的是一种团聚,是一种思念。那些饥寒的岁月,在等待的时空隧道里,竟是那么短暂,那么温馨。
等饭中,总有一些幸福的感动在缓缓地行走。今天,你等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