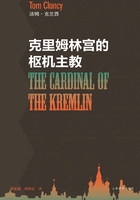数日后一夜,天空下着泠泠细雨,秋意更浓。菊花遍开,冷风送来疏冷的香气。
烟落静静坐在窗下,默默喝着茶,心神不宁。
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风离澈踏着雨中冷艳的香气走来,他穿着家常的青缎锦袍,暗沉的脸色,令烟落心中一阵紧张。
风离澈冷眸向后一瞥,身后宫女立即端上一碗黑漆漆的药汁,旋即退出,阖上殿门。“咔嗒”的关门声,惊了烟落一跳。她的心,一分一分冷下去。
面前的瓷碗,玲珑剔透。里面的药汁,漆黑不见底。刺鼻的气息,几欲令人作呕。
隐隐知道他的目的,她双手绞动着衣摆下角,呼吸沉重起来,声音一击接着一击,似是绝望。
风离澈在烟落对面坐下,挺拔的五官平静如水,他淡淡道:“这是堕胎药。我们大婚,你还是我的王后。”
四周静下来,静得只能听见他的呼吸声,似带着清冷漫长的意味。
烟落望着他,悲戚一笑。她起身推开身侧长窗,冷风汹涌贯入,直逼上她心间,她本想令自己清醒,哪知脑中益发空白。
瞧她低眉不语,风离澈沉声开口:“今日是风离御第四次攻城,他似乎急着拿下晋都。战争这种事,愈急愈难如愿,他这么做会元气大伤。”
顿一顿,有冷意漫上眼角,他道:“据密报,风离御劳心劳神,连月来常呕血。”
烟落的心猛地抽痛,尽量掩饰住面上担忧,她问:“他一向稳重,怎会如此急躁?”
风离澈突然擒住她的手,握在掌心揉着,目光深沉不定,慢慢道:“也许他急欲恢复政权,再挥兵南下夺回你。”
她脸色一滞。
他已冷嘲道:“欲速则不达。风离御如果五次、六次都攻不下晋都,必将士气大减。届时只会更加不利。”
“不过……”风离澈欲言又止,眸中似笑非笑。轻轻抚上她的发,他慢慢道:“我不想替他养孩子,若你生下再送还给他,只怕你不舍。长痛不如短痛,你喝下这药,我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而且我可以派精兵十万,助他攻下晋都,亦算是替我收拾那几个叛徒。怎样?你好好考虑。”
落胎……
烟落轻轻抚上小腹,手慢慢僵硬。心头仿佛被利刃凌乱地戳着,眼中酸涩,几乎要泛出泪来,她的孩子为何都这般命苦。他说得对,长痛不如短痛。他言出必行,若出兵相助,风离御复国指日可待。
她抬眸,望入他深不可测的眼底。她明白,他在等她答复。
窗外秋雨潇潇,落在翠竹上,一点一滴敲进她心中。
深吸一口气,烟落起身关上长窗,烛火幽暗,她的面容在烛光里模糊不清。坐定,她端起药碗,排斥着令人作呕的味道,她一口一口咽下。每一口,都似锥心刺骨的痛,凌迟着她。
随着她将每一滴药汁咽下,风离澈面上血色跟着一点点剥离,整个人被哀痛浸透。他不敢相信,为了风离御的江山,她轻易妥协了,没有恳求,没有哭闹,没有犹豫。其实那只是一碗安胎药,他是想试探下,她对风离御用情有多深。
他突然后悔,他不该试探,胸口仿佛被巨石堵住,渐渐绝望。她如此深情,义无反顾,岂是时间能磨灭?他想要她的心,却不想建立在她的苦痛上。
烟落面颊渐渐苍白,热泪从她空洞的眼窝中缓缓流出。她轻轻一笑,那样的笑凄绝楚楚,“澈,你知道吗?他也曾端了一碗红花给我。那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就这样没了。”
风离澈有些意外,挑眉问:“风离御?为何?”
她拭去眼角泪痕,静静道:“因为我要入宫冲喜,他没法抗旨。”
风离澈冷眸微眯,“你认为是我害你入宫,害了你孩子,这才陷害报复我?”
窗似没关紧,突地又被风吹开,帷幕被风吹得纠缠在一起,轻抚上来,惹得烟落一阵瑟缩。她叹息一声,黯然垂首道:“是啊,我一直误以为是你。”
风离澈冷哼一声,“我才不屑为之,风离御未免小看我。我同他争夺皇位,只不想令母后失望。”
烟落低首搅动着裙摆流苏,徐徐道:“你受封太子那夜,我在醉兰池边听到你与莫寻商议。”
他挑眉,“所以,你认定我与莫寻一路?”
她点点头,“入慎刑司一事令我不愿坐以待毙。我刻意接近你,其实我的手并没废,只想博你同情。以彼之道,还治彼身。我只想让你同样因我失去先皇信任,仅此而已。”
风离澈突然握住她的手,凝神道:“那夜我与莫寻商谈的是,如何借天象之说重翻母后冤案。你误会了。”
她哽咽了,似水秋眸中有着无尽歉意,凄声:“澈,对不起,是我太冲动。莫寻真名是完颜寻,他是夏北国四皇子,亦是日月盟盟主。我入宫冲喜一事,原是慕容傲隔岸观火、坐收渔利的计谋。”
风离澈一言不发,唇角勾起冷冽的弧度。他最恨别人欺骗,慕容傲,他不会放过他。
烟落决定将所有的事都告诉他,深吸一口气,缓缓道:“其实,山洞那夜,我们并没有……我在羊皮囊中放了迷幻剂‘醉春欢’,令你产生错觉。对不起,我欺骗了你。”
烛火明亮,一丝丝照在他脸上,他的神情沉静安然,只是眼角缓缓生出一缕凄然。他苦笑道:“我也怀疑过。只是……”他突然不再说。其实他不想知道真相,他宁可拥着美好的一夜回忆入眠,宁可犹自在梦中,也不愿醒来。
烟落将真相说出后,心头骤然松落。她伸手捂住小腹,痛感尚未到来。她凄凉一笑,轻轻道:“澈,该做的我都做了,该说的我都说了。希望你能遵守承诺,尽快出兵。”
风离澈转过脸去,“这是自然。昔日我离开晋都,慕容父子一路派人追杀,想阻止我纠集旧部。也该跟他们算总账了。”
烟落轻轻吁出一口气,莞尔一笑,“澈,能否请你离开,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再陪孩子一会儿,这也是身为母亲……唯一能做的。”她的话字字嚼着心酸,话音终湮没在泪水中。
他突然将她拥入怀中,心中的柔软与温情一瞬间喷薄而出,“烟落,那只是安胎药,我怎忍心伤害你……我……”他突然卡住,一句“我爱你”徘徊在喉间,终究没说出来。
他心中无望。她一心爱着风离御,如何能有他一席之地?也许他能得到她的感动,也许他能得到她的相守,可要她付出多大的代价?与心爱的人两地相隔,与儿女永生不得相见。她会是何等心痛?命运已令她承受这么多苦痛,还要承受几多?
如果从前是命运苛待,如今却是他一手造就。也许,是他执著了。也许,是他残忍了。也许,是他为难她了。他爱她,他不要她痛苦,不要她挣扎,不要她绝望。
他突然忆起,初次见她时,茫茫人海,琳琳琅琅灯影晃动,她身姿翩翩,穿梭在潮潮人流之中。月色如银,落在她身上,恍若小小精灵遗落人间,吸引了他的目光。
是他,错过了。
当时他收到密报,他知晓风离御在临仙画舫上定是布了天罗地网。他明明知道,她会是扑向灯火的飞蛾。他明明知道,却没有阻止。他一贯孤傲,令他总是冷眼旁观。不想那样的冷眼旁观,竟令他痛失挚爱。
他更紧地拥住她,反复呢喃着,“烟落,我好后悔……”
他的声音支离破碎,满是灰心与伤痛。原来人生就是这样,没有第二次机会,他错过了。他后悔,他好后悔。
烟落听到是安胎药,心口有错落的感觉,仿佛跃入大海,溅起雪白水花一片。风离澈待她那样好,从来只有自己欠他,他何尝忍心伤害过自己?眸中满含氤氲雾气,她哑声道:“澈,我……”
他以唇封缄她的话,她没有反抗。他逐渐加深这个吻,曾经无数个夜晚,他在梦中想起她。无论是被围堵追杀的日子,还是在南漠国寂寥的日子,还是坐在冷硬王座上的日子,他的眼前,总会时时浮现出她的脸庞。
突然,他不恨她的欺骗了,若没有她的蓄意接近,他如何知晓自己也有七情六欲,他如何能感受这样缠绵悱恻的爱情,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冷血的。
他不得不放手。她是别人的妻子,她是别人的娘亲,他留不住。留不住她的心,留住她的人,毫无意义,何必叫她伤心呢。
他只想要一个吻。一吻作别,心再无所求。从今以后,年复一年,无数漫长的日日夜夜,温暖的、寒冷的、阳光的、黑暗的、暴雨的、风雪的,总有能令他怀念的人,总有能令他怀念的事。
烟落默默承受着他的温情,感受着他的轻颤,心中只觉无限宁静。
一吻结束于他的轻喘离开,他拥住她,久久不愿放开。
突然,殿门陡然被人用力撞开,惊动屋中相拥的两人。
风离澈蹙眉转首,见是南宫烈十万火急赶来。
南宫烈急道:“澈儿,你暂时不能大婚。我要去一趟晋都,有件重要的事,我要亲自去确认。”
风离澈长眉扬起怒气,似极为不满,“父王,你要干涉我?”
烟落微愕,原来那晚吹笛之人就是南宫烈。也是,那名中年男子丰神俊朗,英挺贵气,绝非池中之物,原来就是南漠国太上王。
南宫烈轻吁一口气,澈儿桀骜不驯,像足年轻时的自己。他叹道:“澈儿,你等我去晋都问清楚。暂时别成婚,可好?”
风离澈嗤笑一声,抚弄着手上的墨玉扳指,“父王,你觉得我很容易打发?”
南宫烈拧一拧眉心,澈儿的性子令人头疼。良久,南宫烈似下定决心,道:“澈儿,我怀疑烟落是我的女儿。”
风离澈微微一愣,旋即笑起来,笑中带着冷嘲:“父王,你是子嗣单薄,想多认些子女?认了我又想认烟落,太可笑了!”
南宫烈熠熠目光看向烟落,问道:“你娘是歌伶,你两岁时带着你投奔楼封贤。这么多年来,没人怀疑过你的身世?”
“怎会?我娘怎会做这种事……”烟落急急分辩,话至尾音却绵软无力。其实的确有人怀疑过,婢女小厮常议论,哥哥也套过她的话。他们的怀疑,她看在眼中,只是刻意去忽略。
南宫烈见她发楞,追问道:“确实有人怀疑过?”
“够了!”风离澈盛怒道,“你胡诌什么,母后一心惦着你,你还和别的女人……你为何要辜负母后!”
“澈儿,我爱的人是司凝霜。我知你不喜她,一直没跟你提。我怀疑烟落是我与凝霜的女儿。”
烟落彻底怔住,冷意漫上她的背脊,仿若一条条小蛇蜿蜒游移,令她毛骨悚然。
司凝霜,有可能吗?她忆起零星片段,有人说二十多年前,司凝霜一曲画舞博得圣宠。有人说她神韵像极司凝霜。风离天晋与南宫烈都曾将她错认作司凝霜。真的像吗?为何这么多人都这么说?现下再想,确实是像的,三分容貌,五分性情。
如果是真的……
烟落脸庞忽然血色褪尽,眸中失了光彩。如果她是司凝霜的女儿,她岂不是亲手将娘亲封宫?如果她是司凝霜的女儿,她岂不是风离御杀母仇人之女?她心头涌上一团痛苦之火,直欲将她烧穿,风离御知晓了,会怎样看她?
风离澈不察烟落的异常,目光变冷,横眉厉声道:“怎么又是司凝霜?一个心如蛇蝎的女子,值得你们如此痴狂?风离天晋是,你亦是!”
“澈儿!”南宫烈神色一凛,薄怒道:“凝霜本性纯洁善良,是你母亲苦苦相逼,屡次置她死地。澈儿,你什么都不知道!”说罢,南宫烈自觉失言,颓然跌坐在椅中。有些事他本不想说出来,眼下再也瞒不住。
风离澈没有说话,长眉深锁。
南宫烈长叹一声,缥缈的神情仿佛沉浸在如烟如尘的回忆中。很久以前,他年少气盛,性子桀骜宛若一匹脱缰野马,亦是澈儿这般孤傲冷清。
南宫烈缓缓道来:“南宫世家是前朝世袭贵族,我是前朝大长公主的亲外孙,贵中之贵。前朝旧臣中颇有地位的,除了南宫世家,还有宰相司家,翰林秋家。南宫世家素来与司正德交往亲厚,我心中不屑。我不喜司正德,他只知讨好昏君,巩固权势,不明大义。那时我与刚正不阿的秋之衍交好。”
烟落静静听着,秋之衍便是风离御的外祖。
南宫烈折一折袍摆,继续道:“有一日,司正德带着凝霜来到府中。我明白司正德的意思,他想将女儿许配我,巩固自己的地位。”往事浮沉间,他的神情益发缥缈起来,声音无比轻柔,“她真的很美。第一次见她,我就被她迷住了。她的美不染烟尘,眉间一点惘然一点轻愁,好似烟落这样。”
语毕,南宫烈含笑望了烟落一眼。临水照花,看着烟落,仿佛面前正坐着亭亭少女时的凝霜,静静听他说着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