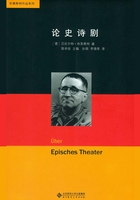又到一个世纪的尾声。当二十一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如今活着的儿代人大都还活着,怛现今活着的我们都在慢慢地送走这个世纪最后的几抹斜阳。历史终于提供了一个机会比我们思考这整整一百年,我们因而显得壮丽而悲凉。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和古老的社会,一百年本来就是短暂而匆忙的。但自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末,灾难和忧患似乎没完没了,中国知识分感到它的“漫长”。因而,关于它的思考显得异常沉重。
本胜纪开始的那一年即1901年,梁庖超发表《过渡时代论》(《清议报》八十二期众这篇文章以富有远见的预示,代表了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二十世纪的觉醒:告别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汜处于“过渡时代”。梁启超指出中国应当把握这个世纪的战略思想:中国有机会结束数千年停滞的封建社会向着开放的现代社会过渡。他认为当时世界“最可以有为之国”是俄国和中国。中国由于“十九世纪狂飙飞沙的袭击和驱实”,“机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已逐渐陷落,正是充满痛苦而又充满希望的弃旧图新的改革时代。他形象地比喻当日的中国“去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话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梁启超热切呼唤“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中国这只争取新世纪的崛起的航船,至今没有驶向大海。(也许驶过,但自然和人为的恶浪颠簸了一阵,总是又驶了冋来。)蔚蓝色对于我们,至今还是一个美丽的梦幻。中国和中转的知识者非没有识见,然而我们得到的却只是面对这发表将近一百年的《过渡时代论》而生发无尽怅惘。
应该承认梁启超的远见卓识。自文章发表之后,至少有辛亥革命宣告的清王朝的灭亡以及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样一些大事件发生。但时代无疑把失望留给了中国。中国这只垂老而犹思奋起的雄狮,几经颠扑依然未能猛迅呼啸于山林。而我们的同行者同样是古旧帝国的俄罗斯,以及具有同样文化渊源同时又有同样封建重负的日本,在本世纪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则似是一只在急浪中打旋的舟船,以将近一个世纪的挫折、受辱和折磨,终于又回到原先的出发地一二十世纪末叶,中国再次展示自己驶向海洋的欲望。
近百年中国国运不振,有深远的世界和中国自身环境的原因。但中国社会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痼疾不能不引起深重的反思。百年来中国知识界为捭救社会的衰颓进行了悲壮的抗争。从严复关于西方启蒙学说的译介到谭嗣同的流血讲演;从胡适艰难的文化反抗到鲁迅全力进行的国民性批判;七十年代以迄于今的大陆人道主义和人性解放的再鼓涌,以及台湾从柏杨的“酱缸文化”到龙应台愤怒的旋风一一它们构成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画卷。这画卷是中国数代知,只分子以血泪为墨彩所绘成。
当然,与它相映衬的还有另一幅历史长卷:它展现中国民众为抗拒奴役和入侵以及为自身的分裂和困扰而进行的正义的以及说不出其意义和价值的硝烟弥漫的画面。流血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令全世界惊愕的“文革”大骚动。
两幅百年画卷令人悚然心惊。百年来有识之士挣扎以罢捐生而徒劳,它未能挽救中国的艰危。
我们这些与二十世纪中国共过苦难的人,我们无疑将永远和这块土地亲近。我们的心情如一位诗人着名的诗句所写的那样:
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恸,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我也要努力飞腾上天空。
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与该社会对于知识者的尊重成正比。虐待和凌辱知识分子的现实,不仅为这个社会打上愚昧和野蛮的金印,而且恶劣的人文环境使这些原可为社会精英者的个性和人格萎缩以节变异。他们在无数次的思想劫难中面对伤害而无力自卫,于是筑起心狱。他们在这里经受着比环境和他人的暴虐更为残酷的自辱、自戕、以至自萎。
也许现今的一代人比任何一代人都要不幸,他们以伤痕累累的身心而要面对百倍、万倍于前辈的艰难困苦:十年的人为浩劫、数十年的社会异变、百年的战乱,文化的沦丧、文明的堕落、爆炸人口、失调的供求、沉重的社会病一一他们在无尽的期待和奋斗之中。一百年后重返中国的“过渡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