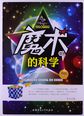鸟神或鸡神
盘古回城堡的路上,苹果还是忍不住跟我讲了盘古。是她主动要讲给的不是我要的。一提到盘古苹果兴奋极了,非要讲出来让我跟她分享一下不可。
我说:“要是不讲出来不行,就说吧,我为你保密。”
苹果说:“是啊,只有讲出来才高兴。”但苹果一再要我对任何人保密,不许讲出去。我明白,在游乐场,“任何人”大概就是指小顽了。
我一字不差全听了去,并答应对小顽守口如瓶。
苹果很崇拜盘古,说盘古是个可大可小的神,但大多数时候他非常非常小,躲在一枚鸡蛋一样的东西里面,一般是不肯出来见人的。其实想见也见不到的,他生活在远古时代,那时候还没有人,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的。
“它需要孵化,孵到火候就出来。”据我分析这个盘古可能是个鸟神或鸡神,所以最初当然是在一个蛋里,这不新鲜。
苹果马上强调,盘古绝对不是一个鸟雏,它就是一个神,它临时留在一个混混沌沌的“蛋”里面。那时候,天和地合在一起,没有山也没有海,更没有好看的云彩。盘古的留在那里的工作是让天和地分开,给生命一个缝隙,然后地上才好长出花草和蝴蝶、蘑菇和小兽什么的,天上才好长出太阳、月亮,长出云彩什么的……它做的事不算小。
“苹果,你讲的是一个神话啊!我在哪本图画书上读过的?”
“大概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说,没有盘古就没有一切,没有你和从前的我。”
“可书上不是这么写的,书上说的生命起源,大概跟盘古没关系。”
“你现在来到游乐场,你就得相信这个神话,这个神话让我们生活得挺有兴趣儿的,捅蜘蛛网这样的事我们早就玩够了。跟你说……”苹果把声音压得更低了,我都要听不见了,苹果说:“盘古藏在游乐场的一个地方,但是那地方没人知道……”
苹果意思是说那块地方“属于很久很久以前”,盘古在那个年代工作着呢。
苹果讲到盘古,就像讲到一位她特别喜欢的朋友,充满感情又有点崇拜,说起来便滔滔不绝。这样讲着,我的城堡出现了。远远地我就看见小顽蹲在城堡外面摆弄着什么,那么苹果的护送也该到此为止了。苹果对小顽还不能完全接受下来。临别苹果在我身后说:“我这里还有个秘密,最后一个秘密,索性也告诉你吧,就当多送一件礼物给你了。是这样,天和地分开那一刻,就是我和这里的伙伴们复活的机会,他帮我们重新回到地面,回到以前!所以我愿意相信这个神话是真的。我们都相信它。”
“还要多久吗?”我努力看着这位在空气中飘来飘去的气态朋友。她说到这里时,我似乎捕捉到了她的形象,很模糊,只一点点。
“快了。但是我们得防备灰蜘蛛破坏。”苹果叹了口气,没有了声息。
苹果把她最后一个秘密作为礼物送给了我,我却没想好拿什么秘密回送给她呢。我想了再想,我也没什么秘密。两年前我还在尿床,这是秘密,爸爸和妈妈知道,可是也不适合送给苹果,人家毕竟是女生嘛。
斧头是一件乐器
在小顽看来,自从来到游乐场,我的变化很大。这也是我对小顽的印象。我和小顽都跟从前不一样了,小顽变得神秘难测,他还有了一个“任务”。有了“任务”却不肯给我讲清楚;我本人呢,也够怪的,喜欢“自言自语”,精神失常的样子。这是小顽对我的印象。他哪里知道,我是在跟那个死去的女生的魂灵对话呢,他还不知道,我与那几个“飞人”都成了好朋友,叫苹果的“飞人”还把最后一个秘密告诉了我。小顽不知道我就像我不知道他,彼此彼此。
小顽单独出去,回来时心事重重。
我问他可是在寻找回家的出路,他摇了摇头。那便不用问了,他果然还是为他的“任务”心事重重呢。
我把城堡的门窗紧闭,拉过小顽告诉他,这个游乐场比看上去的复杂多了……我难以抑制心底的兴奋,但又不能把所有的见闻都讲出来。我显得坐卧不安。
小顽看着我说:“你肯交待了,那就都说出来吧?”
我说:“没、没了,住在这地方,有点不习惯。你没什么话说吗?”
小顽很失望,告诉我:“现在,没有。”
剩下的时间,小顽在石头上磨一把生了锈的斧头。我仔细看了,可以肯定,它不是小蛮手里那把。这把斧头是小顽刚才出去闲逛的最大收获,竟然是在蹦蹦床下面捡回来的。小顽说这斧头大有用途。既然去了那地方,自然要谈到那桶涂料,我赶紧打听它的下落。小顽说它还在,还没让盗贼偷走。我庆幸不已,我还不想舍弃它呢。
小顽几次去蹦蹦床一带,居然完好无损,我不得不钦佩小顽的运气,也对他的胆量五体投地。与他相比,在游乐场里我谨慎得像个听话的班级干部,这很不好。我知道很不好,又难以克服对灰蜘蛛的恐惧。
小顽继续打磨他的斧头,他磨得相当细心,把它当成了宝贝。慢慢的斧头的刃口闪出了银光。这下,我也喜欢上它了,凑到跟前去看。
嗤--嗤--斧头有节奏地在石头上擦出清脆的音乐。难以解释,这种单调的声响竟也让我着了迷。我微张着嘴巴,一动不动,双腿锁住那道银光,看它在石头上窜过来跳过去,一时间暂时忘记了自己的不妙处境,把这里当成了世外桃源,甚至看见了流水和草坪,还有挂在草叶上大睡的绿蚱蜢……
音乐突然停止了。如同惊醒了一个长长的美梦,我仍旧盯着那件乐器久久难以适应。
“你爱听这个?”小握着斧头给我看。
“好听。”我深吸了一口气,以便快点从刚才的痴迷中清醒过来。
“你喜欢你就继续磨它吧。我想歇一会儿!”小顽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把斧头递给我,还告诉我几个要领。
磨斧头也要有些讲究,真不知道是谁指点给小顽的,小顽从前绝对连斧头都没见过。在我印象里,小顽削铅笔的技术都不合格,铅笔总是被他削得疙疙瘩瘩,所以他也不太愿意上美术课。现在我倒十分愿意接受小顽的指导磨磨这把斧头,我渴望进入刚才的意境。我试探着开始磨制,大概是节奏掌握不好的缘故,我再也演奏不出刚才的音乐了。为此我很沮丧。
我磨着斧头,小顽躺在了床上,望着亭顶发呆。我猜小顽十有八九不是为我制造的音响发呆呢。
我问:“好听不?”
小顽半晌才反应过来,回答说:“太一般了……”
我便不再抱什么希望,只好随随便便磨下去。也不能指望劳动总能跟艺术扯在一起吧,劳动大体上来讲是毫无情调的事情。
最后,锈迹斑斑的斧头不见了,一把亮闪闪的斧头出现在城堡里,灰暗的城堡被它的银光映得生动了起来,这时,我才觉得自己没白干。
绿色城堡
磨完斧头,我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把我们的城堡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把它涂成绿色!
“敢去把它拿回来不?”我问小顽,我指的是那半桶涂料。既然他敢从那下面捡回来斧头,拿回涂料就没问题。
“涂成绿色……有什么用呢?”小顽躺在床上没动。
“磨斧头有什么用吗?”我很不高兴,用斧头敲打着石头。
“它跟我的任务有关系。你以为我是为了好玩吗?”小顽看了我一眼。
“可是谁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我真不明白,我们不过是在一个古怪的游乐场迷了路,怎么还捡回一个“任务”。于是我有点怀疑小顽是在故弄玄虚。他太无聊了,才虚构出一个“任务”来打发时间。
“唉!说它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还得帮帮我呢。”一提到这个小顽变得烦躁不安。
“你帮我拿回涂料我就答应帮你。”我没客气,要挟了小顽。说实在的,我真不愿意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小顽无奈地摇了摇头,从床上坐起来。
本来我一直担心蹦蹦床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的,但我担心的事情在小顽身上竟然没有发生。这让我怀疑,小顽真的已经与这个游乐场的恐怖力量达成了默契。接下来的情形又印证了我的判断:小顽很顺利地从那下面取回了我的涂料,什么都没发生。可是我握紧斧头的双手还是湿了,木把儿上留下两片湿迹,我做好了搏斗的准备呢。
涂料又回到我手里,我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好。一路上我想象着城堡的新貌。走近城堡时它完全被我想象成了绿色。这种颜色正好是游乐场里缺少的。我是相当的渴望早日完成这个计划。
小顽对这事没有多大兴趣儿。
我说:“它将比现在带劲儿十倍!”
小顽不冷不热地说:“反正我要你帮忙时你可别说没空儿。我帮过你了。”
我打了保票,保证帮忙,只是小顽一直不肯说要我帮什么忙,我也没心思再问,我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绿色城堡上来了。我甚至怀疑我是与粉刷匠这个行业有点缘分,怎么也说不明白那时候为什么那样喜欢,我都准备将来报考北京大学粉刷工专业。不知道那有没有那个专业呢,要是没有,我就只能考美术学院了。平时我经常看见美术学院的学生拿着笔蘸了各色颜料在画纸上涂来涂去的,这与我的爱好毕竟有点接近嘛。
我需要实践,实践的对象就是这个一点也不生动的城堡。
说干就干,我先做了一把刷子,刷子是用一些绳子头儿扎成的,像一枝质量粗糙的大毛笔。有了刷子就可以在我的城堡上面做画了。
小顽对我的工作视而不见。这时候他像个成年人,他不时地用很世故的目光瞟着我。这样的目光,我一点也找不到共鸣。那么小顽也就不能跟我分享刷墙的乐趣儿了。假如谁能同我分享这份乐趣儿,这份乐趣儿就能变成两份,甚至更多。
不过现在我只要一份。
我从墙根向上刷。忙了好长时间。我的城堡便有了一条绿色的裙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