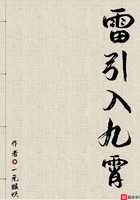洋烟泡来朵打朵,
不会吹烟正在学。
哪天哪时学会了,
自搬石头自打脚。
--民间歌谣
四间土坯平房出现在马灌啾河边,这是獾子洞一带唯一的房舍。按照宪兵队的要求,在地头高土岗显眼处,插面日本太阳旗,在无人区巡逻的日军见到这面旗会走开。
种四百垧地,徐家雇了几十人,由一个叫陈蝈蝈的打头带着,挤满了西屋。蝈蝈,一般比喻兴旺发达,也指难得罪,还指肥胖,多用在肚子上,例如:大肚蝈蝈。有俗语歌谣:大肚蝈蝈刘四海,包子馒头吃二百;瘦螂,胖蝈蝈。这个庄稼把式肚子不大,肚子大怎么哈腰干农活,相反瘦猴似的,叫蝈蝈是因为他能吃,属于干巴撑那种,绰号来源于此。
徐家盖的房子中间开门,西两间,东屋一间,西屋连二的南北大炕,长工短佣都睡在里面;东屋,徐梦地和谢时仿住,管家隔三差五被当家的徐德富叫回去,他也就三天两头住这里。除了四间大房子,东西山墙接着偏厦子,东厦屋也是两小间,十印大锅煮着几十人的饭菜,还有一盘磨豆腐的磨;西厦屋放着绳套和铧子、锄头等工具。离房子稍远的地方,是简易马棚子。
“二少爷,明天我回亮子里,你跟着下地。”谢时仿说,当家的捎信儿让他回去一趟,这几天是关键--下种。罂粟籽太小不可大把扔,要像种谷子似的用点葫芦,搁细心人点种,既不能点厚了,又不能点稀了,匀乎罂粟才长得好。
“中走你的吧。”徐梦地含拉忽吃地说。
“二少爷,老爷把种大烟的事交给咱俩,含糊不得呀。”谢时仿讲些道理,“老爷同日本人签了合同,秋后如数交上烟膏,不然,就惹蝲蝲蛄(麻烦)啦。”
“你们都怕二鼻子。”徐梦地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他管日本人叫二鼻子,管俄国人叫大鼻子,“交不上咋地?”
“小鬼子有多横少爷也看见了,咱可别惹刺子(招惹不好惹的人)。”谢时仿说,梦地少爷他多费不少口舌,换一个人就不是这样,徐家这一辈人中,二少爷肯定是颗瘪子,徐梦天当上警察局科长,徐梦人在四平街读书成绩优秀,日本话冰猴儿冰猴儿(棒棒)的,前程锃亮。徐梦地浑浑噩噩的,当家的对他失望,打发他来种地,也是让他吃点苦遭点罪,瞅瞅耕田耙垄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是什么样,也特地嘱咐管家,经管(管教)二少爷,这现实吗?自己是管家,奴不压主,当家的授权也不行,倒反不了天纲,点到为止,“大烟种子有数,小鬼子精算的每一条垄种多少棵,因此,一粒都不能糟践。”
“别磨豆腐啦。”徐梦地嫌管家话多。
谢时仿起身吹灭灯,走了出去。睡前他要各屋走走,然后才睡觉。这惯是在徐家大院几十年里养成的,那时徐老爷子还活着,他也有这个习惯,灶坑火灭没灭,仓房门锁没锁……睡前都查看一遍。
“管家,还没睡啊?”喂马的人招呼道。
“嗯。”谢时仿走进马棚子,见槽子下掉不少草料,心疼地哈腰收起来,对喂马的人说,“勤添少添,吃再添,省得它挑拣,浪费草料。”
“是,管家。”喂马的人急忙认错,“我懒,都怪我。”
“学会过日子唷。”谢时仿走出去随手捻低马灯灯芯,没立即回屋子,直径向田地走去。
春天的月亮水一样在土地上流动,风中还有些寒意,远处有人莫名其妙地喊山(:
哦--嚇!
附近没有山,又是夜晚,谁在喊山?谢时仿坐在犁杖刚刚扣(翻)过的土地上,土很湿润,蒸腾肥沃的气息。他想当家的急着要他回去,一定是二爷徐德中到家啦,安排吃住。
前几天,谢时仿去郝家小店跟抗联交通员接头。
“管家!”
“小张”,谢时仿问,“二爷啥时到家?”
“下月初八。”小张说出徐德中到家的确切时间,“特派员的住处安排好了吗?”
“腾出间屋……”
小张问药店里的况,对徐家以外的人做详细了解,说到徐梦人日语学的好,抗联交通员打奔儿(打问号)。
“刚毕业的学生,他没什么问题。”谢时仿说。
小张打个沉儿才说话:“注意他和日本人有没有来往。”
谢时仿没等到下月初八,带青份(长工)、伙计来獾子洞种罂粟。他直想着与小鬼子有关的两件事:三少爷日语学的那么好,将来可能为小鬼子做事,小鬼子的学校、工厂、公司、军队需要大量翻译人员;徐德中回来,也是和小鬼子种大烟有关吧?
徐家的故事真多呀!
谢时仿的感慨包含着徐家的过去和徐家的未来,老一辈人的故事还没完,新一辈人的故事已经开始,徐梦天、徐梦地、徐梦人,还有四凤……管家目睹故事的发生和发展,特殊身份决定他有时又是故事中的人物,跳出来跳进去……徐家是条河,他是条鱼,怎样飞起最终还得落到河里,道理是鱼离不开水。
谢时仿起早走的,徐梦地裹着被子大睡,他是给人叫醒的。
“二少爷,起来吃饭吧。”
“啥时候啦?”徐梦地问。
“歇二气啦。”
下地干农活儿,从早晨到中午共歇三气,头气、二气、三气,就是说歇气时间过去了半个上午,也该起炕,要是在家准挨爹骂。
“二少爷早饭……”
“晌午一堆(块)吃。”徐梦地脸没洗朝田地走去,他责任是查边儿,其实陈蝈蝈这个打头的够料儿,干活用不着二少爷督促,早早领人下地干活。
“起来了二少爷?”陈蝈蝈走过来,“您瞧瞧,这活儿干的行不?”
“行,太行啦。你陈打头的又不是二八月庄稼人,种地是把好手。”徐梦地眼盯着地垄沟说,他的心思不在种地上,寻找野菜。
“哦,二少爷别费劲啦,我给你挖啦。”
“大脑瓜?”
“当然,一帽兜儿呢!”陈蝈蝈说在地头放着,过会拿给少爷。
徐梦地爱吃这种叫小根蒜也叫大脑瓜的野菜,他在药店抓过药,知道它叫薤白,随口诵道:
瓜蒌薤白治胸痹,
益以白酒温肺气。
加夏加朴枳桂枝,
治法稍殊名亦异。
“二少爷,这是啥歌呀,好听。”陈蝈蝈阿谀道。
“汤头歌。”徐梦地说,见他傻愣地望着自己,摆弄土坷垃的陈打头哪里懂什么汤头歌呀,“唱大脑瓜。”
“嚄!小根菜啊!我会一段。”陈蝈蝈叨咕首民谣:小根菜大脑瓜,有人吃,没人挖。
徐梦地接上另一首歌谣:大脑瓜,小细脖,光吃饭,不干活。
大烟地上说笑一阵,陈蝈蝈问:“二少爷,你家种这么多大烟干啥?”
“你问我?”
“是啊!”
“我问谁去?”
“难道二少爷不知道?”
“我知道个六(乌有)呀!终日无所事事的徐梦地可不是谦虚,他说,“二鼻子叫爹种,爹就派我来种。”
“日本人叫种的?”
“是啊!”
“他们种大烟干什么?”陈蝈蝈问。
“鬼知道!”徐梦地在药店抓过药,说,“治病吧。”
“我看是抽。”
“二鼻子抽大烟?”
“我看是。”陈蝈蝈说。
谢时仿被叫回来,与昨夜徐德富和徐德中密谈有关。
“哥”,徐德中说,“这次回来不是我自己。”
徐德富一下想到二弟年纪不小,早该谈婚论嫁,在外十几年说不定已经成了家。
“你说了人儿(娶妻)?”
“基本上。”徐德中含混道。
“基本上?”
徐德中将组织的决定,或者说本次回三江的任务,经过思考后怎样对长兄说。抗联决定,派徐德中回老家,以做坐堂先生为掩护,任务先不说,和他同来三人,美丽的尹红以徐德中的妻子名誉,和他住在徐家药店里,还有一个外围的交通员小张,他以药材商贩的身份往返三江和抗联密营之间。他能向长兄说的是,要在家住一个时期,为抗联做事,真正的任务不能说,这是纪律。
“德中,你媳妇现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家来。”
“我们还没正式结婚。”
“没办事,打算什么时候办?”徐德富关心二弟的婚事,老大不小了,二嫂和佟大板儿生的娟儿都几岁了,当年德中如果和二嫂圆了房,孩子比梦人岁数大,做哥哥的能不着急嘛。
“以后再说。”
徐德富见过世面,二弟说的没正式结婚,不等于没结婚,以后也只是补办婚礼,那不过是走个形式,走走而已。他问起尹红的情况,“哪儿的人啊!”
“海城。”
“张(作霖)大帅的老家。”
“她祖籍海城,从小在奉天长大。”徐德中编造女游击队长身世的又一个版本:他的父亲在奉天开家棉花铺,生意还不错,后来一个日本商人也开了家棉花铺,竞争不过尹家,通过宪兵硬给戳惑(鼓捣)黄了,还杀死了她的父母。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在奉天开诊所,招聘护士……”
“这么说她会扎针?”
乡下地主以为护士就是会扎针、抓洋(西)药,怎么认为也都无所谓,反正都是编造的,尹红会注射倒是真的,准备以徐德中妻子和护士的身份到三江协助特派员工作。
“我打算接她过来,不知方不方便?”
“方便,咋不方便。”徐德富连忙说,他心急二弟早结婚成家,把媳妇接过来,“趁早……”
“过两天,我去奉天接她。”
多了一口人,徐德富觉得再好好布置一下德中的房间,至少达到准洞房标准,有必要叫谢时仿回来。
“管家忙着种地,别牵扯他。”徐德中说,“尹红又不是别人,我能住她就能住,没挑。”
“这不是挑不挑的事,你圆了扁了都行,人家毕竟是新人。”徐德富说,他加重“新”字,东北话中,新字用在男女的事情,结婚当天称新郎官新姑爷、双方家属称新亲。
徐德中没去纠正长兄,尹红不是他说的新人,此次假扮夫妻。在游击队里,政委和传奇女游击队长,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他们的友谊超出了普通的友谊,鲜血凝结的情谊,有了爱情成分,只是中间隔层窗户纸谁也没捅破它,这次组织给捅破。
“你多年没回家,突然回去,恐怕军警宪特疑心,”周队长说,“为掩人耳目,你带着夫人回去。”
“夫人?”徐德中惊诧道。
“夫妇回家,反倒比你一个人回去目标小。”周队长说,“这样有利工作,夫人还能帮助你。
“可是……”
“没什么可是,人组织为你选好啦。”
“谁?”
周队长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了一个姓。
“不,这不合适!”徐德中反对道。
“德中同志,这次说公私兼顾也成,你们住在一起,也有利于加深感情,发展了,正好成一对。”周队长说。
抗联密营几位领导都有家眷,在部队上的有,在老家的也有。徐德中是年岁较大,却没有家室。尹红年轻,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直接到抗联来,打了多年的游击,还不到三十岁。
“她也不会同意。”徐德中说。
“错啦,她欣然同意。”
“唔……”徐德中闪神儿。
“尹红在你身边,你安全多了。”周队长不讲,事实也明摆着,尹红机智勇敢,对敌斗争经验丰富,“你侧重劝降天狗绺子……日本鬼子种罂粟,这是一个新动向,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敌人目的,尹红重点注意种罂粟。小张做交通员,你们的情报交他传递。”
徐德中不能对徐德富说这些,长兄积极张罗收拾房间,当他们新房布置,他想想也好,如此也是个效果,给全大院里的人一个印象:徐德中跟媳妇住在一起。
“被褥什么的,我给你备。”徐德富全力以赴张罗。
次日,谢时仿赶了回来。
“时仿,德中这次带媳妇回来,原来的屋子太狭窄也不亮堂,重新打扫一间。”徐德富吩咐道。
“和药店连山的东厢房那两间怎么样?”管家问。
“嗯,离街太近,在院子里头选两间。”徐德富考虑到二弟是抗联的人,将来要做事,背静的地方住着好,“挨我屋的三间收拾出来给他们。”
谢时仿照当家的安排,一一记下来。
“地种得咋样啦?”徐德富问。
“不闹天头(天气变坏)的话,明天就能种完。”谢时仿说。
“宪兵队昨个儿催问种烟进度,我说明天种完,还真蒙正道(准确)。”徐德富说,“林田数马要带日本技术员去实地验收,整如作(妥帖)点儿,日本人好挑眼皮(挑剔毛病)。”
“没问题!”谢时仿问,“四小姐搬回来了?”
“唉,出了档事,四凤去新京几天,回来房子没啦,叫陶奎元的大太太和二太太二上给卖啦。”
“卖啦?那她们住哪儿?”管家问。
“拿房钱溜了。”徐德富说,“你说这出的什么损事儿。”
“什么都没给小姐留?”
“还留呢,连孩子都给抱跑啦。”
“我说嘛,四凤小姐人都瘦了。”谢时仿深深同情她,徐家不幸的人中她算一个,十几岁被卖到窑子里,大她二十多岁的陶奎元三千鬼化狐(鬼把戏)娶她做三姨太,十六岁当妈妈,忽然间陶奎元给人杀死,年纪轻轻守寡,又叫两位太太给算计了。
“真是越瘸越用棍点啊!”徐德富怆然道。
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天灾?人祸?徐德富心里想到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