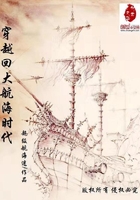在当地居住,若经常与这儿老人们打交道,每年时逢季节交替之际,偶或会听到像“二八月乱穿衣”一类的老话。对于当地人,经常是张口就来一些老话,任何人一旦听得多了,若还认真留心琢磨起来,都一准会从中悟出许多自然规律和生活道理。
大概过了千禧年以后,距离不惑之年,其实还有几个年头的任凯,尽管嘴上没有与任何人谈论过年龄问题,但在他自己心头上,却时常掠过一阵又一阵“即将老去”或“行将就木”的无形压力和时间急迫感。
有一天开车出门,从车载收音机里,听到一段讲解“立秋”的故事。任凯一下子便联想到母亲常说的“二八月乱穿衣”那句话,禁不住心头豁然一亮,暗自琢磨起来:“这儿的二月、八月,不就是冬春和秋冬交替的时节吗。人们之所以穿着服装多样,是因为忽冷忽然的缘故啊!”任凯把汽车停在大哥公司车库里,在把车钥匙还给办公室耿主任时,耿主任热情地对他说:“你开着吧。要变天了。放那里也没人开。”任凯对耿主任笑了笑,摇了摇头。他把钥匙递给耿主任,也没有接耿主任的话茬,转身走到室外,又登上了自己的自行车。
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一阵狂风吹过,树上地面的枯枝败叶,迎面扑来。这一次却让任凯,又突然意识到: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骑自行车与坐在汽车里,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
在路口等待红绿的时候,任凯依然屁股不离自行车座,他一只脚放在车蹬子上面,一只脚踩着路旁的马路牙子。当他抬头瞭望路对边红绿灯时,眼睛完全被路对面新竖立起来的一大幅招贴画吸引过去了。那招贴画是某海边城市选美的宣传广告,一排十多个美女,身着不同款式的泳装,尤其那立体颀长的秀腿,让近来因牵挂“人过四十午过晌”而兴趣低迷的任凯,突然之间有一种青春活力般的冲动。于是,任凯直觉自己总算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并暗自给为自己打气:“是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了。要不一生这样活的,也太窝囊了吧!”
行将就木的秋季暮色中,温度没有刺骨的寒气。
任凯一家三口居住在七层楼房的防盗门,本从外面开锁的钥匙,弄出来“哗啦……哗啦……咔嚓”的动静。随着房门推开,任凯儿子背着画夹走进房间。他停住脚步,先长吐一口粗气,然后大声喊道:“爸爸,我们回来了。”
“噢!在楼上。我还没做饭来,让你妈做吧。菜都准备好了。”上方阁楼里,传来任凯回应的声音。
紧随儿子身后,任凯妻子面无表情地带上防盗门。她站在房门前,不急不躁地依次换下外套和鞋子,等挂好衣服后,再俯身把门旁的三口人鞋子,依次摆好。然后,才开始提速,她径直奔去卧室,先到卧室洗手间清洁过双手后,才换上一套便装,再到厨房里,戴上围裙和套袖,伸手打开了抽油烟机。
任凯妻子瞧了一眼,放在灶台上,已经切好并盛在盘子里的一碟芹菜和一碟胡萝卜丝。她转过身子,冲着客厅里喊道:“叫你爸爸下来吃饭。”
在个人房间里,任凯儿子正双手捧着一个烟盒大小的游戏机,全神贯注地忙活不跌。听到妈妈的声音,他连忙把游戏机塞进枕头底下,赶紧到墙边,迅速拿过来画夹。他一边把画夹放在床铺上打开,一边把里面一张刚刚临摹了一半的圆锥体素描,双手对折起来,小心翼翼捏在一只手中,随后快步闪出房门,径直奔上阁楼。在他身后厨房里,传出来“滋滋…喇喇……叮叮当当”一阵阵炒菜中锅碗瓢盆碰撞的旋律。
“蹬……蹬……蹬……”任凯儿子一溜小跑地上了阁楼。在阁楼上,任凯左手拿着长长的画笔,右手托着下巴,头和肩旁左右调试着,正在点缀着画架上,一幅像是落日晚霞的风景油画。听到儿子奔上楼的声音,他小心细致地把画笔放在身旁长条桌上的调色板一侧,凝视着前方的画面,整个人的肢体语言,都透出一份心得意满的姿态。
儿子推门进了阁楼,走到一张条桌前,他一边把手中的素描展开,一边乐滋滋地喊道:“爸,这是我今天画的,你看怎样啊?”
任凯转过身来,低头用一只手把画纸抚平了一下,只是端详了一会儿,便说道:“线条拉得不错了!你坐在什么位置啊?你画这个椎体的时候,应该完全按照你所处位置的远近视角来画,要去掉你脑子里原有椎体模样。这样,你的‘调子’才能找准,画出来才感觉舒服。我觉得你这个比例上,也有点问题。下次你好好看看,按老师讲的细节,一步一步来,别想当然!”
儿子站在一旁,他仰视着父亲,已经从父亲脸色上,觉察出来这一次评价,其实更多的是表扬成分。于是,他在父亲面前,尽可能掩饰内心欢喜和骄傲,也低头看着自己的画,并认真地说道:“张老师今天没来,小李老师让我们自己随便画的。爸,李老师今天问我妈,你是干什么的?”任凯一听儿子这句,立即不耐烦地问道:“她打听这个干嘛?”
儿子笑嘻嘻地回答:“我也不知道,你问我妈吧。李老师和我妈说,我素描进步最快了!”
任凯听儿子说出后面的话,他干脆用双手拿起桌上的素描,认真端详起来。
“还吃饭吧,你俩?快下来!”从楼下,传上来任凯妻子不耐烦的呼唤声音。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的住宅小区内,任凯家卧室的大灯还亮着。任凯把两个大枕头靠在背后,依在床头上,双手捧着一大本厚厚的“羊皮卷”,慢条斯理地一页一页地翻着书。看他那架势,不像是在阅读,更像催促媳妇赶紧熄灯。
穿着丝绸睡衣的妻子步履轻巧地走进屋里。她打开壁橱,从里面拿出一个天蓝色的床单。
任凯见状,挺身起来,依然捧着大书本,不急不忙地移身到床边的沙发里。
妻子十分利落地摆放枕头,展开床单,一边仔细铺好,一边又从厨子里拿出来一床柔软的双人薄被子,随展开着岁说道:“你儿子真的随你了!不知你儿子说你什么了?今天,李老师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是老师啊?还是画家?你儿子画素描,特别认真。李老师说他进步特别快。还说他,人虽然不大点,讲起素描来,还一套一套的。是不是你教他说的啊?”
听到妻子说出来这样一番话。任凯这时候,才抬起像是一直在看书的眼睛。他面向妻子,没好气地回应道:“你该说,是你教他说的啊!在你眼里,我还能教他学好吗?”
听着任凯说出来的话,明显带着一种不满情绪。她瞥了丈夫一眼,蹑手蹑脚走到卧室门前,用手又推了一下房门。妻子顺手关上大灯,她一边把手伸到上衣中褪出文胸,一边把胸罩挂在床边衣架上,这才冲着任凯和缓地说:“近来,病区里纠纷不断。现在的病号,真是越来越难缠了!”
任凯感觉的出来,今晚妻子又恢复了往时的温柔。他便放下手中书,眼见妻子来到身旁,伸手拦腰抱进怀里,亲着他的胸前,笑嘻嘻地念叨:“还有比我难缠的吗……”
“瞧你这德行,不能给你个好脸!”妻子嘴上这样说着,伸手挽着丈夫,俩人热吻,拥抱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