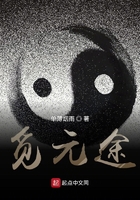当叶子如游魂一般回到将军府时,天色微暗,房屋、地面、树梢都披着一层薄而暖的红光,伴着一缕缕的袅袅炊烟,显得是那么的悠然惬意。
只是,这一切在叶子的眼中都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她自嘲地仰望天空,忽然觉得自己就如那些随风飘浮的云团,无根,亦无形。
东苑,大夫人端坐正厅,一边审视眼前跪地之人,一边冷笑。
“说吧,你是对这份工作不满,还是对我不满?”
叶子摇头,抿着唇一言不发。
“没有吗?!”大夫人拍案而起,“那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还空着手?!”
叶子依然沉默,只安静地跪在那儿低着头,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大夫人给气得笑了,她这是在对牛弹琴吗?
“罢了,不管你是故意在试探我的底线,还是别的什么心思,将军府都不是可以由着你撒泼的地方!”
大夫人甩袖坐下,如寒冰利刃的视线盯着叶子许久,慢慢扯起一边的嘴角:“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是滚,是罚?”
叶子抬头,淡淡一笑:“罚。”
不知是否错觉,大夫人总觉得她有种得偿所愿的迫不及待。
不过,大夫人一向不是心软的,她立刻招来家丁将叶子五花大绑后执行家法。
掺着钢丝倒刺的藤鞭,每打一下都能掀掉一层皮肉,看来大夫人是恨她恨得狠了,早就盼着这一天吧。
叶子忍着身上撕心裂肺的剧痛,暗中对自己故意往刀口上撞的贱样,自嘲不已。
“啪啪啪!”的鞭声,每一次落下都隐约能听到一个女子的轻吟,每一次扬起都溅出艳丽的红色,渐渐女子的头垂了下去,她周围的地上也开出大片的红梅,艳的让人心悸。
只不过,这一切并不能令大夫人完全消气。她还从没像今日这么丢脸,信心满满地说请客人吃最好的螃蟹,结果菜一上来哪有半个螃蟹的影子?!如果当时地上要是有道缝,她准一头钻进去。
比起让人说将军府穷得吃不起螃蟹,她觉得让人说她连个下人都摆弄不了的事,更让她丢人!
大夫人在叶子被凉水泼醒后,冷笑:“是说?是再罚?”
叶子虽然身上痛得都不像是自己的,但思维还很清楚。她明白大夫人是在跟她要解释,只不过……
叶子轻轻一笑,一字一顿地道:“再罚。”
东苑的鞭声到底什么时候停止的,谁也没有注意,因为这种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所以他们已经从习惯到麻木,即使外面整晚都哀嚎惨叫,他们也能酣然入梦。
何况,今晚受刑的还是个锯嘴葫芦。
安静的房间中,昏黄的油灯发出有些微弱的淡淡烛光,像是快要燃尽一般。可惜,它的主人却无暇理会,因为此刻她正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人事不省。
苍白的容颜,双眉因疼痛而紧蹙,被冷汗打湿的碎发凌乱地贴在她的脸颊两侧,她的呼吸清浅而短促,发白的双唇微微张开,这还仅仅只是表象。
在锦被之下,那娇小单薄的身子此刻如破布一般,千疮百孔,体无完肤。让人实难想像这样虚弱的身体,到底蕴藏着怎样倔强的心。
清澜守在床前,眼中痛色明显。你一定要如此伤害自己,折磨别人吗?
幽幽一叹:“何苦呢。”
谁知,下一秒躺在床上的人竟突然睁开眼睛,似要将他贯穿一般地直直看向他。
那清冷目光中毫不掩饰的愤怒和不甘,失望和怨恨,让清澜心中一窒,背后渐湿,耳中不断地重复着她悲凉的控诉——
“你们,骗我。”
翌日清晨,芊卉居中就已多了几个人,他们却似感觉不到冬日的寒冷,于凛冽寒风中伫立屋外,个个愁容不展,心事重重的样子。
“她知道了。”
“这怎么可能?!”
贺斩风不可置信地瞪着清澜,他们费这么大力气将秘密守到现在,怎么就这么功亏一篑了呢。
清澜没有回答他,却听慕容昭在一旁叹息:“原本也没打算能永远瞒住她,但也想不到会这么快。”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清澜长长吐出一口气,环视一圈,问,“由谁说?”
慕容雪犹豫着刚想开口,就被一旁的慕容昭拦下,沉吟道:“还是我来吧。”
慕容雪先是一怔,但很快就明白了哥哥的意思。他是怕叶子知道真相后,要不就直接对她发火,要不就干脆忍着,而这两种情况都是他不愿见到的,所以不如由他去说,让她能毫无顾忌地发泄。
贺斩风和清澜自是没有异议,毕竟最清楚这事点滴的莫过于慕容昭了。
屋中,晨光透过薄薄的窗纱在地上洒下斑斑点点的影子,虽不十分明亮却也足以让人看清。
这是慕容昭第一次踏足叶子的房间,略微一扫便已悉数尽在眼底,桌椅衣柜虽然简单却非常规矩整齐,纤尘不染,与她在外所表现的性情完全不同。
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你呢?
慕容昭向靠在床边一脸病容的女子走近。
女子的面色因身上的病痛虚弱而苍白,此刻她正靠坐在床头,似未察觉屋中有人进来,望着窗外微微出神,视线淡漠而木然。
但慕容昭知道,她是故意无视他,叹了口气也不用她问,便自顾讲起了事情的始末……
在最后一次两军对弈中,顾将军与敌军元帅经过激烈交锋,终是大获全胜,但就在他们准备欢呼庆贺之时一支冷箭凭空出现,并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射向还未来得及转身的顾将军背后要害!
然,最终中箭落马的却是顾荣。
原来,在千钧一发之际他飞扑上前,竟奇迹般地赶在箭矢前挡在顾将军的身后。只是,虽然他避开了要害,却仍旧重伤昏迷。
只因,那箭不但带有倒刺,更是煨了剧毒!
皇上听闻此事特派一队人马将顾荣从边境秘密护送进宫,并抽调太医院医术最高的几位太医为顾荣医治。
所以,这些日子顾荣并不是滞留边境处理事务,而是待在皇宫秘密养伤。
慕容昭又一叹息,原本此事除顾将军之外只有父皇和他知道,并且他们已经成功瞒过朝堂上下,只等顾荣痊愈后便可重新现身,却不料叶子的反应大出他的预料,着实让他措手不及。
叶子的异样,令贺斩风抓耳挠腮,于是几次三番硬闯太子殿,要他想法子把顾荣从边境弄回来。最后,他被磨的没法,又怕贺斩风的脑抽行为惹怒父皇,便将真实情况简单相告。
谁知,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笨蛋竟然被清澜堵在家里,不但被套了话,还把他给供了出来。
后来,清澜不忍见叶子整日胡思乱想,郁郁寡欢,便设了一计引他们出来谈判。
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一致同意用顾荣的亲笔信来暂时安抚叶子,只是这看似简单的事,对他和顾荣来说都绝不轻松。
虽然,顾荣被他秘密安排在宵云殿中一处偏僻的废旧院落,但为免别人起疑他一般并不过去,只在顾荣病情有变时才会过去看望一会儿,其实他也帮不上什么忙,平时他就算过去也没什么意义,因为顾荣多数时候都在昏睡。
所以,要给叶子写信一事,他也只能让留在那儿的宫女在顾荣醒转后立刻通知门外守卫,但饶是如此他也白折腾了五六趟才将事情说与顾荣听。
于是,顾荣几天下来断断续续写了数十封信,最后却只能勉强挑出三封没有任何破绽的信交给他。
“他伤得很重?”
床上的女子终于肯开口了,只是仍然不愿将视线投向他这边,慕容昭眸色微暗,点了点头:“是。”
慕容昭不由回忆起第一次把信交给叶子时,她即开心又气愤纠结的不得了的可爱模样,好像有一种让人将什么烦恼都忘掉的魔力。
所以,他回宫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件事告诉顾荣,因为他知道这对于此时的顾荣不谛于最好的良药。
他过来时,顾荣仍旧躺在床上,就像是在等待他一样,居然难得的没有昏睡,反而精神还很好,率先跟过来凑热闹的贺斩风打招呼。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该不是又为了躲避贺伯伯的管教,跑这儿来找庇护的吧?”
“小看我!再说,我是被谁害成这样的,你还敢提?!”
顾荣一边咳嗽一边认错,贺斩风见此只得偃旗息鼓,直抱怨他现在跟女人一样娇贵了,动不动就喘。
慕容昭上前,一脚踢开这只不会说话的耗子,指了指他滚圆的臀部道:“你如果还想保住后面,最好给我把嘴也管住了!不然……哼哼,想试试在床上躺个一年半载的滋味吗,我非常乐意帮你实现。”
贺斩风一惊,双手紧紧捂在嘴巴上,摇得头都要折了。
慕容昭这才满意点头,又将叶子看信后的有趣反应说给顾荣听。
顾荣笑不可支地摇头:“幸好当时我不在,要不然难保她不会把信直接摔我脸上。”顿了一下,看向面前的两位挚友,语气郑重而诚恳,“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
慕容昭佯装不满:“瞧你说的!这么见外,要罚啊。”
“是滴,是滴。”贺斩风不忘在一旁附和。
顾荣笑笑,想叫人拿来纸笔,再多写几封。慕容昭见状,赶紧阻止:“你行了,好好养伤吧,别再乱来害我被太医骂了。”
这阵子太医天天跟他抱怨病人不配合,磨叨得他头都大了。可他能管得了谁啊,个个都犟得跟牛一样,头上插支两角就可以认祖归宗了!
顾荣有些犹豫:“可她看到第二封信,更会闹吧。”
“闹就闹吧,哄哄不就得了。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埋,遇神杀神,遇魔杀魔,谁能难倒我们京城三少啊。”贺斩风得意地拍着胸脯道。
“就是。”慕容昭指着地上还未来得及让人清理的纸堆,补充,“再说你看看这几天你勉强写的那一堆纸,没一千也有几百了吧?可是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不说,伤势还恶化了!你说,你这到底是在帮忙,还是添乱!”
一直没有出声的慕容雪也趁机劝道:“荣哥哥,你就在这里安心养伤。如此,既是对我们的最大安慰,也能早点见到她不是。”
顾荣终于明白以一敌三不是明智之举,于是非常上道地举手投降:“好好好,是我错了。唉,我这到底算是病人呢,还是犯人呢。”
“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府?”叶子终于转过视线,却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这让慕容昭猜不透她对于刚才的一番解释是否接受,他迟疑了一下,坦言:“这个要请示父皇。”
叶子微微一愣,复又收回视线,声音淡漠的似不愿再谈:“好,我明白了。”
慕容昭看她如此,莫名心里难受,诚心道歉:“对不起,我们骗了你。”
叶子突然笑出声,语带嘲讽:“太子严重了。我不过一个丫鬟,哪里能管主子,又哪里敢怪你们。”
慕容昭脸色一沉,他知道叶子此刻正在气头上,虽然不怪她,但对于昨天的事却难免略有责备:“但无论如何,你也不该用自己的身子来和我们置气。你这样……无疑是在拿刀戳我们的心!”
叶子别过脸不语,泛红的眼眶有一层凝结的水雾。
慕容昭望着她的背影良久,深深一叹:“你好好休息吧。”便要转身离开。
“别告诉他。”这是房门闭合的刹那,屋里人对他的嘱托。
别告诉什么?
慕容昭知道,这个“他”是指顾荣,而不让告诉的事自然是指她昨晚受罚的事。
慕容昭莫名胸中升起一股醋意。顾荣,你真是让人即同情又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