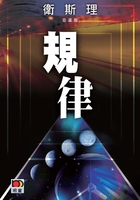这位老人的惊奇也不比他的更小。然而马尔科却不给他发问的时间,就向他快速地讲述了自己的情况。“现在我没钱了,就是这样;我必须干活儿,请您为我找份差事,好能挣几个里拉;我什么活儿都可以干;运东西,扫大街,我能购物,在农村劳动也行;靠黑面包过日子我也心满意足;但愿早点儿出发,能够最终找到我的母亲,求求您了,为我找份工作,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为我找份活儿干,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啊呀,啊呀,”老人眼望周围,手抓下巴颏,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呀!干活么……说这些还早点。我们看一下。在这么多同乡之中,难道就没有办法找到三十个里拉吗?”
马尔科望着他,被一线希望所安慰。
“你跟我来。”农民对他说。
“去哪儿?”男孩子问道,同时又拎起衣包。
“你跟我来。”
老人移动脚步。马尔科跟随着他,他们一起走了一大段路程,没有讲话。老人停在了一个以一颗星星为招牌、只写着“意大利之星”的客栈(zhDn)门前,他伸着脸看了看里面,然后转向马尔科,欢快地对他说:“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他们走进一间大屋子,那里摆着几张桌子,旁边坐着许多男人,他们正在边喝酒边大声地讲着话。伦巴第老人走近第一张桌子,从他跟桌旁的六个顾客打招呼的方式上可以明白,他是不久之前才与他们为伴的。那些人脸色通红,酒杯碰得直响,一边叫嚷,一边说笑。
“同胞们,”这位伦巴第老人仍然站着,介绍着马尔科,开门见山地说,“这里有个可怜的孩子,是我们的同乡,他独自一人从热那亚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找他的母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对他说:‘这里没有,她在科尔多瓦。’他乘船来到罗萨里奥,走了三天四夜,带着两三行的介绍信;他交出信件,他们却让他丢人现眼。他现在身无分文。在这里孤身一人,就像一个绝望者。他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孩子。我们看一下。难道他找不到足够买票去科尔多瓦找他母亲的钱吗?难道我们能把他扔在这里像条狗一样吗?”
“啊呀,绝不可能的!”“可千万别这样说!”他们把拳头打在桌子上,一起高声地喊叫着:“我们的一个老乡!”“过来,小家伙。”“有我们这些移民呢!”“你看,多漂亮的小淘气!”“同胞们,拿出钱来吧。”“好样儿的!一个人来的!你真有胆量!”“老乡,喝一口。”“我们会像你母亲一样地养着你,你不必多虑。”其中一人还捏(niE)了一下他的脸蛋,另一个人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第三个人卸他拎着的衣包;其他的移民也都从邻座桌旁站起身,向他走近;小男孩的事迹传遍了小旅店;从隔壁房间还跑过来三名阿根廷店客,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伦巴第老人拿着的帽子里就收集到四十二个里拉。
“你看到了吧,”于是他转身对马尔科说,“在美洲钱来得有多快!”
“喝吧!”另一个人向他递过一杯葡萄酒说,“为你母亲的健康干杯!”
所有的人都举起了酒杯。马尔科重复道:“为我母亲的……”然而快乐的啜泣使他如鲠(gGng)在喉,他又把酒杯放在了桌子上,扑到了老人的脖子上。
第二天早晨,在天刚亮的时候,他就已经出发去科尔多瓦了,他勇气十足,面带微笑,满怀着幸福的预感。然而,面对大自然的某些阴险面貌,这种欢乐没有持续很久。天气阴沉,天空是灰蒙蒙的;火车几乎是空的,奔驰在人烟稀少的、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他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一节长长的车厢里,那车厢就像是运输伤员的那种火车车厢。他向左看看,向右望望,看到的只是无边无际的荒僻,散落在各处的树干和树枝都七扭八歪的变形小树,它们那样子是他从未见过的,几乎是愤怒和痛苦的神态;这色暗、稀疏和悲凉的植物使这平原看起好像是一望无际的坟场。
马尔科瞌(kE)睡了半个小时,然后又是往外张望:仍是同样的风景。铁路的各站孤零零的,就像隐居者的住房;当火车停下时,听不到一点声音;他觉得好像是一个人身处迷路的火车里,被遗弃在一片大漠之中。对他来说,好像每一个车站都应该是最后一个,过了这之后,就要进入野人的神秘而可怕的土地了。寒风吹着他的脸庞。在四月底从热那亚登船时,他的家人没有想到,在美洲他居然会赶上冬季,他们给他穿的衣服是夏装。几个钟头之后,他开始忍受寒冷,除了寒冷,还有过去几天充满强烈感情冲动的白天、以及痛苦的不眠之夜给他带来的极度疲劳。他睡着了,睡了很长时间,等他醒来时,差不多都冻僵了,他感到难受。
这时,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感攫(juF)取了他,他害怕自己病倒,死在路途中,害怕自己被人扔在那荒凉的平原上,他的尸首有可能被野狗和猛禽撕碎,就像他时不时在路边所看到的某些马匹和母牛的躯体一样,看到之后他会厌恶地移开自己的视线。在那种惶(huBng)惶不安之中,在自然界那种阴暗的寂静之中,他的想象力被激活起来,在黑暗之中展翅飞翔。再说,到了科尔多瓦,他肯定能找到他母亲吗?如果她没在那里呢?如果住在艺术大街的那位先生弄错了呢?假使她去世了呢?在这种种思绪中,他又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夜间到了科尔多瓦,他听见每扇门和每扇窗户都发出高声大喊:
“不在!没有!不在!”他突然惊醒,十分害怕,他看见车厢的尽头有三个裹着各种颜色的披肩的大胡子男人,他们正注视着他,彼此之间低声地讲着话;他闪过一种怀疑的念头,他们也许是杀人凶手,想杀死他,偷走他的衣包。在寒冷和病痛之上,又加上了害怕;被打乱的想象力使他惊慌失措——那三个人一直注视着他,其中的一个向他移动——于是他失去了理智,他伸开胳膊向那个跑去,同时大喊着:
“我什么都没有。我是个不幸的孩子。我从意大利来,我来找寻母亲,我孤零零一人,你们别伤害我!”
那些人马上明白了,对他很同情,他们抚摸他,对他讲了许多他不懂的话使他平静下来;他们看见他冻得牙齿打颤,便把他们的一条披肩盖在他的肩上,又让他重新坐下,好让他睡一觉。天黑时,他又睡着了。当到了科尔多瓦时,他们叫醒了他。
啊!他吸了多深的一口气,又以多么激动的心情冲出车厢!他向一名火车站的职员打听梅奎内兹工程师家在哪里,那人说出一个教堂的名字,然后说:“他家就挨着教堂。”马尔科马上走开了。
已是夜间。他进了城。当他看见那些两旁是低矮的白房子的笔直的街道,又被其他笔直的长长的街道所穿过时,他觉得仿佛又再次地来到了罗萨里奥。但是街上人很少,在稀疏路灯的照耀下,他遇到的都是生疏的面孔,有着一种陌生的肤色,介于偏黑和浅绿之间。他抬起脸庞,看见建筑风格古怪的教堂在夜空上勾画出巨大的黑色轮廊。城市黑暗而寂静;然而,在穿过那无边无际的荒漠之后,他觉得城市是欢乐的。他询问一位神甫,很快就找到了教堂和那所房子,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拉响了门铃,把另一只手按在胸前,以便克制一下快跳到喉咙上来的心脏地跳动。
一位老妇手里举着灯来开了门。
马尔科无法马上开口讲话。
“你找谁?”那老妇人用西班牙语问他。
“找梅奎内兹工程师。”马尔科说。
老妇人做了一个双臂在胸前交叉的动作,摇着脑袋回答道:
“这么说,你也有事找梅奎内兹工程师!我看该到结束的时候了,已经烦我们有三个多月了。他们仅仅在报纸上说说还不够,还必须把它印在马路拐角上,说梅奎内兹先生到图库曼去住了!”
马尔科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然后他愤怒地发作道:“这么说,我倒霉死了!找不到我母亲,我就得死在大街上了!我要发疯了!我要自杀!我的上帝呀!那个地方叫什么?在哪里?有多远?”
“唉,可怜的孩子,”动了恻(cH)隐之心的老妇人回答,“小事一桩!大概有四百或五百英里,需要不多时间。”
马尔科用两手捂住了脸;然后哽咽着问道:“现在……我怎么办?”
“可怜的孩子,你想让我对你说什么,”女人回答,“我不知道。”
但是她很快闪出一个念头,所以急忙又说:“你听着,现在我想起来了。你这样吧,你沿着这条街向右拐,在第三个大门口,你会找到一个院子,那里有一个‘首领’,一个商人,他明天早晨跟着他的货船和他的牛群,出发去图库曼。你去看一下他是否愿意带上你,你可以给他干些活儿,他或许能给你一个车上的座位。你快去吧。”
马尔科抓起衣包,边致谢边跑了出去,两分钟之后,他就到了一个被灯笼照亮的宽敞院落。在那里,几个男人正在干活儿:把小麦口袋装到一些大车上,那些车类似街头卖艺的活动房子,屋顶是圆的,车轮非常高。一位留着小胡子的高个儿男人,裹着一种黑白格子相间的斗篷,脚蹬两只大靴子,在指挥着干活儿。马尔科走近这位,说自己是从意大利来的,是去找他母亲的,然后胆怯地向他提出那要求。
“首领,”从头到脚地看了他一眼,生硬地回答:
“我没有位子了。”
“我有十五个里拉,”男孩子带着恳求的口气回答,“我把我的十五里拉给您。在旅途中我可以干活儿。我可以去提水,为牲畜添饲料,我能干所有的活儿。给我一点面包就足够了。先生,请您给我一点位置吧!”
“首领”又重新望了他一眼,以比较客气的口气回答说,“没有位置了……再说……我们不是去图库曼,我们去另一座城市,外国的圣地亚哥。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还得丢下你,你还得步行走一大段路呢。”
“啊!我走比那多一倍的路都行!”马尔科惊喜地说:“我能走路,您不必多虑(lS);我会想方设法地到达;请您给我个地方,先生,求求您,可怜可怜我,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
“你听好,这是一次二十天的行程!”
“没有关系。”
“这是一次艰苦的行程!”
“我能忍受一切。”
“你还得一个人继续走。”
“我什么都不怕。只要能找到我母亲。请您可怜我一下!”
“首领”把提灯靠近马尔科的脸,端详着他。然后说道:“好吧。”
马尔科吻了他的手。
“今天夜里你睡在一个货车里,”“首领”丢下他时,又补充说道,“明天早晨四点钟我叫醒你。晚安。”
次日清晨四点钟,在星光照烁下,长长的车队带着巨大的响声开始行动:每辆车都由六头牛拉着,每头牛后面都跟着一大群替换的牲口。马尔科被叫醒后安置在一辆车里面,他坐在口袋上,马上又沉沉地睡着了。
当他醒来时,车队停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在太阳下面,所有的人——雇工们——都围着露天烧烤着的四分之一的一头小牛,围圈而坐,那小牛是串在一种支在地上的剑样东西上,旁边是被风吹得摇曳着的熊熊大火。雇工们一起吃饭,一起睡觉,然后又出发。旅途就这样地继续着,就像士兵们的行军一样地有规律。每天早晨五点钟开始上路,九点钟停下来,下午五点钟又重新出发,十点钟的时候再停下来休息。雇工们骑着马匹,用长长的竿子来赶牛群。马尔科点火烤肉,喂牲口,擦干净提灯,送饮用水。
这个国家就像模糊的景色一样从他眼前掠过:棕色的小树形成广阔的树林;正面为红色且筑有堞(diF)口的少数房舍散乱地分布在一些村庄;广漠的空间,也许是一些咸水大湖过去的湖底,视力所及,全是白茫茫的盐滩。四周永远是平原,荒凉、寂静。偶尔才能遇上两三个骑马的旅客,后面跟着一群散放的马,它们像旋风一样地飞驰而过。日子每天千篇一律,就像在海上一模一样;令人烦躁,没完没了。然而,天气很好。
只是雇工们,对待马尔科就好像他是他们的一个仆人,他们变得日益苛(kE)刻,有些人对他粗暴无礼,且施以威胁。所有的人都毫无顾忌地让他干活儿:他们让他去背非常沉重的饲料;让他到很远的地方去提水;他被累得身体散架,甚至夜里无法入睡,不断地受到车辆剧烈颠簸(diAnbQ)和车轮及木轴震耳欲聋的噪声的惊吓。再加上刮起大风,纤(xiAn)细的、淡红色的大量沙土横扫一切,渗进车里,钻到衣服里,弄得人满眼满嘴都是土,看不见东西,又无法呼吸,无休无止,令人压抑,难以忍受。
被劳累和失眠搞得筋疲力尽的马尔科,变得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从早到晚地被人训斥和虐待,这个可怜的孩子日益灰心丧气,如果“首领”不时而对他说上几句好话,恐怕他会彻底失去勇气了。他经常躲在车子的不被人看见的一角,把脸趴在他那只包着些破烂衣物的衣袋上哭泣。
每天早晨,他起床时,都变得更为虚弱无力,更为心灰意懒,望着田野,看见的永远是那一望无际的平原,像大洋一样无法平息的土地,他不禁自言自语道:
“噢!我到不了今天晚上了,我到不了今天晚上了!今天我会死在路上!”
疲劳在增加,虐待更加变本加厉。一天早晨,因为他送水晚了些,在“首领”不在的情况下,那些人中的一个打了他。于是,其他人出于习惯也打了他。当他们给他下命令的时候,一面用手掌打着他的后脑勺,一面说:
“流浪汉,再饶你这一拳!”
“把这一拳带给你母亲!”
他的心都碎了,他病倒了,他车里待了三天,身上裹着被子,发着烧,除了来给他送水和摸摸他的脉搏的“首领”之外,看不见任何人。于是,他以为自己快死了,他拼命地祈求他母亲,上百次地呼唤着她的名字:
“噢!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帮帮我!快来见见我,我要死了!啊,我可怜的母亲,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幸的母亲,你将看见我死在路上!”他把双手放在胸前,开始祈祷。
后来,由于首领的照顾,他的病情好转了,他痊愈了;然而,随着病愈而来的却是他旅途中最为可怕的日子,他必须独自继续行程的日子。两个星期以来,他们都是一起赶路。当他们到达去图库曼与圣地亚哥的岔路口时,“首领”对他宣布,他们要与他分别了,并向他说明了以后的路应该如何走法。“首领”帮他把衣包捆在他的肩膀上,这样就不会妨碍他走路,然后,好像害怕自己会动感情似的,简单地与他告别。马尔科勉强来得及吻了他的一只胳膊。其他那些曾经那么狠心虐待过他的人,看见他剩下孤身一人,似乎也生出一点恻隐之心,在他们离去时,也向他示意告别。他用手还礼,停在那儿望着车队消失在原野上红色的尘土之中,然后才悲伤地踏上行程。
但是现在,有一件事从一开始就让他感到了一些安慰。在多日横穿那一望无际的平原之后,现在他眼前所看到的是天蓝色的、高耸的山脉,以及白色的峰峦,这让他想起了阿尔卑斯山,让他产生一种靠近他家乡的感觉。这是安第斯山脉,美丽大陆的脊梁骨,这条巨大的山脉从火地岛一直延伸到北极的冰川大海,跨越一百一十度的纬度。天气越来越暖和了,这一点也使他得到安慰;这是因为他现在是重新北上越来越接近热带地区了。
走了很长的距离之后,他看见了一些小小的村落和一个小店铺,他买了些吃的东西。他遇到了一些骑马的男人,时而看见一些女人和孩子,一动不动地、神色凝重地坐在地上;对他来说,全是些生疏的面孔,肤色如土,眼睛偏斜,颧(quBn)骨突出;这些人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而用目光追随着他时,则像机器人一样缓慢地转动脑袋。他们是印第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