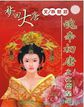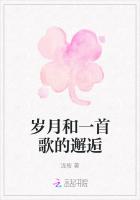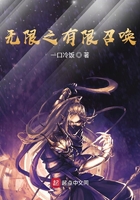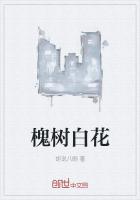《苦恋者的长歌和短歌》
王明韵
白桦先生发来短信,嘱我为他即将出版的诗集《长歌和短歌》写几行文字,答应后我又颇为踌躇:我何德何能,敢对先生的诗歌说三道四,即使再活一生也不配,亦不敢!但我又不忍放弃先生赐予我的说话的机会,我是他历时十年创作的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编者,也是他这部诗集的责任编辑之一,我感到了先生对我的期许与信任。
长年累月的读诗、写诗、编诗,既期待诗人有好诗寄来,又期待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写出一两首好诗,但总是失望多多。
写诗难,写好诗更难。在期待与守望中,面对众多诗稿,我已似乎变得有些恍惚、麻木。大约是2008年元月的一天,我收到了白桦先生从邮箱里发来的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秋瑾何许人也?林昭何许人也?我不说读者也清楚。只是不同时期两个命运相似的女人因诗人白桦而纠结在一起,让我悲从中来。再一看日期,此诗写于1997年7月15日,完稿于2007年7月15日,整整十年--我相信,当这首诗的片断尚处于毛坯状态时,白桦心中情感的岩浆就一直在滚沸中,这块坯芽扎痛着他,灼伤着他,经过十年的孕育与洗礼,才得以棱角丰满地横空出世。
这也正验证了古代大诗人袁枚说过的一句话:“人必先有芳菲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随园诗话》卷十四)那天,我没敢在编辑部细读这首诗,我怕时间太乱,怕琐事太多,打扰了对一首诗的阅读,而是把它揣回家中挑灯夜读。窗外雪落无声,书房里我怆然泪下,雪水是泪水,泪水是泪水,白桦先生的这首诗又何尝不是字字血声声泪呢?
“除非让我死/不,即使是死,我也不会忘记你/我的灵魂会把记忆交给悬崖峭壁/以化石的方式留传后世。”按理说,死,可以终结一切了,但对于诗人,却做不到:也不是做不到,是不能那样做。因为先生明白,当一种善良的声音持久沉默,另一种恐怖的声音必将甚嚣尘上!这让我想到波兰诗人蒂蒙图斯·
卡波维兹两首与“沉默”有关的诗,一首是《沉默的一课》,另一首是《沉默》,那是怎样的一课--沉默,是一只蝴蝶两翼的剧烈对折;沉默,是将大地吸干,是一条山谷被取出了耳膜--这是多么让人不寒而栗而又毛骨悚然的“沉默”,蝴蝶美丽的翅膀因对折而粉碎,山谷因被取出耳膜而丧失了听觉。“她面对的几乎是全体的背弃/成千上万个本可以拉她一把的同胞,在客观上都成为落井下石的凶手。”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黑暗,专制,人妖颠倒,苟活的人群苟且偷生,众多我辈犬儒麻木不仁,以至于林昭这个美丽的女人会留下这样的遗书:“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了。”在这里,“他们”即“我们”,即“我”,她死了,一位美丽的弱女子,一位柔弱的姐妹和母亲。而我们还活着,活在人群里,活在时光里,活在淡忘与世俗的隙缝里,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在这首100多行的长诗中,另一位女人是秋瑾,她也死了,先于林昭而死,她们时空相隔,却仿佛是死于同一个刑场,同一个刽子手,只是,秋瑾之死似乎要比林昭之死幸运得多,“甚至有人跳起来怪声叫好/像戏园里买站票的看客那样/把秋瑾姑娘当作替天行道的江洋大盗/当作杀富济贫、打家劫舍的女侠。”而我总觉得,林昭之死看似与我辈犬儒之流无关,实则实在难逃帮凶之一二!
2009年5月23日,在云南,在白桦先生当年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我把2008年《诗歌月刊》年度诗歌奖颁给了白桦。这次评奖我破例没有请评委,诗人活在那里,诗歌站在那里,先生和先生的诗让我敬慕与感动。作为数量仅存的诗人,作为多年不见的血泪之作,任何真正诗歌意义上的奖赏对于他都当之无愧,而现实给予他的,只有怀疑、盯梢、莫须有的罪名和一次次不白之冤!当下,各种奖项多如牛毛,颁还是不颁?颁给谁?在犹豫和迟疑之后,我们选择了白桦先生,这也是对我、对《诗歌月刊》的最高奖赏。简短的颁奖仪式刚刚开始,80岁高龄的白桦先生就颤抖着双手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他说:
“我十分清楚,我所以能得到这个奖项,是因为我,一个80岁的诗人还有记忆,还有清晰的记忆。还记得一百年间我们可爱的中国诞生过两位伟大的女性,一位是秋瑾,一位是林昭。”说到这里,他哽咽了,会议室的气氛也变得凝重而又忧伤,片刻,他接着说:“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提醒我们记住她们美丽的面庞!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在20世纪的史册上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让我们记住她们的来路和归途!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记住她们的潇洒身影!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让我们预见她们必将复活的日子!”五个“鲜血醒目”
的句子,几度泣不成声,白桦先生沧桑、苦难的皱纹里,尽是泪水,让在场的人无不泪流满面,在无声的敬畏中纷纷起身与白桦先生紧紧拥抱,用肢体语言传送友善、仁爱、信仰、力量与来自生命深处的体温。其实,这已不是白桦先生第一次流泪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诗人,流了80年泪水的眼眶,泉水依然涌动,时时还会长歌当哭。2008年8月9日,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在美丽的青海湖畔签署《青海湖国际诗歌宣言》的时候,白桦先生一直泪洒湖畔,因为在此时,他想到了历史的悠久,青海湖的辽阔和来而复去的匆匆过客,会后,他就挥泪创作了长诗《夏嘎巴·措周仁卓之歌》。泪水不竭,诗思如潮,大爱与痛苦也愈发至深入骨入髓。鲁迅先生曾说过,真正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远是不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这话耳熟,哈维尔似乎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知识分子不断地使人不安,作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因独立而引起争议,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是体制的权力及其妖术的重要怀疑者,是他们谎言的见证人!无论是鲁迅,还是哈维尔,其“痛苦”所指都是“知识分子”,而白桦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无论是面对多舛的命运还是面对美誉辉煌,都是荣辱不惊,痛苦的触须紧系着良心、良知、骨气、骨头,紧系着土地、人民、真理、祖国,紧系着血泪、笔墨、苦难和未来!或许,正是这种大于一己之苦并高于众人之苦的苦恋,才让白桦先生有资格成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吧!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这是我非常喜爱的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的诗句,我觉得这句话之于白桦先生,是再合适不过了。纵观他80年的人生风雨,有过驰骋疆场、出生入死的烽火岁月,有过风雨如磐、九死一生的蹉跎岁月,无情的现实给予他人生太多的不幸、不公平和苦难,对于这些苦果,他吞了,咽了,消化了,并将苦难转化成诗歌,给世界开出了一帖帖醒脑止痛的处方,让后人,让活着的人,让掌管他人命运的人别再为所欲为,让整个国家和它的公民别再付出太多太惨重的代价,也因此,苦难成了他的白发和财富。他以泪为盐,以血为墨,以笔为代言,写小说、剧本、散文、诗歌,他是小说家、剧作家,但骨子里更是位诗人,他的每一行诗都是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滚烫、温热的诗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是白桦先生一生百折不挠的追求,这与当下许多作家、诗人“只玩文字,不爱文学;只研究权术,不研究学术:只写匿名信,不写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在祝贺白桦先生《长歌和短歌》几经周折终得以出版的同时,也愿他用80岁的不老之心,引领着每一位诗歌爱好者去继续寻找文学的来路和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