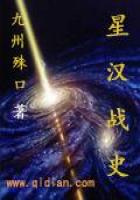这个冬天很快就过去。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仔细回味下,呵呵,真的,这才叫生活啊。
2012年冬,双11过去的第一天,12号,骑着一辆自行车开始了我不可思议的行程。
飞机飞到CD,我本人对这地方是没点好感的,单纯是因为听不习惯本地人说的四川话。
诶,兄弟,问你一下,进藏的路怎么走?
这人没怎么理我,把手上的烟随手一扔,顺便一口水吐出,用典型的四川话边摇头边说:现在滴年轻人,搞神马嘛!进藏,吃饱了没事干。走啥子走嘛,不晓得!
说到进藏,我为什么要进藏?而且是踩着单车进藏?我家姐说,我是吃饱了没事干,找累。全家人一个劲的劝我别。本想叫上我那条女,只可惜这条女不能够同甘共苦。
回到这个问题,进藏!骑着单车进藏,不能不说需要巨大的勇气。考虑这个,那个问题。不过,我不是那种光说不练得人,既然想过,那就要做过,不然,这辈子就错过了。没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决不让自己错过,错过梦想的生活。
车轮子转呀转,一个人翻山越岭,越想越寂寞。不过看看四处的风景,这点点就能让我不后悔。哈哈,这是一种天下任我行的感觉。
地势高爬,气候冷峻,蜂腰上卖力的踩着,转弯的地方有车驶来,声音传来。我止住了脚步,在右手路边是悬崖。望下去,不由觉得晕眩。还没缓过神来,刹车的声音传来,是路面太滑,车轮在地面上滑了一小段,尾箱把悬崖上的护栏撞开,一只车轮已经悬在空中。
这有些悬,全世界都安静了,等到货车一丝不动的在那了,一口气松了下来。在上前看看司机如何,只见他楞在那里。
我叫醒他,他懵懵懂懂的发现有人在车前,于是战战兢兢的下车,一副如履薄冰,如坐针毡的样子。他先没顾得上理我先,跑到了车尾看看情况怎么样。
这司机的样子,看起来只有三十出头,脸色有一条胎印,从左眼穿过鼻子到右耳,像耐克的标志一样。他掏出烟抽口。看看车,又看看我,问我,要不要抽。
抽烟是能够让人温热点,特别是在冬天。我接过烟,想问问这兄弟他要怎么办?
他说没办法,只能叫人帮忙了,这辆车大了点,货厢里装着沉沉的东西。我问他是些啥东西,他却丢了句话,说:“不要多问,你该干啥干啥。
也怪,这似乎是辆军用货车。我试探性的说:“要报警么?
他有些急,在电话寻找帮助,我隐隐约约听见那边的声音,感觉,很急很暴躁。我说:“兄弟,报警吧。这地方,你说了。
听我这么一说,他公式化的一笑,强扮出来一副好面孔,不由让我有些厌恶。他说:“兄弟你这是要去哪了?
我推着我的单车,从车与墙之间穿过,固定好,准备开始研究,是不是能够帮助他解决现在的问题。对于他的提问,我冷笑道:你看我这像是去哪?
好家伙,你这是要进藏了,这冬天进藏可不得了。
我见他智慧也就一般,于是没怎么搭理他。脑袋里计算着我手头工具和这车之间的联系。只是他不停的赞扬我伟大的举动。跟我一起走到车尾,他习惯性的抬起手顺势就要搭在车上。见此,我大声一吼,叮嘱他不要在接触这车。
从整个局面来看,整个货车有3分之1的部分悬空,加上地面湿滑,地面向下大约15度的倾斜,导致任何大于3分之2货车质量乘以地面摩擦系数的力量都可能致使车的坠落。幸好有护栏,不过这护栏怕是坚持不了多久,因为凡是地面震动,都可能致使护栏的松动。要是此刻有车路过,都会造成灾难。
我在他面前宣布了我的计划,让他在出事地点前后500米的地方,设立些路障。而我做着一系列稳固护栏和货车的工作。这时兵工铲和登山器具就成了重要的工具。
做完这些,我问他还有多久帮忙的人会来,只是此时,一些声音。是在车厢内发出,而后车子动荡,顿时这车一只后轮也相继悬空,而4根缆绳猛地一蹦,顿时一根断裂。情况继续恶劣,刹那间剩下的3根缆绳同时断裂,其中一只连着墙夹把腰壁之中实实的拉出一整块石头,有脑袋那么大,一整块击打在那兄弟身上,一击之下,两体相撞,这兄弟擦着地面向我脚下往悬崖而去。只是这哥们竟然这样被砸中了,还有意识,一把手拽住我的脚,这一拉,人仰马翻。他倒好,整个人撞上了车轮,一声惨叫,手一松,我却被甩了出去,在地上打了个滚,最后是脸面贴着地面,实实的划出了悬崖变成一条抛物线,而后紧跟着的就是那辆货车。
我想今天就是要交代在这里了?古往今来,无数英雄是死于类似这样的桥段。这悬崖下面大概四到五百米就见底了,不过幸运的是,一条河附着山,浩浩荡荡的向东流去。这样也足够我做些准备了,四百米的高空自由降落,把握住自己的身体姿势,以最好的入水方式,扑通一声,瞬间被洪流卷走,接在后面的货车,因为受阻面积大,是迟了点入水,庞大的车体与水面的冲击致使车厢破开大个口子,在狂澜之中,慢慢淹没。里面的东西,也被一卷而出,三三两两的,发出绚丽的色彩,如昙花一现,也被掩埋。
这种高度,我早已是失去了意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出现在一间屋子里,用两个字形容这屋子,就是简陋。不一会,就进来一位女子,面目还算清秀,衣着是典型的老乡装扮。没一点流行的元素。她手上拿着衣服,是我的衣服?
看看自己,哟,还好,不过是谁帮我换的衣服呢?身上穿着一身,不过怪了,这似乎是女人穿的衣服。我装作模糊的说:“这是哪啊?
这女子一眼望来,眼神交替之间,我顿时看到自己身体从下到上,一块块肉变作了石头,一种寒意心生,失去的知觉,那刹那间即是永恒,下一刻,又觉得自己全身血液奔流起来,意识恢复,活了过来。
我这是怎么了?那女子看着我向我走进,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胆怯挪退了一屁股,这?不会摔坏脑子了吧。强行接过女子的目光,隐隐约约那一刻的感觉依然。只不过这一刻好多了。
你没事吧。这女子问道。
没事,我答道。
她的声音很甜,不由的我就自我介绍起来,聊起来后,慢慢的知道,她的名字叫做:徐诗。这个地方是个小村子,名叫:山水村。只有一条山路通往了镇子。在四川边界,靠近云南的地方,一个三不管的地带。村子里大约200户人口,年轻力壮的都去了城里,留下些老弱病残,继续着上个世纪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也是我夸张了,是我这个城里人,觉得乡下实在是太落后了,才有此一说。不说别的,就说说,乡下的厕所。是一间大约30平的瓦屋,之中挖个坑,坑中搭两板子。人只要两脚一踏,蹲下来,手上一张厕纸,就可以开始干活了。乡下的小孩,经常拿这个来唱。唱着:“脚踏黄河两岸,手拿秘密文件,先是机关扫射,在是地雷炸弹。”虽然简单的四句,就很清晰的让人明白这事,什么叫“浩瀚”。
我说,谁帮我换的衣服,她不说话,有些害羞,于是我便想,肯定是她“帮忙”的。于是联系到这边上厕所的风俗,他们是上厕所不关门的习惯,人要是从面前走过去,是不能笑,或是去观察其中的细节。这样就不礼貌了。所以,我想,就算是她帮我换衣服,也没什么的,毕竟人家都没不好意思,我一个大男人,纠结个啥。
一开始,我的全身都觉得剧痛,是掉落那一刻,与水的剧烈接触力,肌肤之间一条条血丝,被强大的撕扯力压迫从肌肤中溢出。身上有明显的痕迹,我这是下不了床,只能轻微的移动自己的四肢。连我那条命根,也没了一点反应,要是换到以前,每天早上醒来,它就一柱擎天。直到一个月后,我才好了很多。随后想到,这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以后怕是要行大运了。
能下床之后,才真正注意了解这地方,徐家只剩下她一人了,这就有些奇怪,村里的其他人家似乎也不与她来往,更奇怪的是,人人看到她就回避,而只有我,才与她“相伴”想是她的那种让人害怕的眼神有关吧。虽然我也是如此,但始终人家也是我的救命恩人,也不能知恩不图报吧。
徐家祠堂,是山水村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看样子古老而沧桑,想必有些年代了,而后看了徐家族谱才发现,这祠堂已经有了千年历史,在祠堂的附近有文物管理处的同志扎岗在这。
奇怪的是,这山水村上上下下就徐诗她一人姓徐,听管理处的人说,徐家传到徐诗这一代就要断了。可惜了,在以前这山水村也叫徐家庄,树立了千年不倒,只是在以前打小日本的时代,整个族群都没落了,才有了现在的凋零。
从出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月了,也没跟家里联系过,不知道家里人会不会以为我死了。在这村子里也打听不到什么消息,先还是报个平安回家吧。
山水村通往镇子的山路很难走,这样的身体怎么了不好走那么远,只不过还是有办法的。我的背包幸好也随着我一起被徐诗搭救,里面有一些电子设备修好还是可以用的,特别是我的苹果手机,事实上还是ok的。
翻两座山,就可以看到一座信号塔,这塔好像荒废了,说是以前打越南的时期建的,其具体作用我就不知道了,是一种单纯的接发和放大信号的装置。借用这个塔,我就可以发射信号了。
一个简易的手携式电瓶,一块磁铁,电线,手机,就能够做发出一个微电波,产生一个电流,刺激信号塔的信号放大装置,利用手机发出加载文字的匹配电波,发出信息。这一系列看着简单,其实里面的学问深了。
哥,不用担心,一切顺利。一条短信被发出。
目前为止,自己的身体还算虚弱,还要多多保养才对。平日就陪着徐诗去采药,她不怎么喜欢说话,都是一个劲的听我说,我说的都是城里的东西,搞得她向往不已,我问她想不想去,她说:“她想。只是,只是,我是个被诅咒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灾难。还是不去的好。
我说,徐诗小姐,不要这么迷信好不好。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飞机大炮漫天跑。外面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没有,我带你出去,然后带你去检查检查,也许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一种超自然现象,要知道一切迷信在科学面前都要波灭。
我一个劲的说,她微笑着听我说,只是忽然,她好像想到些什么,一双秀目望向我,我不禁想要移开眼神,而忽然间内心一股勇气的洪流固定好我的身形,接过他的眼神,表现的丝毫不惧。她看这我,思想一茬,恢复过来继续说着: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哪里?就算上刀山,下油锅也在所不辞。恩公让我去哪都可以。我装做一副与薄云天的样子,油嘴滑舌的说。
呵呵,她扑哧笑出,她眼神之中的冰凉之意少了些许。她对我点头,我拉着她的手,我说等等,走到不远的地方,有一朵花儿,散开了5瓣花叶,白里透着粉红,我把它轻轻的栽下,温柔的走近,插在她的发上。我拉着她,到溪边,看着倒影。
多美啊!我赞赏到。她此刻似乎也发现溪面中的自己如此的美丽,微笑,微笑以后整个人都变了个人似的,就像一个人一辈子就只有冷漠的表情,忽然间多了种微笑的表情,一下子形成了差别,差一点认不出自己。
她都快把我忽略了,这女人爱起美来,简直没完没了。我打断了她,说着:你要带我去哪啊?可还想说些什么,没说出口,只见她脸色,忽然一变,倒在我怀里,手捂着眼睛说,好疼,好疼。
我被他这么一弄,思绪打乱,她疼的叫唤没几句,忽然呜呼,失去了意识。我检查了她的脉搏,还好只是昏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