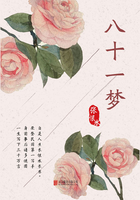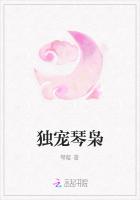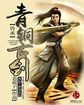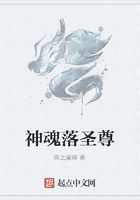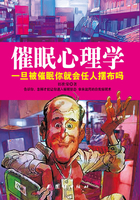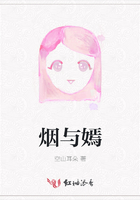“那就这么定了。一集一万块。”郭大头说,“以前物色的编剧全部给辞了,尤其是那个叫党……什么的家伙,让我们韦小姐很反感。”
张达真正答应下来之后才感到荒唐而可怕,焦影会为五斗米折腰吗?张达觉得没有把握。
韦小姐和张达路过前厅的时候,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人,带着深色墨镜,大背头油光发亮,见到韦小姐,他朝她笑了笑,显然他们很熟悉。张达猜想这可能就是那位云南客人。
吃饭时,张达问韦小姐:
“云南的那位客人是做什么的?”
韦小姐用筷子在药膳火锅里轻轻搅拌,说:
“这道当归牛腩是很有特色的菜,用冬笋、当归、香菇、白参、银白、山楂、椒茸、桂圆等做辅料,有强身祛病的功能,请多吃点。”
张达见韦小姐避而不答,自己也觉得问得过于唐突,为了掩饰狼狈,他拿起汤匙喝了口汤。
“这味道确实很奇特。”他放下匙子说。
“我在郭老板这儿只做我分内的事,文化秘书--这职业在美国很普遍,但我们中国秘书职业好像还没分得这么细。郭老板的其他事,我做秘书的从不过问,也不能过问。因为,那是危险的。我和郭老板的前妻是很要好的朋友,和郭大明也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
“曾经?难道现在不是很好的朋友了吗?”张达抑制不住好奇地问。
“现在只是工作关系。我在美国学的是犯罪心理学,但我更喜欢文艺,在郭老板手下,我能够充分发挥我这一爱好,像拍电视、策划畅销书等。当然,郭老板给我的薪水也不薄。我相信,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会有自己的经营文化艺术方面的公司的。”
凭着直觉,张达觉得韦小姐说的是实话,她和郭老板之间像是没有什么瓜葛。韦小姐说的过问他的其他事是危险的,给张达留下了扑朔迷离的悬念,但他又不好追问。
餐厅不大,但非常雅致幽静。来这里就餐的人大多是些谈生意的,他们把说话声压得很低,只能听见阵阵喁喁声。
“‘犯罪心理学’……”张达迟疑地说道,“国内好像还没有这个学科吧?你是美国哈佛大学犯罪心理学博士?”
“是的。”韦小姐有点警觉,这让张达不解。“国内这门学科还没有博士点。但有的高校已经开设了硕士研究点。”
“你们犯罪心理学都学些什么?”
“就学‘犯罪心理学’呀!”
韦小姐显然不愿谈论她的专业。张达认为韦小姐确实不喜欢她的专业,而更喜欢文艺类的东西,而有一天张达明白了韦小姐对自己专业疯狂而残酷的痴迷程度时,回想跟韦小姐最初的接触,张达觉得人生的复杂是没有界线的,任何想象都是局部。张达同时认为自己的世故精明更是一种单纯天真,我们思考问题的界面已经不同,而张达还是在原有的界面上体验和发挥世故经验。
后来,他们就做一个独立制片人所要考虑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就《山村的神秘女郎》来说,在标准预算中“线上”部分已准备得较充分;“线下”部分,包括使用群众演员、技术人员、设备、外景地与生胶片等,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张达和韦小姐分手时,表示一定尽全力帮忙,并就撤换编剧的事达成一致。也就是说由焦影任编剧--假如他同意的话。
焦影同意了。焦影一秒钟也不迟疑的态度令张达措手不及。本来张达准备了一大堆说辞,比如将计就计,通过跟郭大头的接触了却心病啦,等等。所有这一切的精心准备在焦影的果断面前都显得似是而非、不得要领,甚至可笑至极。张达并不知道,“处女问题”焦影已经解决,他已在戴仪那儿获得了与他一生至关重要的“贞操体验”。有了这种“体验”,其他事就一了百了。他甚至对郭大头的发迹抱有某种敬意,至于他妻子跟郭大头是否发生过关系这一折磨得他死去活来的悬案,也不再重要了。
“你怎么像换了一个人?”张达说,“哪一根神经又蹦回来啦?”
“心病还是心来治。”焦影说,“我在另一个人身上完成了生命的使命。怎么样,明白了吗?”
“我看还是一集一万块吸引了你!”
“不全是这样。这个片子的主题对我很有吸引力。我现在不缺钱……”焦影想说,我的一块表就值十几万。焦影想到给郭大头干活,这个不共戴天的仇人要成为他的老板,焦影倏然觉得是在玩火,心病了却了,郭大明对他的嫉恨不存在了吗?郭大明是不是在设一个陷阱有意折磨他?本来焦影是要找郭大明算账的,没想到这么快事物的面目就反过来了。焦影忽然觉得这么快答应张达是过于幼稚轻率了,也许焦影骨子里的用意是证明让他死去活来的心病确实不存在了,焦影知道他的超脱潇洒中多少含有伪饰的成分,焦影知道无论在哪方面的较量他都不是郭大头的对手,而这一次郭大头究竟藏着怎样的祸心呢?更奇怪的是,纠缠着如此复杂悠长的恩怨情仇和难以启齿的隐痛折磨的人生事件转眼之间就真的烟消云散了吗?
焦影忽然想到的是把他在郭大头手下干活的事演绎为电视剧中的情节,两个男人的内心对峙在工作中若隐若现,也许这一情节既充满张力,也扣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