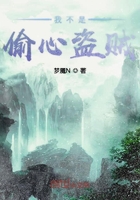早上八点钟,睁开眼睛,发现洞中的光线足以看清四周的东西。
原来是洞顶的阳光经过岩壁上无数反射点的反射,光线像雨点般洒向洞底。
叔叔搓着两只手对我说:“喂,阿克塞,怎么样?你在家里睡觉可不会像昨晚一样安宁,没有马车的声响、女人的尖叫,也没有轮船的鸣笛。”
“没错,叔叔,这里确实够安静,但是这种躺在洞穴底部的安静让人心慌。”
“行了,要是这样就被吓死过去,那怎么行,要知道,我们还没开始进入地心呢!”
“还没进入地心?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还在海平面上呢,昨天下降的高度不过使我们到达了冰岛的地平线高度而已。”
“果真如此?”
“当然,这是气压计告诉我的。”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下降的时候,气压计中的水银柱一直在上升,此刻水银柱停留在29英寸刻度的位置上。
“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普通气压计,我希望很快能用上无液气压计。”
叔叔说得没错,这个普通的气压计很快就派不上用场了,因为空气重量将超出它的测量范围。
不过我也有自己的担心,我对叔叔说:“当气压逐渐增大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很难受?”
“不用担心,我们慢慢地,一点点往下走,会逐渐适应密度越来越大的空气环境。我们和飞行员不一样,他们升入高空之后会觉得空气稀薄,不够用,我们则正好相反,不过我还是更愿意保持现在这样的水平。不说这些浪费时间的话了,我们之前扔下来的东西呢?”
叔叔的问题让我们想起来,昨晚我们就找过之前扔下来的包裹,但是没找到。叔叔问汉恩斯,汉恩斯的眼睛像猎人般敏锐,他四处看了一下,最后说:“在上面呢。”
我们抬头望去,果然,包裹在我们头顶的一块凸起的岩石上,目测有100英尺高。这位冰岛人没用几分钟,就爬上去把包裹取了下来,整个人像猫一样灵敏。
“好了,快点吃早饭吧,下面要走的路还长着呢。”叔叔说。
早餐的内容有饼干、肉和杜松子酒,每个人都吃了些。
早餐结束,叔叔拿出笔记本,又一件件摆出仪器,测量记录了各项数据:
星期一6月29日
间:早上8:17气压:29.7英寸温度:6度方向:东南偏东从指南针上的显示来看,我们马上要进入黑暗的通道。叔叔仿佛显得很兴奋,激动地对我说:“阿克塞,这才是真正的旅行,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地心了。”
说罢,叔叔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感应线圈,把它接到提灯上,黑暗中马上亮起了一道光,照亮了前行的路。
汉恩斯拿起另外一根路姆考夫感应线圈,接亮了另外一盏提灯。在这种人造光的照应下,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走在黑暗中,哪怕周边都是些易燃的气体也不用担心。
“出发吧!”叔叔喊道。
我们每个人拿起自己的行李,叔叔走在最前面,汉恩斯走在中间,我走在最后。在走进黑暗的通道之前,我抬头通过洞口望了一眼冰岛的天空。
1229年,这座火山最后一次喷发,当时岩浆便是沿着这条道路喷发出去的。岩浆给道路镀了一层光滑的物质,灯光照在上面,显得格外亮。
路上全是不低于45度的斜坡,怎样控制自己不滑下去成了我们唯一需要对付的难题,好在斜坡上面有不少凸起的岩石,可以被我们用来作为台阶。至于行李,我们采用老办法,用绳子拴住,一点点放下去。
那些被我们当作台阶的凸起岩石,其实是钟乳石;此外,还有类似于水泡的多孔熔岩;类似于眼泪的石英,石英不是很纯,但里面夹杂的玻璃很纯,它们悬挂在我们头上,像极了吊灯。我们从下面走过,它们在上面闪烁,就像是代替魔鬼宫殿向擅自闯入者打招呼。
见到如此美景,我不禁开口喊道:“叔叔,你看,真是太壮观了!”
“哦,我的孩子,你也看到那些美丽的东西了。不过,我敢说接下来你将见到更美丽的东西。走吧,让我们向前进。”
其实说“走”有些不太恰当,最合适的词应该是“滑”,我们沿着斜坡,一路下滑。这让我想起了维吉尔的著作《轻松坠入地狱》。通过我对指南针不断地观察来看,我们一直沿着通道走向东南方。
通道里的温度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已经走了两小时,温度只增加了四度,现在是十度。这也说明了亨弗里·戴维的推论是正确的。温度基本没变化,说明我们不是在向下走,而是在向前走。叔叔一路上都在计算着脚下的坡度,他肯定知道我们下降了多少米,但是关于这一点,他保持沉默,我们也就无从知晓。
晚上八点的时候,叔叔示意停止前进,汉恩斯卸下行李,坐在了地上。我们把提灯挂在突出的岩石上。此时身边竟能感受到微风,像是处在洞穴中,而非地道,这让我觉得有些奇怪,风是哪里来的?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寻找答案,疲倦和饥饿让我懒得想任何问题。我们已经连续走了七个小时,换做谁也累得够呛,所以当听到叔叔说停下的时候,我那种高兴就不用提了。汉恩斯拿出食物,摆在熔岩上,每个人的胃口都很好。水的问题让我担忧,我们已经用完了一半的水,但至今没有见到地下水源。
我把这个问题抛向了叔叔,他有些不屑地说:“怎么?害怕了?”
“我们的水只够用五天了,我当然担心。”
“不要担心,我告诉你,阿克塞,我们会找到水的,而且保管多的让你吃惊,足够我们用。”
“你说的水什么时候能找到?”
“首先需要走出这片熔岩,你总不能让泉水从岩石里淌出来吧。”
“谁知道这些熔岩还要走多久,没准还早着呢,我觉得我们才下降了一点点。”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要是我们进入底层的话,温度应该上升不少,不会是现在这样。”
“那按照你的推断,现在应该是多少度才正常?”
“现在温度计上才15度,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只增加了九度。”
“所以呢?”
“我的结论是:按照常理,每深入底层100尺,温度上升一度。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比如西伯利亚的雅库斯特,因为岩石导热性不一样,那里每深入36英尺就会上升一度。在这样接近火山的岩石中,每下降125英尺才会上升一度。我们可以按照最乐观的这种情况来推算,就能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
“好吧,孩子,你快算吧。”
“这再简单不过了。”说着,我开始在笔记本上计算这些数字。
“9乘以125等于1125,就是说,我们现在身处地下1125英尺深的地方。”
“没错。”
“所以……”
“你算得没错,但是按照我的观测,我们现在位于海平面以下一万英尺的位置。”
“怎么可能?”
“当然可能,在这里数字已经失灵了。”
叔叔说得对,我提不出任何反驳的意见。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远远超过人类所达到过的最深的位置,比狄罗尔的基茨布黑尔矿区和波希米亚的威尔腾堡都要深,深度已经超过了6000英尺。如果是按照我的计算方法,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应该是81度才对,但是温度计只显示了15度,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