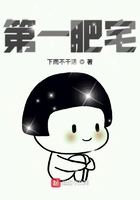第一个出现的人是潘西。他有着像古钱币一样颜色的手臂,飘忽的微笑短暂到令人难以察觉。他从三种角度检视研究过那只象拔蚌后,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冷藏箱中,再往里塞进三十二个温哥华蚬和八个奶酪蛤。
他很少说话或和我有任何目光接触。他在研究过我对这些贝类的发现时间和地点的记录清单后,会再和州政府的水质检测资料作一次交叉对比。然后,他会在沙滩上卷起一根烟抽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动作总让我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一直到这天下午为止,我还是想不通潘西为什么会不嫌麻烦地来和我做生意,这感觉像是在帮我的忙一样。无论“神秘西贡”需要多少蛤蚌和牡蛎,托考持海产公司都可以充分供应才对。而且,潘西虽然是餐厅的老板和管理者,但每次只要我打电话,他一定亲自并且迅速地赶到--即便只是一只象拔蚌也不例外。
这一天,他连抽了两根烟,这样他才有时间讲完他的家人是如何从柬埔寨的东南角一路走到泰国的故事。
“我们在晚上赶路,排着队走,直直的一行。”他挥着香烟在空气中用力一劈,表示那队伍有多直。
“领头的永远是我母亲,所以如果我们误触地雷的话,损失的就只有一个女人。”他摇摇头。
“真是疯狂。”
我试着想象妈妈带领我们在黑暗的丛林中穿越地雷区的画面。那不只是用疯狂可以形容的。
潘西说,他们离弃的家园距离一个大海湾只有不到两公里远,他和父亲常到海湾去钓鱼。“比你采集到的要大得多,但有时也有和这些差不多的。”他说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非得离开那个美丽的海湾,去住臭得要死的难民营,他母亲就是在那里得了某种粪热的病死掉的。“到现在,回想过去的事,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我爸妈快离婚了。”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大声地将这句话说出口,所以我不知道听起来会如此的刺耳。“我听到他们说的。”
潘西跟我说对不起,但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和一般人不一样。他道歉是因为自己说得太多了,因为他说了太多私人的事,让我也说出了心里话。但让我呼吸不过来的并不是爸妈要分开的事,而是他让我了解到,我很可能因此也必须和我的海滩说再见。
他捻熄了还未抽完的第二支烟,畏缩或是尴尬地微笑了一下后(实在很难分辨),递给我一张崭新的二十元和一张十元的钞票,叫我不用找了。
一小时后,一辆粉蓝色的埃尔卡米诺小卡车驶上我家的车道,听起来消音器已经出故障了,我一边听着他的车隆隆作响地开来,一边喃喃复诵着坚定的台词,打起精神迎接B.J.的到来。
我打过电话给一些大型水族馆,但他们好几天都派不出人来。我怕海蛞蝓撑不了太久,而且我的水族箱对于向日葵海星来说也太小了,所以我只好勉强在B.J.的电话答录机里留下了讯息。
我不是从克拉马教授那里认识B.J.的,而是他自己找上我的。我只知道他有朋友在交易珍奇的海洋生物,而且还认识塔克玛市立水族馆的人。我甚至不晓得他的本名是什么,只知道叫他B.J.就行了。
他从冒着烟的车子里走了出来,茂密的络腮胡,双颊布满深刻的皱纹。他曾经自称是墙板工人,但我怀疑他根本没有工作,虽然他有着一双像磨破的帆布手套般的大手。
B.J.和潘西刚好相反,他老是喜欢跟我杀价,不过我心里暗暗发誓,这次一定要守住底线,否则宁愿什么都不要卖给他。我要他在车库外面等着,我把要卖的东西拿出来。
但他还是跟了进来。
车库里塞满了工具、备用的弹簧床垫、脚踏车和一些废旧家具,根本没空间让我们两个人同时站在水族箱旁。当他朝我弯下身来时,我可以闻到从他嘴里传来的意大利腊肠味。“让我看一下。”他要求道。
我试图往后退,免得碰到他,结果被我妈妈那辆从来不骑的脚踏车绊倒了,和车子一起跌倒在水泥地上,还被齿轮划伤了手臂。
B.J.连头都没回一下。“海蛞蝓在那个袋子里放太久了。”
“它的状况很好,”我擦擦手臂上的血说,“我常常换水,你可以看我的记录。”
B.J.从来不跟我要纪录看。我在他的答录机里说过我有一只海蛞蝓要卖十元,一只向日葵海星要十五元,还有一只很特别的杂色海星要五元。我告诉过他这都是底价了。
“这向日葵海星也太大了,没人会要这种东西。”他坚持说,“根本是只怪物。”
“好,”我知道他是在吹牛,“那你要海蛞蝓和这只蓝色的海星吗?”我努力让语气听起来很冷淡。
“你没看到我在考虑吗。急什么呢,小鬼头!”
“我要跟我爸去钓鱼,”我撒了个谎,“他在家里,就等着我出发了。”
B.J.哼了一声:“算帮你一个忙吧,这三只我全要啦。”
我把两只海星装进袋子里,和海蛞蝓一起拿到外面。他把它们全堆在货车车厢里,好像那不过是两袋钉子一样。
“你没有容器可以把它们倒进去吗?现在天气蛮热的。”
他拿了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在我面前晃了晃,好像在逗狗一样。
“是三十元!”我说,不去理会那张在我们中间摆来摆去的钞票,心里后悔得要死,刚刚竟然忘了照演练过的那样先向他收钱,“这价钱是--”
“那只海蛞蝓已经快挂了,”他打断我,“你自己很清楚。如果它在哪个浑蛋的鱼缸里马上死掉的话,我就得退钱给人家。而且那只蓝色海星我不知道有谁会看得上眼。还有,我刚也说过了,那只向日葵海星太大了,我的顾客没有人会买,要是水族馆也不需要的话,我就麻烦了。二十元已经很多了,够你买一堆泡泡糖啦,小朋友。”
我希望他没有看到我脖子上抽动的肌肉。“三十元!”我本来还想多说一些话,但怕会抑制不住尖叫起来。
“有没有人和你说过,你真是个顽固的小浑蛋!这样吧,免得你一会儿哭闹起来,我们赶快解决算了。二十五元你要不要?”他把二十元钞票先递给我,好将手塞进口袋里翻找。
等我一收下钞票,他拍拍口袋,露出一个局促不安的笑容说:“看来我得先欠你五块了,好吧?”
眼睁睁地看着墙板工人B.J.开车离开,还载着我最喜欢的海洋生物,这令我感到一阵恶心,等我想到以后可能再也不会看见他后,紧咬的牙齿才放松开来。
大约一个星期以来,夏天又重新恢复原有的脚步,继续往前走。我甚至还说服爸妈一起玩益智问答棋盘游戏。本以为这种游戏可以让家人感觉更亲密,结果却只是让我爸觉得自己很笨,还让我妈很火大,因为我抽到的问题都很简单。而在这段期间,弗洛伦斯也教了我一些可笑的东西,像是怎么解读塔罗牌之类的。那还真是会让人搞昏头,每张牌几乎可以代表任何意义。像“恶魔”可以代表启蒙、束缚、自我惩罚、分离或其他六种可能。如果我太努力思索的话,脑袋一定会打结的。
有一天,弗洛伦斯突然变得全身都很僵硬,有两次必须得靠我帮忙才能从椅子上起身。但我没去多想这件事,我脑子里除了安琪·史坦纳之外,容不下任何东西。她绑架了我的整个思绪,我连书都快看不下去了。
有一个晚上,我还溜到她的窗口偷看。我盯着她卧室天花板的一个角落研究了至少二十分钟后,才想到她可能根本不在家,只是忘了关灯而已。如果史坦纳法官逮到他的牡蛎先生--也就是下一个伟大的雅克·库斯托想偷看他女儿没穿衣服的话,不知道会说什么呢?
隔天早上,我在报上看到一个长相平凡的家伙的照片,旁边还写出了他的名字,另外还有两三句的报道,简单交代了他是一个第三级性罪犯。性犯罪总共到底有几级呢?偷看人家卧室算第几级?我可以想象报上刊着我的照片,旁边还加了几行警语,说明迈尔斯·欧麦里是个喜欢在窗边偷窥的第九级性罪犯,而且这家伙在脆弱的状况下,连在幻想时都会粗心地将屁股、乳房、脸蛋的位置搞错。最后,当然还要加上一句不祥的预言:欧麦里很有可能会再次作案。
不过除了安琪让我心烦意乱之外,这个夏天开始变得和以前没什么两样:漫长,毫无特色,容易被遗忘。不过至少远离了乏味的教室、辣酱牛肉汉堡和礼堂里不时出现的呕吐物--警卫会用一种栗色的沙子将呕吐物盖住,结果闻起来比原来还臭。
要说服费普斯进行他的第一次夜间潜逃行动并不容易。他继父睡得很浅,连他老哥都不太敢偷溜出来。不过那天我到达时,瘦皮猴肯尼·费普斯已经在查塔姆湾等着我了,他拿着一支几乎黯淡无光的手电筒,正站在他的桶子边发抖。
他白天时的威风模样全都消失无踪,事实上,他看起来快被吓死了。对任何感觉健全或没有喝醉的人来说,夜晚的海滩的确会有这种效果。嘈杂的海鸥和专吃腐肉垃圾的乌鸦令人安心的吵闹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蝙蝠快速飞行的呼嗖声,和猫头鹰尖锐刺耳的叫声。就连一只中等体型的寄居蟹拖着壳在沙地上走路发出的细微摩擦声,听起来也让人觉得备受威胁。曾经有一次,我在查塔姆湾瞥见一只巨大的杜宾犬,吓得我蹲在那里十五分钟一动也不敢动,虽然之后发现那不过是一根漂流木,但还是害怕了好久才恢复过来。
费普斯从黑色的沙地里采了十几个奶酪蛤,再加上我保证会给他法定的抽烟休息时间后,才渐渐恢复一点他骄傲自大的本色。我陪着他一起点了根烟,他这时的情绪已经不错了,连我没把烟吸进去,也没换来他任何嘲笑。他甚至还由着我拼命指给他看我在月亮上发现的打架痕迹。
“所以第七频道的那个宝贝什么时候会播我们的片子啊?”他问。
“这很难说,”我突然间变成了媒体专家,“我希望永远都不要播。”
“该死的!我那天很帅耶!”费普斯的牙齿和月亮一个颜色。
想到第七频道还没有任何行动,这令我感到不安,我想这应该是我把他们留在答录机的三个留言都删掉的后果。想到要跟那个假人模特儿说话,就让我觉得肚子痛,尤其是在接到克拉马教授那通来电之后。他问我关于威士忌角的新种螃蟹和煎饼湾的新种海草的事,因为那个女记者跑去问他了。我把所知道的告诉他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唉,迈尔斯,你知道你这样让我和州政府看起来有多蠢吗?”
我心脏跳得飞快。“我没想到那是多么了不得的大事。”我尖声说。
“哦,迈尔斯,你当然知道什么是物种入侵,以及那会导致多严重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