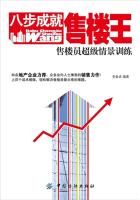孔子的感应说
孔子主张感化而不主张赏罚,是基于他的“性纯可塑论”。子贡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重视教化,很少谈论性与天道的问题。但他却是我国先哲中第一位讲性的。虽然他仅仅提及:“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谓“相近”和“相远”,系指人与人间的相近、相远。“性相近也”即“人人所禀受以生的性互相近似”;“习相远也”为“原本相近的人因习染不同而拉长其距离”。不过习之为用,陈大齐先生推定其为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即“可导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
正因为其双向,所以习的结果,使人在行为的善恶上互相远离,造成“相远”的现象。孔子的“性纯可塑论”
孔子的“性纯可塑论”,要点如下:1.人性是善是恶,孔子并未提及。《孟子·告子》记载:公都子向孟子提出若干种人性学说以后,问道:“今日性善,然则彼皆非与。”问话中用有“今”字,可见孟子的弟子确认性善之说,应该是前人所未道。2.人由先天遗传下来的性,初生时像白纸一般。后来信仰孔子这种“纯而无所谓善恶的”性说,似乎只有告子一人。他的著述没有流传下来,仅仅在《孟子》一书里有他的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3.性相近也,指先天的性互相近似。顾亭林在其《日知录》中引曲沃卫嵩说:“孔子所谓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谓之相近乎?”因此后世儒者,大多认为性善之说,本乎孔子。孙中山先生则具体说明:“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天要做的。”
“保”和“养”是人人所禀受以生的性,亦即生命的表现,大体上是一致的,应该是孔子“性相近也”的最佳诠释。4.习相远也,后天的习惯,把人与人间的距离拉长了。孔子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上知、下愚的人,是不为教育和环境所改变的。但是这两类人,为数极少。我们所重视的,乃是界于上知、下愚之间,众多的“中人”。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又说:“中人若遇善师,则可上;若遇恶人,则可下,故再举中人,明可上可下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说:“中人,为中知矣。”中等智能的人,易受后天教育和环境塑造,有的向善,有的向恶,因而彼此相远。5.一般的人,都是“中人”,可以任由后天环境塑造,改变其形态。告子也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美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Dewey)在其《人性会改变吗?》(DoesHumanNatureChange?)一文中指出:“当人性科学发展到像物性科学一样,关于人性如何最有效地改变的问题,自是十分重要。所问者不是能不能改变,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如何加以改变。”人性可变,于今大致获得公认。为政以德方能有良好的感应由于性纯可塑,而塑造者,就是环境,于是孔子创立仁道,把它当做塑造人性的理想模型,希望把所有“中人”的性,都塑造成他所拟定的理想模型一般。合乎仁道理想的环境,就是塑造人性的实际模型。仁道是人生活动的目标。
但是我们有了这样美满的模型,又如何才能使更多的人刻意向仁而不违背它呢?如果依照现代的观点来说,必然会提出“施加压力”的主张。孔子并没有完全忽略“压力”的必要性,只是他认为:压力可以分成“外来的”和“自发的”两种。施以外来的压力,本身就不合仁道,而且容易引起承受者的反感。不如激发他内在自发的压力,让他自愿走向仁道。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任何人从“我欲仁”而“志于仁”,便是自发地“用其力于仁”。结果必然走上仁道,因为一个人真有一天决心用力去行仁,不可能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内在的自发压力,胜过外来的施加压力。前者是“自力”,后者则系“他力”。依据“作用、反作用”定律,“自力”的运作空间,限于人的体内,作用越大,反作用越强,自己驱使自己走向仁道;“他力”的情况刚好相反,运作空间介乎人我之间,作用越大,反作用越强,适得其反地把人逼得近乎盲目地反抗,因而一旦压力减弱,就趁机转入邪途了。自发压力是“应”,外面的环境才是“感”。孔子倡导管理者“为政以德”,这样管理者就好像北极星静居其位,而满天星斗都环绕着它正常地运行,即能“无为而治”。
《论语·颜渊》记载,季康子向孔子请教管理的道理,说:“如果杀了坏人以成就好人,你看怎么样?”就是问孔子“施加外力”的效果如何。孔子说:“何必用杀呢?”可见他并不赞成假借外来的压力,以免造成“以杀止杀”的“互杀”恶果。他认为“你喜欢好事,大家就会做好事”,有德的管理者,最好像“风”那样,微微地吹着,使被管理者如“草”一般,在和煦中不知不觉地自愿顺风而倒。管理者所散发的,是柔和的微风,为大家所欢迎的“和风”,绝不是“暴风”。把草连根拔起,就不是良好的感应,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刑是赏罚之具,乃系“他力”,礼、德才是良好的“感”,可以激起“自力”的“应”。当然,管理者是众人“十目所视”的对象,也就是“十手所指”的目标。由于大家十分注意,成为最具有感化力的一种“环境”(他人对“我”而言,其实都是环境),所以孔子一再强调管理者必须先自正其身,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孟子的感应律
依据对公司雇员的访问调查,部属多半不满意自己的主管,而且他们还抱怨地指出:没有不好的部属,只有不好的主管。孔子说“有教无类”,即君子有教,则人人都可以为善。拿破仑自夸有能力“以泥土造军长”,他说:“头脑过热的人,我则冷之;头脑过冷的人,我则热之。我要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我就能使他照我的意思去变。”我国向来也认为第一等主管,乃是善于陶铸人才的人,就像具有“点石成金”的手段,似乎可以作为佐证。
但是,担任主管也鲜有不认真负责的,他们只是鞠躬尽瘁,却不幸劳而少功,好像在球场上奋力奔驰,满身大汗,却屡投不中,未能得分。我们最好肯定:没有不好的主管,只是稍为欠缺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我们便承认部属是人而不是物,是人便有感情,亦即有其好恶,诚如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巴纳德所说:“关于管制或影响集体的行动,不论做法如何,常有其不可预测的反应,或好或坏,颇难以确定。”但是,西方学者仅仅了解领导的过程是领导者、跟从者及其他环境因素的方程式,却无法突破这种不可捉摸的情况,寻出我们的传统法宝:孟子的感应律。
孟子的感应四律是安人的法宝孟子虽然主张“性善”,却也认为人性是可塑的,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类本来就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它们是内在的,自己努力去求,就能够发扬光大;自己不努力,等于舍弃原有的东西。他显然是重视“自力”的,却进一步把“父子”和“君臣”的感应加以适当的区分。《滕文公上》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尽心下》则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明示君臣间的感应关系不同于父子,前者主“敬”,后者主“恩”。君臣之间应该互敬,《万章下》说:“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
孟子把这种上司与部属的感应,归纳为四个定律:1.出尔反尔律。在《梁惠王·鲁哄》中邹穆公问孟子:“我的将士在前方作战死的,有三十三人之多,而百姓没有一个为国家效死的。如要杀他们,是不能杀尽;如不杀,他们都眼睁睁地看长官战死而不肯救,这该怎么办。”孟子答道:“平时凶荒饥馑的年岁,老弱的倒毙在田沟间和山涧中,强壮的流离颠沛在四方,总共有几千人了。但是君王的仓廪盈满,府库充实,官吏们没有把灾情向上呈报,设法救济,这是对上疏忽责任,对下残害百姓。所以曾子说:‘警惕啊!警惕啊!现在你们做的恶事,将来一定还报在你们身上。’那些百姓,现在才算得到机会来报复,不要去责怪他们吧!如果能够施行仁政,那些百姓必会自动亲近君王,拼命地替长官效忠了!”
曾子的话,原本是“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旨在提醒我们:“你如何待人,人亦将如何待你。”这和孔子一贯主张“欲正他人,必先自正”的道理,完全是一样的。2.施报对等律。孟子向齐宣王说:“人君看待臣子如同手足,臣子就把人君当腹心看待;人君看待臣子如同犬马,臣子就把人君当路人看待;人君看待臣子如同土芥,臣子就把人君当敌人看待。”手足必然听命于腹心,上司视部属如同左右手,部属当然视上司为腹心而彻底服从。犬马系看门、拉车的工具,上司把部属当做利用的器具,随时可以更换或抛弃,部属也就视上司为陌生的路人,彼此既然缺乏深厚的感情,那么随时可以跳槽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