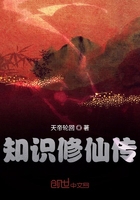黑蛋爹,小学文化。酒精作用下,他狗嘴里吐出来的东西一套一套的,人送外号“嘴皮大王”。
一,这爹能晕
父母早亡,邻居看不惯他这样的老鼠药皮子嘴。
他张口回应:“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出了水平,舒服了胃。不中,你也来俩口?”
妻子看不惯他这种油腔滑调,特别是嗜酒为命的饕餮行为。
他张口对答:“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
妻子说,那也不能天天喝得晕头转向地不顾家。
“喝酒图醉,娶老婆图睡。咋不顾?”
说着,他醉马失敛地扑过去。气得妻子只该离家出走,不再跟他过日子。
之后,没尾巴流星,少了绊挡,黑蛋爹更是大喝特喝恶喝哩。
这不,寒冬腊月夜,跑到二十里开外的集镇上,黑蛋爹又喝将起来。
熟醉,三两酒下肚,黑蛋爹话匣子打开,牛笼嘴卸套,云天雾地,滔滔不绝,卖弄口才,举杯换盏,瞎扯胡喷。
见他嘴巴上开关失灵,一位老者上前劝说,别喝了,天黑了,回家去吧。
“东风吹,战鼓擂,男人喝酒谁怕谁。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喝活着太疲惫。”他醉眼张飞地拉住老者:“革命领导不喝酒,狗屁朋友也没有。来,来,干了这杯!”
谁革命领导了?你这人,咋这样不伦不类不着调的!
咱都是平民百姓,不要再胡言乱语。老者批讲他。
“平民百姓不喝酒,一点快乐也没有。来,爷们,干了这杯!”
“跟你喝酒?丢身份!”好像孔乙己,是唯一站着喝酒的长衫叫花子,谁愿意与他同类为伍,煮酒论英雄?老者起身,打算离开。
“兄弟之间不喝酒,一点感情也没有。走什么,不够意思。”他
踉跄着上前阻拦,“来,来,干了这杯!”
“胡言乱语。去你的!”
“哟呵。处女阶段,严防死守。哥们,真有你的,装得挺像,滴酒不沾?话说,少妇阶段,半推半就。来,来,干了这杯,还有一杯。”
“错辈儿,鸡不认鸭子,还喝?”
“鸡不认鸭子,不打渣子。不喝不笑,生人不热闹。”黑蛋爹还有点色哩,他趔趔趄趄,借酒壮胆,缠向门口边一位单身吃麻辣烫的女子,“男女之间不喝酒,一点机会都没有。妹纸,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来,来,干了这杯,还有一杯。”
“嘚瑟!”女子回绝。
“出门在外,寂寞难耐。妹纸,感情深,一口闷,扯嗓子,倾盆大雨。”
“去你的,你是谁呀?”
“装醉,不给小费?抖擞精神,剩掉两杯,权当小费,妹纸。”
“吼什么你?”女子扶墙站起,也要离开。
“赢了不喝,输了耍赖。扶墙好走,墙走我不走。”他死皮赖脸,纠缠,“只要感情有,睡谁都是睡,喝啥都是酒。来,来,以水代酒,干了这杯!”
“喝死你!”女子说话结实,发狠。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缥缈梦里有我紧相会。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上边有人,干爹用劲,临时工照样提干。这叫感情到了位,不喝也陶醉,昏睡百年才乏味。”
二,不怕谁不醉
“别扯啦!我这里可不留客人住宿。”小吃铺老板担心事态闹大,及时阻挡上来。
“麻雀有窝,狐狸有洞。谁稀罕你这破庙,我还要住我的老店。”言语之间,黑蛋爹开始闪舌头,开始腿脖子发摆。
“你,住得起店?”众人捧腹大笑。
“不诓你们,喝得再醉都住老店。”黑蛋爹身子一歪,瘫倒在门边。
“起来,起来!不要赖躺在我这里呀!”小吃铺老板不耐烦地吼叫,真想是扔癞皮狗一样给他撂倒在大街上。
“没事。一会儿,我那宝贝儿子会来接我回老店的。”
“你这号酒精鳖子,还会有儿子?”众人愕然,“别是拐卖的儿童吧?”
“怎么,你们还别不相信人?货真价实,我自己的窑自己的灶自己的模子,标准不山寨。一会儿,我儿子来了,你们见识见识,可别看得醉了,眼气死?”黑蛋爹满脸幸福荣光,无比自豪地夸耀,“牛逼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哩。比起我儿子,你们的那都是窝瓜菜。”
“呵呵!”众人鼻子都气歪了,“晕吧,喷吧!狠劲,晕喷晕喷!”
黑蛋爹身子发软,好像一摊烂泥,只是头脑尚且清醒,他拨打手机。
约摸二十几分钟之后,一辆电动三轮车,“嘀嘀!”鸣叫着寻找过来。
“爹!”一个明显乳臭未干的娃娃,驾车呼叫。
“黑蛋娃,宝贝儿子,你爹我又喝醉了。”黑蛋爹耷拉着抬举不起来的脑袋壳子回应道。
“这,就是你眼气死人的儿子?他今年几岁了?”众人不约而同地发问。
“七岁。”
“七岁!娃娃子,黑灯瞎火,独自开三轮,来回几十里疙瘤拐弯岗坡路!”有人了解黑蛋爹的家庭地形。
“如果是你们家七岁娃子,中球用,早废了!俺们,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嘴皮大王,黑蛋爹好像又要来劲。
“晕,真叫晕!”
苍茫的夜色下,凛冽的寒风中,七岁娃子驾车拖带着醉成烂泥的爹。
谁见了不感慨,不震惊,不看得人都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