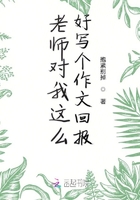[1]这是一场悲伤的相识
轰轰烈烈的炸弹案事件结束之后,莫白和韩真真被拘留了,同时被拘留的还有傅颜若的爸爸。他被查出和纵火案有关,被判处死刑。
原来韩真真的妈妈在十八年前是傅颜若爸爸的秘书,有一次傅爸爸酒后乱性强暴了韩真真的妈妈。韩真真的妈妈生下韩真真后丢了工作,被家人唾弃,很快就疯了。傅颜若被丢在了汽车站被刚好出差的安海孤儿院院子给带回安海去了。后来韩真真外婆找到,领回长乐。外婆在几年前得了重病死了。韩真真一直和妈妈相依为命。
所以韩真真的身上,总有一种对命运的无奈。
他们出来的那天,我陪蒋幂去接他们。蒋幂显得很平静,她只是很温和地对莫白说:“我来接你们。”
韩真真和莫白的精神状态都不太好,韩真真走到蒋幂跟前,说了一句:“蒋幂,你这个傻女人,一辈子都这样。”
蒋幂突然就笑了,问:“那你们跟不跟我这个傻女人一起走呢?”
那一刻,我看到远处的莫白,脸上也微微地露出了笑容,细密的阳光像一张网,罩在他的脸上,罩在隐隐有些忧伤的眼睛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守在韩真真身边我好像又看到了夏时。多少年,他总是用这样的目光看着我,深不见底,充满忧伤。
蒋幂这么多年寻找的人,他终于出现了。同时,她也知道,她和这个人不会有别的感情发展。
我和蒋幂在走回宿舍的路上,一直牵着手,月亮是月牙弯,垂在夜幕上像好看的弯钩。蒋幂捧着一瓶红酒往嘴里倒,我们两个喝得醉醺醺地在路上东倒西歪地行走。
这是高考的三天假期,教室做了考场,所以其他年级集体放假三天。这三天,我没有联系夏时。
他的腿好了,所有人都感到惊讶。我远远地看着他,内心有许多复杂的情绪。我一直在思考我和夏时的关系,扑朔迷离,纷繁纠结。
阮小骨告诉我夏时不打篮球的原因,小时候有一回他用篮球砸到我的脑袋,我哭了几个小时,再也没理过他,后来夏时就对我发誓,绝对不再打篮球,我才和他重归于好。
原来我小时候,是如此霸道无理任性矜贵的女生。
我和蒋幂在空旷的草地上把头抬起来看星星,蒋幂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原来真的是,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他却永远不属于你了。”
我说:“蒋幂,对我来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爱,可是我们却永远不能在一起了。”
6月8日的晚上,我和蒋幂像两个被人丢弃的孩子,在草地上默默哭泣,月光那么凉,照在我脱了鞋的脚丫子上。我们就是从一个日夜到另一个日夜,在时间的转换中,一点点地变得忧伤。
唐欣和我最后的谈话,是关于夏时,她说:“云朵,我不管夏时腿是不是为了不出国而假装没好,我也不计较他为你做了多少事受了多少伤,他对你好,这是我没办法控制的事。也算我们家亏欠你的。很多事,到如今,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了吧?这么多年你一直找寻的答案,你都已经找到了吧?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你和夏时,永远都只能是兄妹。只是兄妹。没有其他。你明不明白?”
唐欣依旧如往常一样精明干练,说话强势,不能人半点转圜的余地。哪怕她已经猜出我知道了事情的全部,她也没有要和我解释什么,她只是用她一贯的风格告诉我,我和夏时,除了做兄妹,没有其他。
我把那些要问出口的问题全部吞回肚子,望着眼前我喊了五年的妈妈,心凉至深谷之中。
[2]真相如想象中让人心凉
我自己去了阮叔叔的牛肉面店,到的时候阮叔叔正在下面条。他的头发有些油渍,脸上有层叠的肉和皱纹,他的目光憨厚平凡,他是唯一一个在我失忆后来寻找我的人。爆炸事件闹得很大,我想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报纸,所有人的脸都像放了特写,明目张胆地被无数人翻阅。
阮叔叔看到我来,端了一碗牛肉面给我,在我没开口之前,就说:“我早就知道,事情肯定要捅破,婉云来了,她不可能会让我们安生的。”阮叔叔的眼睛里,含着眼泪。
“婉云和夏时,是一个爸爸,他姓夏,当时在我们景坊是新闻局的局长,他有钱有地位,他喜欢唐欣,是因为唐欣有一回采访他,他就被她吸引了。唐欣是外地来的,家在很偏僻的小镇,读大学很不容易,所以她很珍惜每一个机会,也比任何人都努力。她家里还有三个妹妹要养,生活很艰苦。直到遇到夏时的爸爸,对她很好,也承诺会解决她家的经济困难,所以就算他大了唐欣十岁,唐欣还是嫁给他了。可是其实那时候他是有老婆的,他为了唐欣硬是和老婆离了婚,老婆很快远走他乡,走之前把他们的五岁女儿留下来了。他们的女儿就是婉云。婉云对唐欣很不好,总是和她对着干,直到唐欣生下夏时,这个现象才好转。很奇怪,婉云很疼爱夏时,从小到大,这种爱甚至有些变态。婉云高中没读完就不读了,一直在外面和乱七八糟的人混。夏时那时候遇到你,他很喜欢和你一起玩,婉云很不高兴,变着法地欺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唐欣认识了你爸爸,这事开始没人知道,可是有一次新闻报出来,说景安度假村遇到山洪暴发,死者里就有你爸爸的名字,当时赶去的现场记者正好拍下了唐欣在你爸爸尸体前哭泣的场景,新闻说他们俩去那里偷情。”
阮小骨爸爸叹气,继续说:“夏时爸爸当时心脏病发就死了,而你妈妈受不了打击自杀了。你爸妈本来就是孤儿,他们这么一死,你就没有人养了,所以你妈妈在遗书里把你托付给我们。你因为受了太大的刺激,突然失忆了。唐欣就来找我,说要带你到另一个城市去生活,保证会对你好。说是夏时求的她。那时候我们家经济真的太不好了,唐欣接收了遗产之后就变得很富裕,我想你跟着她总好过跟我们吃苦。是我自私啊,是我自私,云朵,你恨叔叔吗?”阮小骨爸爸因为说了太多的话,泣不成声。
这些就是我一直想不起来的残酷真相。
这些就是所有人一直不愿让我知道的真相。
这些就是夏时多年来心事重重,性格大变的真相。
这些就是我每次梦里哭喊着的痛苦,内心百转千回的真相。
他们一下涌入我的脑袋里,把我的头快要撑爆。
“那婉云呢?唐欣为什么没有带婉云走?”我的牙齿在发抖,狠狠地咯咯地响声。
阮叔叔稍微抚平了一下情绪说:“夏局长死了之后,唐欣联系了婉云妈妈来领走婉云,可是没想到,婉云没有离开景坊,她一直留在那里,等你们回来。你这次回去,正好让她知道你们在哪里了。她才会找来的吧。这个孩子,我一直觉得她仇恨太多啊!”
许多年的纠葛仇恨,全盘托出的时候,竟然比我预计的还要让我感到恐怖和害怕。它正在一寸一寸地刺入我内心深处,把我封存的记忆一点点地刺裂开,让我在疼痛中去记忆那些被我一夕遗忘的痛苦。
原来真的很痛很痛,把想象中的疼痛上千倍万倍。
我悠悠地叹息,仿佛看到那个打着紫色雨伞的男人在雨中朝我走来。
是爸爸,他是我的爸爸。
那个一直在梦里对我哭泣的女人,那个管教我严厉教我用手拍死蟑螂的女人,她就是我可怜的母亲,她的目光悲凉,无时无刻不在和我诉说她的悲伤。我的伤似乎长了痂,一拨开,就如此地疼。
我感觉我脸上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一串地在脸上结成了水帘。
[3]唯有离开你
而夏时,此时的夏时,正在考场里,答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试卷。我和曲方歌坐在学校外面的茶餐厅,把糖一块一块地放进咖啡里。
曲方歌问:“你有什么打算?”他比我冷静,他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我想了许久,看着学校的方向,一字一句地说了三个字:“离开他。”
离开他,离开这个我喊了五年的哥哥,离开这个一直徘徊在我心里的人,离开这个会做鸡蛋水饺会讲冷笑话会陪我吹风的男孩子。
我记得韩真真在他父亲被判死刑的那天,对我说:“仇恨会让人看不到光明,会让人扭曲,也会让人痛苦。恨一个人,比爱一个人,还要难。”
所以,我选择不恨,因为,恨,是一个多么让自己痛苦的东西,它就像一把利器,深深地插入自己的内脏,把自己伤害得体无完肤。
我也知道,我和夏时,永远都会隔着一把尖利的刀,只要走近,必定被伤害得鲜血淋漓。
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他。永远地离开他。
我握着曲方歌的手,我说:“这一次,你一定要帮我。”
“你的请求,我什么时候拒绝过呢?”曲方歌无奈地笑。
[4]傅颜若会替我照顾夏时
我假装若无其事,照常上课,吃饭,睡觉,弹琴。
夏时填志愿的时候,我带曲方歌回家吃饭。我们故作亲昵,手挽手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唐欣又做了我最爱吃的西梅炒饭。我和曲方歌在客厅里为看《蜡笔小新》还是《樱桃小丸子》争执起来,夏时推开房门的时候,曲方歌和我正好都在抢遥控器,手握在一起,夏时的目光落在我们的手上,脸有一丝的阴沉。
吃饭的时候,我问夏时:“哥,你填哪里?”
“上海。”
“好地方啊,我明年也考那里去。”我笑嘻嘻地应。
“就你那文化成绩,考得到不?”曲方歌又拉我后腿。
“关你什么事啊,哼。”我在桌子下面踩曲方歌的脚。
唐欣微微地笑,说:“云朵真是好福气,找了曲方歌这么个好孩子。”
“妈你怎么把话倒过来说呢?是他好福气,找了我这个好孩子。”
夏时一句话都不说,一直扒着眼前的白饭。碎碎的短发遮住他眼底的寂寞和空洞。
我和夏时像是有默契一样,在婉云的婚礼之后,再也没有提那天发生的事和那天说的话,就好像那是一场幻觉,他依然是我哥,我依然是他妹妹。
可是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都知道对方已经和当初不一样了。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再也回不到从前,我们只能像两棵忧伤的树,了解彼此的心,却再也不会靠在一起了。
吃好饭我在厨房洗碗,夏时和曲方歌站在客厅里。厨房的窗户正好对着客厅的窗户,我看到夏时对曲方歌说:“云朵她怕冷,怕黑,怕一个人,夜里睡不好,你要经常陪着她,她喜欢赤脚走在家里,所以你要经常检查她的暖水袋是不是好的,她总是丢三落四,你要帮她把所有的东西摆放的位置都记好。她不吃芹菜不吃葱,爱吃鸡蛋和寿司。你的口袋里永远都要摆一颗棉花糖,在她要吃的时候随时可以拿给她……”
夏时像交代遗言一样对曲方歌说了一大堆的话,我多想像平时一样笑着喊:“夏时你别烦了,你真啰唆。”可是一张口,只有嘶哑的声音,眼泪哗哗哗地迎着吹入的风掉到水池里。心口像是被谁狠狠刺了一刀,疼痛欲裂。
这个晚来的夏天,突然开始狠狠地炎热起来,知了在树上大声地叫着,池塘里的青蛙总是呆在荷叶上,就像那些兜头而来的事情,让人应接不暇。
[5]谢谢你帮我照顾他
夏时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出乎所有人意料,他只是考上了上海一间很普通的理工科学校。而傅颜若,和夏时考了同一个城市。
这对在学校里公认的情侣,为他们的感情,又增添了一笔精彩,虽然是遗憾的,也是众人艳羡的。
我去找过傅颜若。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找傅颜若,她自从爸爸出事之后,退去了以前奢华的一切,搬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小区里,和妈妈住着两室一厅的房子。我到的时候,她妈妈外出买菜,她们把韩真真也接到家里来住了。她们三个人,过得很开心。
我在傅颜若和韩真真的脸上都看到了一种释然的表情,曾经的倨傲冷漠都只是厚重的面具,一旦拿下来,一眼就能望见她们的纯真。当事情都公开了,各自都找到了心灵的归属,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的幸福吧。比任何的锦衣玉食,高床软枕都来得珍贵。
我说:“拜托你,好好的对夏时。这辈子,我不可能和他在一起,希望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
傅颜若坐在房间的床上,头发披散在腰间,雪纺的白色长裙落在白皙的大腿上,她睁着明亮的眼睛微微地笑着说:“我答应你,我会好好照顾他,其实这一次我要谢谢你,如果不是婉云想要报复你,我也没有机会卸下我心里这么多年的困扰和包袱。”聪明的她,应该明白了这件事的曲折。
“把对我感谢转换成对夏时加倍的好吧。我也谢谢你。”我握住傅颜若的手,第一次真心的和她道谢,我知道这么多年,她虽然一直喜欢曲方歌,可是她对夏时的感情并不比当初喜欢曲方歌少,我相信夏时有傅颜若在她身边,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他,陪伴他,至少在他难过的时候,他不会孤独。
[6]我们就这样,长大了
夏时走的那天我没有去送他,我帮他整理了衣角,帮他刮好了胡子,他碎碎的刘海遮住眼睛的光,深邃的轮廓勾勒出他冷峻的脸庞。洗干净的衬衫还有洗衣粉的清凉味道。是我熟悉的气味。
我把头放在他的肩膀,抱着他的脖子说:“哥,再见。”把头深深地埋在他的脖颈,像要记住他的味道。他深深地拥抱我。时光很短,心却连得很长。长到一个世纪,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他在我的额头前落下一个吻,有一些湿冷,他说:“云朵,这么多年,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再让你受伤害,可是我始终无法做到,现在我要带着这份遗憾走了,希望曲方歌能帮我做到。”
他走了之后,我扣上门,缓缓地蹲在门口,客厅里的菊花开始凋谢花瓣,侧面照进来的金光让人一下子就遥想起曾经的旧时光,我低低地抽搐,最后大声地哭泣。我知道,我和夏时,就像我们天天抬头看的云那样,思念着彼此,却再也触碰不到了。
我的十七岁就这样遥遥地过去了,夏时送给我十七岁的字条上写:已经不知道要送什么给你了,如果想要什么,记得打电话告诉我。无论多难,我都会帮你实现。
那一天下了蒙蒙细雨,我站在开走的火车站抱着曲方歌放声大哭,谁都不知道我内心的痛,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悲伤和绝望,曲方歌轻轻地抱着我说:“云朵,以后我会对你好的,好吗?”
我想起以前在景坊的时候,婉云常常欺负我,每一次夏时都为了我和婉云撕破脸。
婉云在她父亲没死之前,一直和夏时居住,后来父亲过世,她才回到她妈妈那里。她一直都不喜欢我,可是夏时总是告诉我,无论姐姐怎么欺负你,你都别怕,因为我会帮你的。
夏时离开的这一年,我想起了很多事,我想起我手上的伤疤是第一次遇到夏时的时候劣质烟花炸的,那一年下了很大的雪,他们在楼下放烟花,夏时给了我一根坏的,烟花炸起来的时候,整根都爆炸在我身上,我的衣服被烧坏了,手也烧黑了,我对着夏时哭喊着:“你这个坏蛋,我恨你一辈子。”手好了之后,留下了一道难看的伤疤。从那天开始,夏时就满怀愧疚在我身边照顾我。
我每想起一件和夏时有关的小时候的事,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落下来,怎么擦也擦不完。
我的教室从楼下搬到了顶楼,以前夏时他们生活过的楼层,我每天晚自习都很晚走,趴在窗台上看所有的灯亮起灭掉,曲方歌给我带很多好吃的,像是要把我养成一个胖子。蒋幂发奋地读书,莫白又回来了。他们像两个普通朋友,偶尔交集。
蒋幂和我说,人生如戏,散场了,就不要再继续沉溺在戏的精彩里无法自拔。
我觉得我们都是天生的好演员,不动声色地掩盖得那么完美,可是彼此都能从各自的眼眸中看到沧桑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