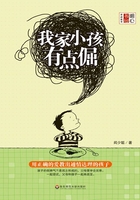那是一个森林,那里有密密麻麻的树木,但是那里的树木都没有叶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刚从埃诺家出来,我就听见了我的米拉米斯在痛苦地嘶叫,它那响亮、凄惨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我几乎被吓得停止呼吸了。可是米拉米斯还在长嘶,它好像在呼喊:“——米欧,亲爱的米欧,快来救救我!”
“丘姆—丘姆,他们把米拉米斯怎么样了?”我高声地喊叫着,“你快点听一听,听见了吗?他们把米拉米斯怎么样了?”我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了。
“小声点,别说话,”丘姆—丘姆说,“他们捉住了它……肯定是侦探……”
“我的米拉米斯被侦探捉住了?”我喊叫着,我才顾不得被谁听到呢。
“你一定不要再说话,”丘姆—丘姆小声说,“不然我们也会被他们给捉住的,那一切都完了。”
丘姆—丘姆的话我一点儿也听不进去。米拉米斯,我的好马!他们正在夺走我最爱的好马!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最善解人意的马了,我舍不得它。
我不时地听见它在嘶叫,我觉得它好像在责怪我不去救它。没错,它就是这样呼叫的——米欧,你怎么不来救救我!
“走,快点走,”丘姆—丘姆说,“我们一定要去看看他们究竟把米拉米斯怎么样了。”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攀上峭壁。我们又爬又攀,我的手指被锋利的峭壁刺破了,我全然没有感觉,因为此刻我的心里只有米拉米斯,我只为米拉米斯担心。
我们爬上悬崖,看见米拉米斯高高地站在一块峭壁上,它在黑暗中显得特别的白,这时候我更觉得我的米拉米斯是这个世界上最白、最漂亮的马了!
我看到它疯狂地嘶叫着,不时地把前腿立起来,试图跑掉。但是怎么可能呢!在它的周围有五个密探紧紧地围住它,其中有两个人拉着它的嚼子。那几个穿着黑衣服的侦探面目狰狞,他们用沙哑、可怕的声音交谈着。可怜的米拉米斯一定是被他们吓坏了,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丘姆—丘姆和我紧缩着身子,静静地躲在一块峭壁的后边,听着他们讲话。
“我们最好把这匹马弄到黑色的船上去,然后运过死亡之湖。”一个侦探说。
“对,我们应该直接把它运过死亡之湖,交给骑士卡托处置。”另一个侦探说。
这时候我真想对着他们喊叫,谁也不许动我的马,但是我并没有那样做,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也被侦探捉去,就没有人与骑士卡托决一死战!啊,为什么偏偏是我要与骑士卡托决一死战呢?我躲在峭壁后边后悔极了。如果乖乖地待在我父王身边就好了,那里不会有人夺走我心爱的马!我听见被魔化的鸟儿仍旧在湖的上空叫个不停,但是此时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我一点儿也顾不得它们了。我只想保住我那长着金色马鬃的米拉米斯,它们是否继续被魔化只得听天由命了。
“一定有人越过了边界,”这时候听见一个侦探在说,“那个人一定是骑着这匹白马驹来的,敌人肯定就隐藏在我们心脏里。”
“不错,如果敌人隐藏在我们心脏里,”另一个侦探接着说,“那我们想要捉到他就十分容易了,骑士卡托想要摧残他、消灭他也就比较容易了。”
他们的对话,让我听得浑身直打战。因为我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越过边界的敌人,我就是骑士卡托想要摧残、要消灭的人,这时候我对于到这里来更加后悔了。我非常想念我的父王,我想念留在他身边度过的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我不知道此刻父王是否也在想念着我,是否为我担心。我多么希望他能出现在这里,能帮助帮助我,哪怕是我能够跟他说一会儿话也好啊。那时候我可能就会对他说——我知道,你希望我与骑士卡托决一死战,但是好心的父王,你就饶了我吧。我不想失去我的米拉米斯,帮助我找回米拉米斯吧,带我们离开这里,离开这个鬼地方!离开得远远的,让这个地方在记忆中永远消失。你知道,我过去从来没有自己的马,我非常喜欢米拉米斯。你也知道,我过去没有父亲,我也非常地想念你。如果骑士卡托把我捉住了,我就永远也无法回到你的身边了。把我救出去吧!亲爱的父王!
我一刻也不愿意再待在这里了,我想待在你身边,每天陪着你,和你散步聊天。我想与米拉米斯还有丘姆—丘姆一起重新回到绿色草地岛去。
在我躲在峭壁后面悄悄地想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了我父王的声音。这也许只是我的幻觉吧,但是我仍然觉得我好像听到了他的声音。
他在喊“米欧,我的米欧”。虽然没有再说别的话,但是我还是明白了父王的意思,他希望我勇敢起来去和骑士卡托决一死战,别躲在那里像小孩子似的哭呀叫呀,即使我失去了我心爱的米拉米斯也不该这个样子,谁都知道我是个骑士,我应该勇敢坚强起来,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只知道在玫瑰园里搭草房子、在绿色草地岛的山坡上闲逛或吹笛子的小孩子米欧了。
我是一名骑士,一名优秀的勇敢的骑士,一名绝对不同于卡托的骑士。骑士一定要勇敢,那首先就不能哭。
想着我身上的责任,尽管当我看见侦探们把米拉米斯强行拉到湖边,又强行赶上一条黑色的大船的时候我没有再哭。我真的没有哭,尽管米拉米斯不停地嘶叫着,好像他们在用鞭子抽打它。当侦探们坐在船桨旁边,我听到从黑暗中传来他们摇橹的声音时,我也没有哭。
我听见船桨的声音越来越小了,船消失在远方之前,我最后一次听到从湖的远处传来的米拉米斯绝望的嘶叫声——但是我还是没有哭,因为谁都知道我是一名骑士,“我是一名勇敢的骑士。”我也这样对自己说。
我没哭?其实我哭了,我确确实实地哭了。我静静地靠在峭壁后边,前额对着坚硬的土地,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承认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哭过。一名优秀的骑士得讲真话,我确实是哭了。为了米拉米斯,我哭呀,哭呀,我一想起它那双忠诚的眼睛就泪流不止。我还记得那位织布的老太太说过,几百匹白马为了被夺走的小马驹眼里哭出了血。可能我为米拉米斯眼里也哭出血来了,不过我不确切地知道,因为天太黑,我看不清楚。我的长着金色马鬃的米拉米斯就这样被他们带走了!它不在我的身边了,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它了。
这时候丘姆—丘姆弯下身来,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安慰我。
“别再哭了,米欧,”他说,“我们一定要到宝剑制造人那里去。
你需要一把锋利的宝剑,有了宝剑你就可以与骑士卡托决斗了。”
我心里真委屈,我想我的米拉米斯,但是我还是咽了下去,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咽下去了,然后我们去找那个宝剑制造人。
埃诺曾经告诉我们,要穿过死亡森林去才能找到宝剑制造人,但是连死亡森林在哪儿,我们都还不知道。
“在天亮以前,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宝剑制造人,”我对丘姆—丘姆说,“黑暗掩护我们,黑暗中侦探看不见,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夜里穿过死亡森林,找到宝剑制造人。”
我们又匆匆地爬回埃诺房子旁边的峭壁,房子静悄悄地坐落在黑暗中,我们没有再听见房子里有人呻吟。
我们在黑夜中不停地赶路,最后我们终于很幸运地来到了死亡森林。这片森林里既没有风声,也没有树叶沙沙地作响,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能沙沙作响的绿色嫩树叶。那里只有枯死的树干,树干上长着的是黑色的、疤疤拉拉的死树枝,连一片叶子也没有。
“我们已经进入了死亡森林之中。”当我们走在树木中间的时候丘姆—丘姆说。
“对,我们大概进来了,”我说,“不过我不相信我们还能走出去。”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会使人迷路的森林,这样的森林只有人们偶尔在梦中才能见到。人们在里边走呀走呀,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永远走不出去。
我们穿过死亡森林的时候,我和丘姆—丘姆一直手挽着手,因为我们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茫然,密密麻麻的枯树使得我们几乎无法向前进。
“如果树长得不这么密那该有多么好啊,”丘姆—丘姆说,“如果天不这么黑,我们不这么渺小,不这么孤单那该有多么好啊!”
我们走呀走呀,有时候我们能听到远方有声音,那肯定是侦探们弄出的声音。埃诺大概说得对,到处都是骑士卡托的侦探,整个死亡森林里都布满了他的侦探。当我们听到他们在远处的树木间活动的时候,我和丘姆—丘姆就停下脚步,不敢再往前走,我们静静地站着,连大气儿也不敢出。
等他们朝别处走去时,我和丘姆—丘姆又继续上路,我们走呀走呀,不知道走了多少路,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死亡森林的夜真够长的,”丘姆—丘姆说,“但是我想通向宝剑制造人的山洞的路肯定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