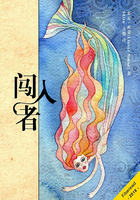颠不刺地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光撩乱口难言,灵魂儿飞在半天。
急忙将眼光移开,一首《上马娇》又跳动在眼前;
这的是兜率官,休猜做了离恨天。呀!谁想着寺里遇神仙!我见她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
这两阙曲牌,韦惜玉原先并不喜欢。从前读《西厢记》读到这里,总有一种不平、不真之感涌上心头。哼,鼓词、传奇、小说、残曲,动不动说女人“杨花水性”!仿佛只有男人才是钢脾铁性,玉洁冰清。可那张君瑞,身为堂堂解元,刚丹瞥见了崔家小姐一眼,就眼也花,心也乱,连灵魂儿都“飞在半天”实在是糖汁豆腐性,连女人也不如!不过,就算莺莺小姐真的是生着罕见的“可喜庞儿”。可人家连眼梢也没向你瞟一瞟,何至于那觳丢魂入魔似地神魂迷乱,将肉体凡身的相府千金,当作供奉莲台的“神仙”呢?没道理,实在太没道理。壬实甫的生花妙笔,也编造得太离谱儿啦!
伸出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灵巧地将书页翻了过去。书页尚未落稳,她又倏地翻了回来。
“眼光撩乱口难言,灵魂儿飞上半天!”三天来,自己眼前闪动的,心里翻腾的,不都是那位“神仙”吗?哪有一刹儿“灵魂儿”不飞在“半天”上呢?
讨人厌的杨月楼!我跟你无怨无仇,凭什么非跟人过不去从此刻起,要是再想到你一次,我就不是韦家的好姑娘!
呸!你个耍笔杆的壬实甫,早年写下这混书,候到今天专来挖苦你韦姑娘。你好没道理。去你的《西厢记》,没安好心肠!
两行热泪簌簌地滚下她丰腴地双颊。猛地站起身,狠狠将书本往桌上一摔,一头栽到床上,面向枕头,极力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
“壬姐,你说说,阿宝这孩子到底是咋啦?这两天象丢了魂儿,茶不思,饭不想。满脸挂冷霜,象是哪个惹恼了她。说她病了吧,又不象,体不燥,脑不热,连声咳嗽也听不见。离经期也还有十多天,怎么会成这个样子?问起来,没嘴葫芦似地,十句九不应。问急了,朝着你撤嘴瞪眼要小孩子脾气。你看,方才她哪里象吃饭,吞苦药不是?唉!真不知该咋办才好哟!”
吃过中饭,女儿放下饭碗刚上楼,韦王氏就焦急地向奶妈倾诟心中的忧虑。说着,说着,鼻子一酸,流下泪来。她从腋下抽出麻纱手帕,揩乾眼泪,两眼望着奶妈,祈求般地说道:“王姐,阿宝是你一手把她带大的。她的心境脾性,你该比我这做娘的还透彻。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壬妈显得有些犹豫,苦笑着摇摇头,答道;“太太说的是--俺也看着小姐变啦。”
“你说,这是咋回事哟”
“依俺看,伯是有了心事……”
“咳,刚刚十七岁的孩子,整天藏在绣楼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来的心事?当初我都二十岁啦,出嫁时象卖一袋稻谷,糊里糊涂被背上花轿,抬到了韦家,睡了一夜觉,才看清丈夫是啥模样。这孩子怎么会呢?”
“但愿小姐不是--”奶妈欲言又止。
“兴许就是。”韦王氏一时没了主意。“王姐,我没福,嫁给韦家十八、九年,没给人家生下个儿子。落得……这姑娘,可是我的命根子。王姐,你可得替我出出主意哟!”
看到女主人不住地揩眼泪,奶妈两眼发热,缓缓劝道:“太太,莫着急。不是大不了的事,法子总是有的。”
韦王氏指指方桌对面的靠背椅:“王姐坐下说话。”她把面前的盖碗,双手送到奶妈面前。“喝杯茶,咱姐俩好好唠唠。好王姐嘹,你可得跟我掏心里话哟。”
王妈慌忙将茶杯捧回到主人面前。长吁一声,坐下来,字斟句酌地答道:“太太,话既然说到这里,俺要是不掏心肺里的话,对不住太太这些年对俺的倚信。小姐吃过俺的奶水,在俺心里头跟亲生女儿一样亲。俺留心了,小姐这两天的变化,实在是太大,太让人担心受怕。”她叮着女主人问道:“太太,小姐没看杨月楼时,是这个样子?”
“不呢,原先好好的,去戏场的路上,她还低声哼啥曲子呢。这么说,她的心病是出在看戏上?”
“是的,太太。小姐的反常,就反在这三天夜戏上。”
“会吗?”
“错不了,太太。”
韦壬氏连连摇头:“头两晚上,这孩子又哭又!f的,是有些两样。自打昨天晚上,没见她拍手跺脚,淌泪!喊,真有个大家闺秀的样子,怎么会--”
“太太,小姐是外面安祥,内里张惶:当她听到王佐说超陆文龙的父母惨死,文龙被掳,并作了金贼义子那功夫,眼泪湿得手帕儿只莉下四个干角儿。”
“咦,我怎么没看到?”
“兴许太太只顾看戏,没留心。”王妈俯身向前,声音压得很低,“今天上午,小姐还哭过呢。”
“咳?”
“太太,方才没见小姐两只眼圈儿,殷红殷红的吗?”
“怪不得,她光低着头吃饭,不肯抬头呢。”
韦王氏如梦方醒,她觉得女儿分睨已经瘦了。焦急地问道:鼻王姐,象这样下去,孩子的身子要糟塌了。你看,是不是先给她做点爱吃的哚?我叫范五去买杏仁、莲子、葡萄干、青红丝什么的,晚饭先熬一锅她最喜欢的八宝饭,再炸几个蜜汁鸡蛋--先给她补补身子要紧。”
王妈摇头道:“太太,治病要打根上治,眼下,怕不是顺口的东西,能治得了小姐的厌饭病。”
“那--该怎么办哪?”
“太太,怕是只能这样啦!”
“王姐,你快说!”
王妈站起来,口气象主人吩咐仆人。“第一要紧的莫让小蛆再去看杨月楼。”
“说的是,我也这么想!”
“小姐看的那些书,里面怕也少不了分心乱神的风流邪事!
“唛?你是说,她的病根还出在那些坏书上”
“太太,俺是睁眼瞎,不知啥是好书,啥是坏书。可俺常常看到,小姐念起书来,一会儿低眉顺眼,一会儿两眼放光,有时直愣愣的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窗外,象是天上要飞下只金凤凰。可俺瞅瞅天上,连只黑老鸹也不见。俺估摸着,准是书里头那些邪门子事儿,拘住了她的心。你想,这样天长日久下去,用不着到洋场舞厅游逛,什么稀奇古怪光景,学不到心里去?太太,不知俺说的对不对”
韦王氏连连“哦”着,不住点头。壬妈的一席话,象吹散她心头乌云的一阵轻风,使她看见了一角蓝蓝的天空。对呀!因为看书,女儿还跟她呕过气呢……
有一回,她定好了座儿,要女儿陪她去看戏。不料,女儿一口回绝。当时她拍着女儿的肩头,细声细气地相劝:“阿宝,大长长的夜,闷在家里熬个啥辰光嗦?哪跟上看两出戏,热闹,开心,又长见识。”
不料,女儿竟答道:“要去,你跟王妈去,我要留在家里看书。”
“咳,几本闲书,有啥番头?就算讲的是故事,论的是理儿,直说白道地也没啥意思。戏台上,可是原模原样地做给你看嘹。”
“才不是呢--我的那些宝书,顶得上一万出好戏!”
韦王氐一直觉得,女儿看的那些书,大都是些消磨时光的闲书。不料,女儿竟说是“宝书”她不由一怔。自己的父亲是一位读书破万卷的老儒生。不知为啥,科运不佳,虽然县试轻易地考中了秀才。空有满腹经纶,乡试却屡屡败北。以致穷困潦倒,做了大半辈子私塾先生。一领蓝衫,整整穿了一生。老秀才为了让女儿懂事明礼,教书之暇,教着女儿读书识字,“开开眼”。但只教会了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便不肯再往前教。“诗书文章,不是女儿家的功课,针黹刺绣,才是闺阁秀女的正功!”老秀才不主张女孩子多读书,犟得牛拉不动。这样,她的“学问”也就始终停留在开蒙第一年的水平上。等到自己做了母亲,她谨遵家训,把珍藏的家传四本书找出来,一一教给了女儿。四本书被女儿翻来复去,读得倒背如流,却仍不肯罢休,吵着闹着,要读《四书》、《五经》。莫说《四书》、《五经》,韦王氏教不了,即使能教,老子的教诲,她也不愿违背。“你外公常说,念完那四本书”尽够女孩儿家使用。省出心思,学好女人活路,尔后到了婆家,妈妈也不落个养女不教,的笑骂。”但是,作母亲的苦口婆心,外公的大道理,都不能使女儿就范。“妈妈,知书为着明理。不成,书念的越多,人变得越糊涂,越给当妈妈的招惹乱子?人家宋代的李清照,比丈夫赵明诚的学问强百倍,赵明诚服贴得五体投地,满天下的人都尊她是才女呢!阿宝,你要相信外公的话。外公是有学问的老秀才,断事哪会错!”哼,我才不相信呢,倘使天底下的理儿都让老秀才相公看准了去,还耍举人、进士、翰林、状元做啥?”
女儿撒娇地翻开了糊饼儿,做妈妈的哭笑不得。仔细想想,多念两本书,多知道些古人今事,作兴也没多少坏处。当初,要不是害怕老父的威严,也会祈求他给自己开讲《四书》、《五经》、《千家诗》的。想到这里,韦王氏赌气似地答道:“要念自已念去,我可教不了!”
“不要谁教,我自己能念!”女儿得意地歪着头,一面伸出右手:“妈妈,给钱。我让范五伯买书去。”韦王氏从钱柜里取出二两“元丝”交给女儿。“呶,拿去。给归给,可只准买正经书!”嘴上是这么说,究竟什么书“正经”什么书“不正经”王氏自己也闹不清。
范五先买回的是一套《四书》和一本(《千家诗》。韦王氏看了,知道这是“正经书”。心里很欢喜。渐渐地,阿宝床前的长几上,摆上了《牡丹亭》、《西厢记》、《花间词》和《漱玉词》。后来,又出现了一部石印的《金玉缘》和许多弹词小说。哼!又是“花同秒,又是“牡丹”!又是“花”呀,“玉”呀的。不用同,八成不是正经书。韦主氏心里直犯嘀咕。可是,女儿对她的委婉质问,竟是将书一本本地搡到她面前,翻开来,指点着大声嚷嚷起来。“你自己看,不是好文章,就是好诗词,那点儿不正经?”她虽然看得懂书里大部分的字,却弄不甚透彻,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看看上面,都有着排列整齐的字行,分明象是诗词,看来,女儿没有欺骗自己。《诗经》唐诗、宋词不都是诗词吗?可见,面前的书,也都是好书。心上的疙瘩解开了。嘴上却说道:“好好好!我不懂。是正经书,你就念。也别管累坏身子,伤着眼!”娘疼女儿,不由得把阻拦变成了劝解。“妈妈瞎操心--看书又不是摇船、割稻谷,哪基就碍着身子,眼睛啦!”韦阿宝极力掩藏着心中的喜悦装傻蛋。
女儿一夭到晚,哼哼呀呀,抱着书本不松手。虽然她的身子和眼睛,没看出受到什么损伤。可是,她的心绪却在一天天地变。半年前,不知念了哪本歪书,一天学屋门没进的姑娘家,却独出心裁,给自己取了个学名--借玉。从此把所有的书上,都工整地写上“借玉珍藏”四个字,还正正经经地告知仆人范五和奶妈王氏:“往后别再喊我的乳名。借玉才是我的名号!”近几月来,又不知中了哪门子邪,不喊“吃饭”不下楼,一天到晚跟书粘在一起。看着,看着,格格大笑起来;眨眼的工夫,却又眼泪鼻涕地哭个没完。有时喊她吃饭,都喊不应。她担心女儿患上了什么病,便缠着盘问底细。谁知,问得缓,女儿低头看书不理睬!问急了,惹得女儿皱眉斜眼:“哎呀,打破砂锅纹(问)到底--妈妈好哕嗦!看古书掉两滴眼泪,谁不这样?有啥好奇的!你在戏台底下,不也常常哭天抹泪吗?”
这话,使她无法回答。心里却暗暗为女儿担忧。总想变着法儿让她分分心,免得尽在没来由的古书上耗精神。可是,她始终也没找到个有效的法子,让女儿跟书本疏远一些……
现在,听王妈说蓟女儿迷恋书籍的情景,深深触动了她的心事。抬起头,向王妈问道:“王姐,你看,是不是,不能再让她看那些坏书啦?”
“俺也是这么想呢,太太。”
韦王氏站起来,向楼上指一指:“走,我去把她的书都收起来,你帮我抱下来。”
“是,太太。”
王妈扶着韦王氏往楼上走。刚走了几步,韦王氏又停下来阊道”!姐,那丫头会不会不让呢?”
“八成。”
“你可得帮我好好劝劝她呀。”
“太太,尽管放心。”
韦王氏又向王妈耳语道:“壬姐,等会儿我喊你--我先自己上去。”
韦壬氏来到楼上,坐蓟床前的方杌子上,跟手擎书本、歪在床上的韦惜玉,没话找话地扯了阵子家常。然后,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踱到长几前,摸挲着一摞书本,轻声问道:“阿宝,这些书,都看完了?”
“嗯。”惜五歪着头,没有动。
“还看不看啦?”
“不看了。”
“那……妈给你收进樟木箱子里吧?省得放在外头,落灰招虫的。”
“高兴,你就收走呗。”
“真的?”
“哪个有闲功夫开玩笑!”
女儿出乎意料地回答,反倒使书壬氏犹豫起来。她嗫嚅地说道:“也好,我先收起来。二天要看,我再给你。”
“放心吧,二天我也不看啦。”
“好,那好。壬姐,”韦王氏向楼梯口高喊,快来帮帮我。”
王妈上楼来,抱上桌上的一摞书往下走。惜玉招手喊住了!”回身将枕边的一册《石头记》,也塞进了她的怀里。
“阿宝,一本也不留?”韦壬氏被女儿突如其来的慷慨弄糊豫了。
“一本不留!”
“那……闲来做什么?”
“你不是老嫌我,闲来捧书本,不象个闺阀女儿家吗?”警过来的眼光似真又似假,“打从今天起,韦惜玉改邪归正,做个有板有眼的女儿家”!”
移韦王氏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
“妈妈,别愣着。快找些缎料、花样子来,我要给你跟奶妈锈枕头!”
“那可是好,那可是好哟!”
韦王氏踞动着小脚,快步下楼。一下楼梯,便向正在整理书本的王妈同道:“王姐,这是咋回事?越发反常了!”
“就是呢,真教人想不彻。静芏妈指指刚抱下来的一大堆书,“这可是小姐的心肝命根子。要是在往常日,拿走一本,准得吵个火燎烟呛。有一回,抹桌子时,俺不小心把一本《牡丹亭》,还是《芍药亭》的,碰到了地下,痛得她拿眼瞪着俺,抱在怀里捷擎了好一阵子。”
“莫非她在使气?”
“不象……”王妈心里犯嘀咕,嘴上却宽慰遭,“兴许年轻人心眼透灵,明白过来了。”
“菩萨保佑!”韦王氏为女儿的“明白过来”长吁一口气。”
“王姐,先别管那些书,我找出缎料、花样子来,赶快送上去,她一旦绣开头,就顾不得想别的了。”
“正是呢,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