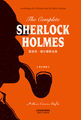衔冤负屈心千结,无由告金阀。
--《鸣风记》
从昨天傍晚就下起的秋雨,一直没有住点儿。一会儿淅淅沥沥,一会儿哗哗啦啦。黑沉沉的天幕,仿佛变成了一面竹筛子,非把天上的水气,全都漏完放净不可。
一场秋雨一场寒。秋风挟着秋雨,秋雨裹着秋寒。骤然之间,气温下降了许多。昨天还是苍蝇嗡嗡,蚊虫哼哼的单身牢房,此刻竞成了冰冷的水牢。
杨月楼蜷缩在草苫上,仍觉阵阵寒气袭人。被捕时就穿着的杭纺绸衫裤,被汗渍、血污弄得潮腻不堪,更增加了几分寒冷。被夹棍夹伤的下肢,棍棒打伤的脚踝,虽然红伤逐渐平复,酸痛麻木感,却一阵比一阵剧烈。
自从“招供”以来,他颈上的大铁枷被拿掉了,但手上仍带着那副红毛巡捕给戴上的洋铐。洋铐闪着白色的寒光,紧紧缠在手腕上。双腕象绕上了两条白花蛇,冰凉冰凉。
大概妻子也仍然穿着被捕时的衣衫。这样的倒霉天气,连自己都受不了,她那单薄的身子,只怕更要冻坏了!王妈穿得也很单薄……
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杨老板。”见杨月楼瑟瑟发抖,狱卒单二近前问道!“加件衣裳吧?这样的鬼天气,不把人冻出病来才怪嚓。“
“衣服?单爷,我哪有衣服?”
“嗨!曾老板来看你的时候,不是送来了夹衣吗?”
“噢,我倒忘了。”
“咳,冻病了不是玩的。大牢里,本来就是让健康人生病的地方。病倒了没人疼惜事小,不知有多少人,没等冤枉官司打出个眉目,就把小命扔在了这里。我见的多啦!”扭着胡子稍儿,单二发起了感慨。
“唉,不换也罢。”杨月楼缩成了一团。“反正换上了还得脱下来一-我约摸着该换囚衣啦!”
“咳,哪里想得那么远!暖和一会儿是一会儿。按说,案子一审结,就要换上囚衣等待服刑。不知为什么,至今没给你换。”
“单爷,您就给我个实底儿,半个多月啦,为什么不审不问呢?”
“说的是呢。这位叶大老爷就是格路!”说到这里,单二急忙扭头望着窗外檐下的雨柱。“看这天:成心要把人沤死。杨老板,您等着。我去给你找衣服去。”
不一会儿单狱卒从外面返回来,带回一件夹衣,并亲手给杨月楼披在身上。杨月楼戴着手铐,不能穿袖子,洋铐的钥匙又不在狱卒手中。只得将夹衣披在身上。结上颈下的一颗纽扣,以防止衣服滑落。
趁狱卒给他披衣服,杨月楼低声问道:“单爷,我求你打听我妻子的情形,您老人家怎么迟迟不开“呢?你一定是不愿说,噜!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她的脾气太暴烈,我真担心她……”
“杨老板,你莫胡猜乱想。你太太又没象你似的,受那么歹毒的刑罚,怎么会呢?是我没打昕到实信儿。原先她被关在女牢十三号,后来转走了,说是去个更舒服的地方。可谁也不知去了哪里。依我看,不管她去了哪里,人,至定是平安的。你多挂她也无益,还是多当心自己的身体为是。”
“这叶廷春搞的什么鬼名堂呢?”杨月楼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发问,自然也得不到单二的回答。过了半晌,他忽然怒喊道:“哼,冤枉了男人,还不放过人家的妻子!总有一天我要越衙告他的!”
忽然响起一阵闷雷。杨月楼后面的话,单二并没听到。
正在这时,狱外传来了呼喊:“带五监四十七号杨月楼,他韵妹妹探监!”
杨月楼一听,倏地站了起来:“单爷,一定是我妻子韦惜玉--我并没有妹妹。”
“准成是。”单二兴奋地站了起来。“杨老板,我说的对吧?刚才咱们还在这儿瞎猜呢。原来你太太已经回了家!”
“这大的雨,她怎么来得了啊?唉!”杨月楼痛惜地发出一声长叹。
“看你说的!今天是九月二十五。逢五,探监的日子。她要是今天不来呀,还要眼巴巴再等十天。走,快去会会就放心了。”
探监室里,木栅栏后面,站着一位细高挑丹风眼的妙龄女部。杨月楼一见,不由一愣。他并不认识这个女人。心想,一定是狱卒搞错了,将别人的家眷错当成了自己的妹妹,他正在犹疑,女郎朝他淡淡一笑,开口说道:“哥哥,我看你来啦。”
女郎抬抬手,让他站到对面的木栏前。杨月楼刚要说,“小姐你弄错了,我不是你哥哥”对方紧接着又说道:“哥哥,曾历海大哥和丁少奎大哥让我向你问好。”她举一举手中的点心包。“还让我带来了你最爱吃的蜜三刀和切糕呢。”
杨月楼不知道面前这位打扮入时的小姐是什么人,但从她的话断定,无疑是看望自己的。因为她不仅知道曾、丁两位是自己的至交,连自己爱吃的东西也弄明白了。他回头看一眼正在一旁监视的单二。单二正面朝窗外,仰头观察天上的灰云。为了不露破绽,他急忙含糊应道:“噢,我很好,请告诉曾大哥和丁大哥,不要挂念我。”他摇动两下双肩,接着说道,“看,我身上也很轻爽啦。不知我母亲的身体如何?”
“母亲的身体,跟从前一样好,照样吃饭、睡觉。”她回答得很爽快,完全是“妹妹”的口气。“她老人家就是记挂着你,怕你不爱惜身子。她要我告诉你,不论饭菜多么难咽,都要吃饱。天冷了,多穿点衣服,当心受凉害病。她老人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千万大意不得。哥哥,你听清楚了吧?”见“哥哥”频频点头,她继续说道:“曾大哥还说,三庆班闲在这里唱不成戏,几十“子人要吃饭,想让他们先回北京,顺便陪伴母亲回去,免得她老人家在这里过分操心。这里的事儿,由他和丁大哥、小程一起,留下照看你。问你,这样做妥不妥当?”
“也只好这样,”杨月楼沉吟了一会儿,又问:“我岳母呢?他老人家好吗?”
“妹妹”答道:“好,好!她老人家身子骨挺壮实。她要跟我一块来看你,因为下雨,路不好走,我劝她好了天再来。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听着“妹妹”连串的劝慰,杨月楼不住地在心里品味。他知道,母亲“照样吃饭睡觉”以及岳母“身子很壮”的话,不过是对方给他的一剂定心丸,是绝不可能的事。可是,这个陌生的女郎到底是谁?她冒雨来此干啥?难道就是为了给自己一番亲切的劝慰吗?心里纳阎,当着狱卒的面,却不便直问。正在为难,“妹妹”又开口了:“哥哥,嫂子也叫我问你好。她说……”她略微停顿了一下,“她不久就会释放回家……”
杨月楼终于说出了满腹狐疑:“您怎么知道的?”
“昨天,我去看望过嫂子。是她亲“对我说的。”
“真的?”杨月楼目光灼灼,脱“喊道,“多谢您啦--妹妹!你知道奶妈的情况吗!”
“她的身子比谁都好。”她没有正面回答。
“谢谢你啦!”
“哥哥说到哪里去啦,自家兄妹何必见外!现在,全上海滩的好人,都在为哥哥操心呢。她一面说着,朝手里的点包儿,使了个眼色。“哥哥有什么话就快说,大概时间快到了。”
“请您,”杨月楼恢复了平静,用一副对外人说话的“吻。“请您告诉母亲、岳母、师兄及三庆班的弟兄们,说我杨月楼一定遵照他们的嘱咐,爱惜身子……”
杨月楼忽然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沈月春见状,急忙把头扭到一边。然后说了一声:“哥哥多保重,再见。”说罢,她把点心交给单二,低着头匆匆去了。
回到牢房以后,单二并没象往常那样,开包仔细检查,随手便把点心给了杨月楼,然后笑眯眯地问道:“杨老板,你啥时候认了这么个亲妹子!”
“……”杨月楼不知如何作答。
“哈……”单二仰头笑了起来,“杨老板,你知道这俊妮儿是谁?”
“我也不认得。”知道瞒不过,杨月楼只得说实话。
“上海滩不认识她的人不多。她是广和书场的红角儿,唱评弹的沈月春!”
“原来是她!我听说过”
“不是她,是谁?这几年咱也断不了去听两场呢。那唱腔儿,韵调儿,吐字儿,嗨,别提多么动听啦!”
杨月楼轻轻“噢”了一声,半响无语。
单二又说道:“你那个妹妹一进探监室,我就觉得挺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沈老板!嚯,今天是名角儿看名角儿,名角儿成了兄妹,真有意思!”说着,单二笑了起来。“杨老板,你这个戏台上专会做戏的名角儿,怎么在戏台下面演起戏来那么蹩脚呢?今天,要不是我值班,换了别人,当场不戳穿你们这出口兄妹疑案”才怪呢!杨老板,你别心惊。眼下岂止是一个沈月春,上海滩给您抱不平的人多着哪。我单二要是不睁只眼,闭只眼,岂不成了不讲义气的畜生!”
“单爷言重了。”杨月楼感动地抱拳施礼。“今天,多亏单爷包涵,不然……”
“唁,您就别客气啦!”单二打断了杨月楼的话,“人活在世界上,谁敢说有一天不落到难处?人家有难,多给方便;等到自家有难的时候,兴许才有人给方便。这H报还一报。您说是吧,杨老板!”
“单爷说的是,说的是。”杨月楼连声应诺。
当天夜里,杨月楼肌沈月春送的切糕里面,找出了一个小纸团儿。借着微弱的灯光,展开一看,上面是八个蝇头小字。
“锻炼身体,等候劫狱!”
他猛吃一惊,心里不由地喊道:“好哇,你们真想出了妙点子!”
他双手一揉,慌忙将纸条填进嘴里。咬一日切糕,猛嚼一阵子,然后一起咽了下去。
十天以后,丁少奎兴匆匆前来探监。
最近一个时期,丁少奎一直陷入忙碌和亢奋之中。他不仅把。拯救杨月楼,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而且认定,只有他才能承担和胜任这义务。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划与奔波,他完成了三件志得意满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他狠狠惩罚了韦天亮。一开头,他就把杨月楼冤案平反的希望,寄托在那恶棍的撤诉上。可是,他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不但再未找到答应撤诉的韦天亮,杨月楼却已被屈打成招,定成了冤案。既然撤诉已无实际意义,他也就放弃了继续寻找韦天亮的努力。不料,踏破铁鞋觅不蓟影子的流氓,竟被无意中发现。有一天,丁少奎去一家下等妓女的台基里寻找三庆班一个武生演员,无意中,竟碰上了韦天亮。原来,那恶棍并未逃离上海,而是包了一个小倌子,足不出户地藏了起来。丁少奎二话没说,拖例韦天亮就是一顿好打。直到给他敲碎了双腿的膝盖骨,方才扬长而去。有了这点“报应”从此以后,韦天亮再也别想站起来走路。丁少奎也出了一口恶气。
他最为得意的第二件大事,是智救王妈。当王妈游街的时候,他当着人山人海的围观群众,一举救出了被殴打的读报人痛快地惩罚了两条乱咬人的疯狗。最使他兴奋的是;当王妈头碰石狮,晕倒在地时,趁衙役返衙报信之机,他急中生智,飞步抢上前去,将昏迷的王妈,背进停在附近的一辆马车中,打马飞跑。终于躲过役衙的追捕,将王妈转移到安全地点,隐藏养伤。
而风险最大、最陡丁少奎兴奋的却是第三件大事--设计搭救杨月楼。他知道,叶廷春是个宁肯错判,却不肯错放的酷吏。杨月楼落到了他的手里,只恐难以囫固着出去。因此,唯一一条救急而有效的路,便是劫狱。凭着他的武功,要想破牢救出一个同样浑身有功夫的人,并不是什么难事。何况他已经说服三庆班十几个身手矫健的年轻演员作他的帮手。准备趁夜深入静之时,翻墙进入大牢,将杨月楼一举救出。然后连夜逃离上海……
一切都进行得异乎寻常的顺利。只要杨月楼一点头,朝暮之伺,便可行动。但是曾历海对丁少奎的豪举,一直摇头表示反对。
“大哥,不来绝招儿,你有啥法子让师弟出狱?”
对丁少奎的质问,曾历海自然只有摇头叹气的份儿。
“还是的!我们能瞪着大眼儿不管,让叶廷春任意折腾好人?大哥,这事用不着你担干系。你陪着伯母赶快离开上海北归,天大的风险由我担。即使不成功,大不了坐上几年窝囊牢。我决不会连累师弟。娘的,这世道,到处是吃着人粮食,不拉人屎的正人君子。往后,我们也犯不着再粉墨登场,累死累活地给他们解闷取乐!”
“少奎,怎么也要遵重桂轩的意思。如果他不答应,说什么也不能干!”自己动不住,只得端出杨月楼来。曾历海猜得着杨月楼会怎么回答。
“好,我依你这句话。”丁少奎只得让步。“我不信,师兄还没受够那份牢狱之苦!”
丁少奎满以为,他的周密策划,一定能得到饱尝刑狱之苦的扬月楼的欣然首肯。所以,今天早早地来到了探监室。
等到杨月楼脚步蹒跚地来到木栅前,刚刚站定,丁少奎便兴奋地问道:“师弟,你的身子骨近来如何?”要举事,首先得杨月楼行动利落,所以密信申,强调要他“锻炼身体”。丁少奎的第一句问话,正是暗含着这层意思。
不料,杨月楼冷冷地答道:“我的身子已被严刑重讯搞垮了--短时间内,绝难恢复健康!”
杨月楼的回答,不啻是当头一棒。丁少奎不由打了一个冷战。
“师弟,这身子骨,也不能指望一天就好呀!”他用恳求的声音说道“刚才你走路,我看清楚了,也差不多……”当着狱卒的面,丁少奎差一点把“差不多可以越狱”的话说出来。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差不多恢复了健康。只要能够自己走路……”
“师兄!”杨月楼知道他还想说些什么,便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上次就跟你说过,赶快让三庆班的同事回北京,久住下去害多利少。师兄,你想过没有?戏班留在这里,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在这花花世界上果久了,吃饱饭没事干,假使学坏几个兄弟,怎么回去交差?再说,戏不能唱,只开支,无进项,再耽搁下去,不但饭没得吃,只怕连旅费也要筹不出。三十多“子人,天天要张嘴吃饭,那时,你怎么招架?”
“师弟,戏班子用不着你操心。天大的事,有我承担!”丁少奎焦急地望着对方,“现在要紧的是你,你!怎么也得想法子,救……证他们放出你来。”
“师兄,你们千万别再蛮干惹事啦!你听明白了没有?有劲,要使在槎“上。我怎么把三庆班带到上海来,你再怎么把它带回去,交给师傅。就算是了却了我一桩心愿。这也是孰唯一要求你做的!”
“师弟,我们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哇!”丁少奎分明忘记了旁边还站着个狱卒,突然冒失地高喊起来。
“既然都准备妥当了,你们今天就该动身!”杨月楼故意把话槎往别的事上扯。
“师弟,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丁少奎急得直跺脚。他把“意思”两字说得很重。
“我懂你的意思!”杨月楼也把“意思”两字加重了语气。“可我的意思你也该明白:我下定决心,要把这冤枉官司打到底,直到他们无罪释放我!我是每天都在锻炼身体,可那是怕扔生了身上的活儿。怕将来重新登台的时候,对不起我的热心听众。别的,我根本不想!”
“师弟!”丁少奎流着热泪在恳求。
“你不要再说啦!”杨月楼怒视着对方,话冷得象往外抛铁球。“我打定了主意,谁也别想说动我!我只求你把我的意思,跟我母亲、岳母、曾大哥以及三庆班全体同事讲清楚。恕不久陪,再会!”
杨月楼一口气说完,不等丁少奎开口,车转身子,大步走出了探监室。
“你认为真有爱民如子的官家吗?尾毛灰!他们首先是为自己。”望着杨月楼的背影,丁少奎在心里狠狠骂了起来。“哼!只怕等到无罪释放那一天,你也就让他们折磨得登不了台啦--精神病!”
善良的人,总是用一颗善良的心去衡量别人。
上海县令叶廷春的醋刑严鞫,并没有使杨月楼清醒过来,改变初衷。人是好的多,官是清的多。被吊过大梁之后,他仍然认为,象叶廷春那样的奸官酷吏毕竟是少数。总有一天,会碰到一个揆情度理的清官,平反他的冤案。“无罪开释”才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只有“无罪开释”他才能一身轻松,光明正大地重登红氍,与他的热心听众,台上台下,共同陶醉。要是不能再登戏台,还不如死了痛快!他从未想到过借助别的门路,尤其是大逆不道的途径,离开这使人受尽煎熬,思之生畏,地狱般的囚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