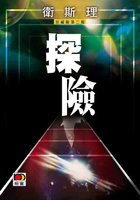阴雨增愁肠。杨月楼站在廊檐下,迟疑了好一阵子。长叹一口气,无限惆怅地返回了旅舍。推开自己的房间门,见曾历海捧着水烟筒,坐在了临窗的桌子前。
“大哥,这么快就把少奎赢啦?”他感到一阵快意,不是为赢棋,是为曾历海的不期而至。
“嘿!赢啦?我要是赢了棋,他会放我走?输棋,还得输得象真的一样,这才脱了身呢。哈……”
杨月楼笑道:“下棋本来是玩耍嘛,可师兄,一摸棋子,就象披挂出台,非得斗出个高低胜败不可。”
“咳,这人,哪儿都好,就这脾性--难改呀。”曾历海点上烟,抽罢一简,接着说道:“桂轩,刚才你去那边儿,是找我有事儿?”
“没,没啥事。”本来想找曾历海聊聊,不知为什么,又否认起来。
“桂轩,您又来啦!有话就痛快地往外说么,憋在心里头,又不能顶饭吃,你说对不?”
低头沉思了一阵子,他终于抬头说道:“大哥是为小弟,月楼终生难忘。我也不是不赞成你的主意。你不是常说,推己及人吗?我总觉得,咱们做得绝情了些。那么粗鲁的回绝,不,是打击,一个小姑娘家,怕是要承受不了的。”
“夫子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历海缓缓答道,“论说么,我们不该那样决绝。那姑娘也够可怜人的。”他望了望扬月楼痛苦的脸色。按着提高声音说道:“可是,天底下,该可怜的人无其数,咱们可怜不过来呀!再说,一个小姐,看了三场戏,就那样走邪入迷,硬闯辕门地自荐自身,太轻佻了点不是?这样的女人,谁能保她始终如一不变心?再其一说,咱们千里迢迢来上海滩献艺,举目无亲,比不得在京城,人情面子多,遇事有个帮衬照应,在这认钱不认人的十里夷场,要是闹出点饥荒来,有咱们好看的!”
“大哥,事情能有那么严重?”
“凡事不怕一万,就伯万!”曾历海右手捏着烟签儿戳得桌子笃笃响。“你忘了交北不交南,交南要难看的话?人们不是还说宁交十个北侉子,不交一个南蛮子吗?本来,蛮子就比猴子还多着仨心眼儿。自从上海滩辟为通商口岸以来,他们整天跟洋鬼子一起搅合,不沾上几分鬼气才怪呢。只怕我们这些傻侉子被他们坑死了,还不知哪来的症候呢。所以说,跟蛮子打交道,要是不抱定十二分的小心,不定啥节骨眼上,就落进了他们的圈套!”
杨月楼苦笑摇头:“大哥,岂可以地域论人?哪里都有好人、坏种。对谁都三心二意,咱们自己不也成了狡诈的人”
曾历海半晌未吭声。又装上一筒水烟,长吸一日,然后说道:“你这话也在理。不过,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古训一刻都不能忘记。况且,韦家是富商。无商不奸。只伯比平常人家还多着几尺黑肠子呢,不信……”
杨月楼打断他的话道:“大哥又在以事业论人。人跟人不同,连强盗都有义盗,难道买卖人就个个见利忘义?”他鼓起勇气继续说道,“我觉得,狡诈狠毒昀人家,未必生得出那样情深豪爽的姑娘……”
“哈一一”曾历海未等杨月楼说完,便大笑起来。口桂轩,你叫我不以地域、事业论人,你自己倒以血缘论起人来啦。照你这么说,刘备生了个阿斗武大郎的胞弟是武松,诸葛亮的老子竟是个无名之辈--你怎么说?依我看,女儿豪爽,未必老子不是嘎货!”
“大哥,人家又没得罪你!千吗那么……”杨月楼把后面要说的“缺德”二字咽了回去。“算啦,不说啦。我不过是,随便聊聊。”
对于曾历海的话,杨月楼不但一向唯命是从,而且总是以长兄之礼相待。不料,今天不但听不进他的忠告,反而当面反驳,差点连挖苦话都说了出来。曾历海感到一阵不快。转而想到“当局者迷”的古语,又立刻原谅了他。低头吸罢两筒水烟,抬起头,掉转话头向道:“喂,桂轩,伯母何时能到上海呢?”
杨月楼无精打采地答道:“原想从天津搭海轮。我伯海上风浪大,老人身体吃不消。劝她沿大运河南下。虽然慢一些,但却安全。母亲信上不是说3月!6日动身吗?今儿是四月初一,已经半个月啦。朝暮之间该来到啦。”
“伯母来到以后,该陪着他老人家好好玩玩。老人家一辈子受苦。如今,儿子成了名,该让她享点清福咯?”曾历海无话找话。
“大哥说的是。”杨月楼迟疑了一会儿。又问道:“大哥,母亲来了之后,韦家之事,要不要向她老人家提起呢?”
“已经过去的事啦,还提它干啥!”
“我总觉着,有点……万一那姑娘有个好歹,咱们怎么交待呀?”
“与咱们毫不相干!”曾历海豁地站了起来,神色严肃的象审判官。“月楼,当断不断,必有后患!你在台上尽演英雄好汉,何至于连个轻佻温情的姑娘都放不下呢?难怪古入说:“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就凭你杨老板这样的一表人才,武生泰斗,啥祥的女人不尽着你选?千么非得去找风险冒呢?”
“……那就算啦!”
本想得到曾历海的支持,不想又一次被他软硬兼施地顶了回来。他车转身,惆伥地瞅着窗外阴霾的天空出神儿……
不论洋医,国医,凡是请来给韦惜玉诊病的,无一不是沪上名家。他们个个声称自己妙手回春。说什么要不是请了他来,“病人怕没指望了静。但他们不但不能“妙手回春”连病症所在,也无一人说得出来。王妈说的在理。看来,除了杨月楼能将女儿从枉死城里拖回来,怕是没有别的灵药妙方啦。韦王氏也知道,韦宅不是普救寺,女儿的闺房也不是张君瑞的西厢书房。由她在一旁紧紧盯着,丢人现眼的事,他们想敞也做不出来。
可是,要照王妈说的,自己亲自出马,登门礼请那戏子,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不行,一万个不行嘹!”她在心里一遍遍地高喊。死丫头!由着性儿胡闹,已经丢尽韦家的面皮啦。再要我堂堂一家之主去下价恳请,不如让我给叫化子磕头作揖哩。再说,真到了那戏子跟前,笑脸容易做,施礼也不难。再往后呢?怎么开口?能说;“杨老板,我女儿想你想得害上了相思病啦。劳您的大驾啦,到我家走一趟--救她一命嘹!”呸!呸!死啦也不能那么干!可是,请不来那贱戏子,能眼睁睁看着女儿等死吗?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哟,给我指一条路吧!”
焚上一炉香,韦王氏跪在新设的神龛前,双手合十遍又一遍地祷告。
丹桂戏园案目陈宝生,笑嘻嘻地来到了韦宅。
对于除案目来说,就象“陈”字永远跟他分拆不开一样,笑容也早已成了他脸面五官上的有机组成部分。自打十八岁人丹桂戏园混事起,二十多年看顾主脸色行事的案且生涯,使他练就了一副恼怒不形于色,笑容永远挂在脸上的本领。有人说,“有钱买得鬼推磨,”也有人说,“走遍天下钱开路”。这千古真理,他从心底佩服。对于一个穷案目来说,既然跟赵公元帅搭不上亲戚,他只得投靠和气与笑容。和气生财,笑语怡人嗦。于是,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分外轻松和欢愉。笑容,帮他办成了许多本来希望渺芒的事体,也推着他从打杂的,爬上了戏园案目领班。凭着一副嘻嘻的笑容,门禁森严的阔公馆,富丽堂皇的宅邸,永远向他洞开着大门。
他已经有一个多月未来韦宅“送座儿舻了。杨月楼领衔的三庆班,一个多月来,愈唱愈红,天天爆满。光找上门的老主顾,就够他八面应付的。哪里还顾得上主动上门送座儿?今天,他笑嘻嘻地来到韦宅,名义上是“看看老主顾为啥一个多月不再看戏”。实则是想探听一下,他替王妈“引见”杨月楼的事,发展到了什么地步。看看是否还需要他搭桥牵线,以便从中“意思”几块银洋花花。
不料,韦宅的气氛今天有些异样。开门的老仆范五,虽然与往常一样,彬彬有礼,脸上却露着愁容。进到客堂之后,前来献茶的王妈,也是脸色苍白,神情忧郁。显然,韦宅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体!一看这情景,他急忙收起笑容,正色说道:“韦太太跟小姐,这么久勿来戏园看戏,小人记挂得很嘹。”他阿眸子里闪着关注的神色。“令天,小人一来是给韦太太、韦小姐请安;二来呢,特来禀告太太,杨老板在丹桂的合同,只剩。下三天就满了。收场戏更加精彩--耐看的紧嘹。阿拉已给府上留好了座位。不然,杨老板转往别的戏园,一来看戏路远;二来涅,小人效劳也勿方便不是?”
王妈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得敷衍道:“陈先生,眼下,太太不能去看戏。”
(赵公元帅--传说中的财神爷。)
“莫非太太小姐不在府上?”探询的目光,停在王妈脸上。
“在……在呢。”王妈瞥一眼陈宝生。略一沉吟,指指内室说道,“这两天,太太身子不舒坦。这不,刚剐睡下呢。”
“那……”陈宝生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奶妈的神色。“阿拉是勿是改日再来蝗?”
王妈若有所思地答道:“请陈先生稍等。俺看看,要是太太醒了,禀告一声,看陈先生留的座儿,是不是让给别人。”
陈宝生连连点头:“那好,那好嘹!”
进了内室,主妈附在韦王氏的耳朵上低声说道:“太太,陈案目来啦,问太太去不去看戏呢。”
“什么时候啦,还有那闲心!”韦王氏闭着眼睛,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喂,太太。俺想出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韦王氏睁开了红肿的双眼。
“陈案目,人机伶,又跟杨老板熟,对他的脾性不用说摸得着几分。要是咱们请他帮忙,一准能想法子把杨老板请来。”
韦王氏抬起了身子:“阿宝的事,怎么能跟他说哩?”
“太太尽管放心。当说的说,不当说的,俺不会漏一点儿口风。俺知道怎样维护韦家的体面。”
“唉,没法子--你就试试看吧。”
王妈回到客厅,朗声跟陈宝生说道:“陈先生,太太睡熟了,不忍心叫醒她。留的座儿,就让给别家吧。”
“那好,那好。”陈宝生点头应着,但坐茌那里一动不动。然后眨眨眼问道:“王姐,倘使府上有需要小人帮忙的事体,你尽管吩咐就是啦,小人一定遵命嚎。”
王妈在他对面坐下,极力平静地答道:“不瞒陈先生,这两天太太心里很生气呢。”
“那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