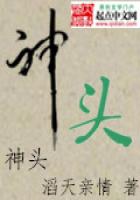第四十三节:星空老和尚旧话
我与退居的老和尚很有缘的,寺院为了整理老和尚亲身经历的一些管理寺院的文献,让我负责记录整理。我得以亲近本山长老星空大师。老人家是个直性子的老实人,八十高龄,很平易近人。从老人家的口述文句中,我们可以想象老人家走过的时代速影,也折射出佛教的历史背景。老人家的话,平白实在如话家常,真实可信。
现收录我的整理文献,如下,题为《我与寒石寺》。
我与寒石寺
一、初来寒石寺的我:闷着头干,铁下心管
1963年那年,我43岁,昆城市统战部、宗教处和佛教协会的领导派我到寒石寺来做监院那时的寒石寺没有现在这样气派,就连我现在住的方丈室等大多数地方,还都不是寒石寺的。当时的寒石寺只是包括服务部(现罗汉堂对面的工艺卖品部)、客堂和藏经楼这么大点的地方。“文革”以前,从外面一看,就一口井,一个藏经楼。现在的小卖部在当时是长着冬青树、山芋、“雪里红”菜的菜地。
僧人们都是从昆城市内的乡下小庙里集中过来的。当时的方丈叫通如,住在东侧。另有韶一、昆山两位法师——韶一卖门票,三分钱一张,住在西北面;昆山干闲杂活儿,住在现在的长着黄杨树的那个地方。平日里大家要吃水的话,就到那口井里去吊。
我来寒石寺之前,在西园寺做僧值,在安上老法师统领下,学修自在,不需操太多心。昆城市佛教协会的领导把我从西园寺抽调来寒石寺当家,我很犹豫——我知道寒石寺庙不太大,生活很困窘,十分担心自己会不能胜任。最终宗教处还是把我调来了。当时的庙确实并不好管。韶一是四川人,脾气不太好,整天干些杂七杂八的事,常在庙门口卖小说书赚点零化钱,还看相算命的,很让人头痛。通如老和尚不管事,人是个好人,遇事哈哈过,啥事都落到我头上。我一去管韶一,他就跳,说你还管我?
“屋漏偏逢连天雨”。到寒石寺之后,寒石寺的房子好像要看看我的道行似的,三天两头的,不是这儿漏点雨,就是那里瓦破墙塌。而按当时的制度,超过五元钱的开支,就一定要打报告到宗教处去审批。记得有一次我自作主张买了把大剪子,去修剪冬青树。通如老和尚知道后,就责怪我太胆大。当时我手上又没钱,要买黄沙、买砖瓦,就只好跑到西园寺去找安上法师求救。我当时身体好,用两个蕃箕到西园去挑砖瓦,一天好几个来回都不累。回来和泥、修墙和铺瓦,还要小心两脚不能踩到底瓦上,以防踩坏漏雨。每逢上面来客人要接待,就得找居委会,帮助打扫卫生,接待以后就又一如既往,恢复原状,没什么大事件了。
刚来的那一段时间,寺务繁忙,人又难管,庙穷缺钱,我就又跑到西园寺去找安上法师理论,说寒石寺我弄不了!要求回来,安上法师不让。我就又隔三差五地去看望他老人家,倾听他教诲开示。有时上面来领导或居士带东西供养安上法师的,安上法师却把它布施给我,又一面好言相慰。
不久,来了两个和尚,一个叫妙华,一个叫月波,是昆城城里来的,有俗家老小,硬软不吃。我便吃住他们打扫卫生,他们不扫,演林老法师主动代扫。妙华喜欢下棋,上街去下到吃饭也不回来,让人去叫,还发脾气;俗家有人生病了,有困难,来吵着要我补贴,说家里穷,没钱。月波有气喘病,在枫江楼卖茶、卖碑贴;看到炉子上的茶水开了也不去灌,我管他,他却到安上法师那告我的状,反怪我不帮他灌水,横竖乱告;他吃饱了,有时还要带点回俗家去,我只好睁一眼、闭一眼。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知难而上:闷着头干,铁下心管。
二、极“左”思潮冲击下的寒石寺,靠卖大粪来补贴生活
六十年代初的寒石寺,不但蒙着困难时期的阴影,而且当时社会上有个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宗教理论是反动的,和尚属剥削阶级范畴,宗教不可以为社会服务,和尚要通过教育改造以后才能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上面的干部来到寺院里,就是这么面对面地教训我。每个星期,佛协都要求全市的僧尼集中到华严寺(现为昆城市景德路察院场邮电局)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佛教是迷信,僧人挨个儿要自我批评,大骂自己一通——迷信职业者,属剥削阶级的同路人。以后三、四年,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是1966年,我45岁。
为了解决寒石寺常住僧人的吃饭问题,我想出了一个卖碑贴的法子。碑贴由碑房处拓下,是由月波在枫江楼卖茶代卖的。有时来些日本人,在一旁等着拓,生意也渐渐多起来了,特别是清朝俞樾所书的张继诗碑,倍受欢迎。卖碑贴的事一天比一天红火,旅游局的人看得动了心思,不肯让和尚卖,他们要来拓碑卖贴,为这事插手、争夺。
那时的宗教处长叫高其志,是位老干部,现在还健在。我到宗教处找他反映情况,告诉他寒石寺的生活来源:一是靠三分钱一张的门票;二是靠卖碑贴,五角钱一张。若碑贴不让和尚卖,我们生活没着落,经济来源何处来?高处长答应去查点,但并不说好丑。后为这事我又跑过好几趟,卖碑贴的权总算收回来,让寒石寺卖。
光靠这两项收入,是解决不了五、六个和尚的吃饭问题的。我又想出了卖大粪的法子,就是现在素斋馆后面的厕所里的大粪。每逢春三月,我们把大粪挑到乡下卖给农民。大粪虽然卖出去了,但收不到现钱,三番五次地催要,结果弄了些稻草来抵钱。
现在的寒山别院,原来也是寒石寺的,南侧的一条河叫纸浆河,华盛造纸厂的工业废水往河里排。当地人从河里捞废纸浆,借寒山别院的地皮,做成饼粑粑晒干,卖,也送些给寒石寺卖钱,抵地皮租金;做纸的稻草脚子,也捞上来晒干,卖给城里人烧火,也送些给我们。这样可解决烧草问题。
其实,在那个时代,不光是寒石寺的和尚生活困难,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很困难。今天寒石寺的好日子,是党的改革开放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好政策带来的,我们要当好和尚撞好钟,只有国富民强,和尚才能安心念经,如法修行。
三、“文化大革命”初,寒石寺的劫难
1966年,我45岁,是人到中年的黄金时代。但国家不幸,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不象现在这样:宗教信仰自由,寒石寺的佛教文化事业蒸蒸日上,和尚参政议政,成为管理国家的主人。所以你们年轻的法师一定要爱国爱教,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为了让你们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现在给你们讲讲“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老和尚是怎么走过来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灵岩山的佛像首先被打掉了,接着附近尼师住的寺院里的佛像也被打掉了。情况一天天地严重了,我们在寒石寺里整天听到外边“乒乒乓乓”的嘈杂声,和“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声。寺院外的红卫兵叫嚷着要向我们这些“和尚走资派”夺权,但寒石寺的和尚们在这时抱定誓死保护寺院的决心,任由他们软硬兼施,死守庙门,防止他们进来搞破坏。
还是安上法师有智慧,叫我们把大门关上,佛像封好。当时佛像——罗汉堂内供着西方三圣,空海堂供着观音菩萨——一律封好,在门上贴上“游客止步”或“禁止参观”等字样。这样一来对游客开放的,就只限于现在罗汉堂对面的小卖部,当时叫旃檀园的。中午,我在罗汉堂打坐照应,他们或小睡、或下棋、或卖水,大家齐心协力地来保护寒石寺。
偏巧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在当时说不清的事情,——有个日本人的游客,来买碑贴——大概是开车子的人汇报上去的,加了个帽子说是和尚用报纸包的什么机密文件,泄露给日本人了。上面来人严查核实,要求马上汇报日本人来寺里的准确时间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如实地详细地汇报。
日本人买碑帖的事件过后没几天,红卫兵叫通如和我一起到华严寺去开会。我预感到什么事情要发生,心上七上八下的,晓得不好,又不知道个究竟。
一跨进华严寺的门,还没看清,就有人把我装材料的包一把夺去,扔在一边,让鞠躬。要九十度弯腰,不让抬头;一边听着“你们剥削分子”的叫骂喧嚣,说和尚是寄生虫、放毒。仔细瞅瞅,西园的安上法师在,明开法师也在,还有一些二堂尼师。从早上九点左右开始鞠躬,一直鞠到下午两点多钟,一开始还能坚持,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腰疼得爬不起来。做得稍微慢了一点,他们就拿东西抽。就是这个样子搞的,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说到鞠躬,性老情不自禁地拄杖蹒跚起身,做一个弯腰垂手的姿势,我感觉他身心在颤栗,他双目溢满愤怨与惊恐,我隐约感到“文革”这场劫难在一个出家人心灵和肉体上留下了怎样不可磨灭的伤痛,乃至抽搐至今,真是让人胆寒生惊,我的额头不禁渗出一层冷汗。)有些尼师穿得干净整洁,造反派强迫她们脱光了鞋,在地上爬着走,还要被打。骂她们躲到庙里,睡避风港,享清福,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剥削分子,正是革命的对象。出家人没有说话的理,只有被造反有理。
两点多钟了,我们饭也没吃,腰痛得要命——最后还是安上法师向造反派们求情,请宽容一点,造反派头子念及“寄生虫”可怜,让我们滚,大骂一通相送。
我当时手上有张月票,被他们翻到了,一把抢过去,骂着“剥削分子,还买月票!”。
四、内忧外患
在华严寺院一炮斗、一炮弄的,回来一看,大殿的佛像被打坏了,我寮房里也是一片狼藉,连地板也被敲翻了个遍。到处都贴满了什么革命派、红卫兵造反派的标语,上面写的是:“打破封建迷信的意识形态”、“限期交出所有财务账目”等等。
当时的会计姓方,是街上的在家人,宿舍就在现罗汉堂的角楼里,和演老住一起。那时每月都做财务报表公开,很透明,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钱。可造反派非要“交帐”不可,通如也气得不开口——本来就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嘛!红卫兵夜里爬墙过来撬锁,说是封建的东西,就要坚决铲除。日里夜里,我们总是心神不宁,生怕会发生什么事,真是一夜十惊,寝食难安啊。
出于对时局和寺务的不了解,家里的韶一、昆山、月波他们时常到安上法师处乱告状、探风声——那时人人心都不安,和尚内部也成立了造反派,是红卫兵组织的。也有些老和尚也糊涂,随风倒,揭露僧人的内部事件,乱写大字报。更可气的是当时,有一个叫月发的乡下和尚,是赶经忏的,竟跑来鼓动寒石寺院的造反派闹到西园去,畜谋打西园寺的佛像,但是被大家识破了,没有成功。北京也来了个造反派头子,跑来煽风点火,说我也是当权派、走资派,惑众斗我。唉,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不久,生活费不发了,大家没有饭吃,我上去哭诉,向当权派要。每个僧人好不容易分了一份,可还有些有俗家的和尚在那里闹,要我的一份,说我就一个人拿一份生活费嫌多。后来搞批斗会,有人联合起来批斗我,那打斗喝骂的场景,凶神恶煞的,直到现在,我常常还会在睡梦中被那些不堪回首的痛史惊醒。
五、在混乱的日子里,尽力保护寒石寺
寒石寺有好多碑刻,都是宝贝。如清朝俞樾写的《枫桥夜泊》诗的手迹;宋朝的岳飞、明朝的唐伯虎、文征明、清朝的康有为、罗聘等等名人,也都留有墨迹或字或画。红卫兵常爬墙过来,想砸烂一切“封资修”,我一面讨笑求饶,一面暗里加紧找演林想办法来保护好,以免不测。
我们用稀泥巴把碑上的字糊起来,把买来的宣纸染黑贴上,让它晒干,再用白色粉笔研成粉末制成的颜料在碑面认真书写上“最高指示”和“老三篇”,让造反派和红卫兵看到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随意破坏。当时写的有:《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等等。
我和演老连日连夜地搞,藏经楼也用这个办法,恭恭敬敬地贴满了伟大领袖的画像。月波和妙华看到我们还反唇相讥,说走资派还要吃苦。那时藏经楼里有清版的龙藏,还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
五百罗汉是清朝一位雕刻家的杰作。为了保护他们,我们请五百罗汉搬了三次家。演老是有功的——搬家就是靠他和我用扁担、提桶一担担挑,然后藏在藏经楼隐蔽的密室里。
那时我还要表扬爬到墙上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功德无量。不要现在就砸滥“封资修”,要等“后期处理”,那时执行什么“后期处理”,我也搞不清了,反正一说,他们就被吓住了,大概也是最高指示里的重要一条。
后来,城里来了队“红黄会”的造反派,是轮船上的红卫兵集合起来组织的。他们把大殿、藏经楼用门拦成一格格的,住在里边。枫江楼里挂的些字画匾,我偷偷把玻璃取下来,把字画藏起来。有两幅是清代名人的画,被造反派抄家抄出来,扯碎扔到垃圾堆里去了。还有一尊铜观音像,一尊玉如意,也丢失了。
佛教内部的情况也越来越不好了。寺里的韶一、月波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很吃香。西园寺的明开老法师被斗,把头往墙上撞。明开是个硬骨头,说你们是社会上的垃圾,庙里养着你们,还造反,搞破坏。安上被剃掉眉毛。明学、皖峰、我也都是被斗的对象。皖峰后来到安微迎江寺做了方丈,前年过世了。唉,惨呐!
这期间的寺里生活来源,主要是靠我给附近的村里人理发赚来。村里人也有时也送点肥皂、面粉什么的给我们。
文管会的人来看看,要求我们保管好藏经,防止被破坏。保存好寺院文物是“封资修”,有时又被他们斗我是保皇派,我到现在也弄不清,反正都是红卫兵说了算,只得认命,随他们去。
文革期间,我不谈有功,藏经、碑刻保住了,现在觉得欣慰。
六、“先劳动,再学习,斗的斗,死的死”
造反派、红卫兵红极一时,好在安上、明开和我也没被弄死。“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搞闹闹的,也不是个办法,我们都暗地里担心这样下去究竟会是个什么结果。西园有两个和尚阴阳怪气地来通知,要我集中到西园去学习,学习什么?我想。
到了才知道,是位叫姚天惠的人负责的,那个人倒是个好人,现在九十多岁了。去“学习”的人,不只有佛教的,还有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不过是以和尚为主体,集中到一起改造的。陆建也在——陆建当时六十多岁,是西园寺的退居方丈,即明开的前任方丈。当时普遍认为,信仰宗教的人思想上都有污点,虽然程度不同,但都反对过政府,都是放毒的,所以要通过改造,要在监督下劳动。
白天把我们送到龙兴学校去劳动,种菜、拔草或挑粪,陆建也去。下午四点多到西园去吃晚饭,日日如是,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晚上回来要学习——自己骂自己,批判佛教是迷信,害人的。还不仅如此,陆建除了拔草,还把他隔离到土坡上,让他趴在那里除草,有人专门看住。当时陆建六十多岁的人了,年老体衰,手脚活动不方便,力不从心。干活稍慢了,就要遭人喝骂,骂“跑快一点,剥削分子、卖什么老?卖!”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陆建吃饭先合掌,默念供养咒,马上就有人汇报上去,说是怀念封建,吃饭也不肯丢,还梦想回到已失去的天堂。
为什么会这么折磨陆建呢?原来在以前,上海有个有名的流氓头子叫黄金荣,曾送了个匾到西园寺,当时陆建是西园寺的方丈——因为这件事,就被扣上了“中统特务”的帽子,每天斗他。就这样,在“文革”中,造反派一直按“中统特务”处理他。
白天把我们集中到龙兴学校劳动,晚上开会学习,把西园寺、寒石寺院的僧人集中到灵岩山上去,叫陆建交代。
由造反派领导的工宣队负责,华九年当队长,倪志海当指导员,进住灵岩山,他们高举“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口号,说和尚躲在避风港里,都是一批坏蛋。对和尚们“内查外调”,实行“一斗、二赶出、三抄家、四占据”的政策。
灵岩山的70多岁的妙真上吊而死,还有几个和尚跳崖而死了。其中有个和尚想把戒牒藏到石洞里,被人看见报告上去、要斗,吓得从山上跳下去死了。西园寺的仁理、三思等跳河而死。那时天天斗,西园有个叫旭明的,看见猫吃鱼,就骂猫懒、贪馋,被人汇报上去说是“指樟骂毛”,阴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小眉毛”也被吓得吊死了。
当时,西园寺有个叫大宝的和尚,文化好,字也好,曾在南京为伪政府汪精卫做过事,被安排在西园文物室看藏经。他想得开,人倒也潇洒,有时到街角去改善改善生活,回来后就痛骂自己为业障深重,到灵岩山去也照直说自己在南京为汪精卫做过事,吃过两餐大菜,造反派却没怎样他。
有个和尚叫胡胜的,曾做过伪保长,查出来,开批斗会,高呼“纠出胡胜,有冤还冤,有血债还血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后来押送回原地了。
上海真禅有个兄弟,也集中到寒石寺院的,是个老实人,对历史古典很熟。妙华、韶一甚是嫉妒他,说是哪个山上下来的大和尚,后来也被拉到灵岩山上批斗了。
还有一个泸洲的达和,后来押送回原籍的,他走时,关照我,还是别回去的好。后来知道了,达和说得对!
山里面有个农场,有人讥笑和尚在在城里过得开心,吃现成的,说风凉话。挑煤炭上山,挑大粪、扛面粉、推煤球和挑煤炭,这些明学和我都干过。
和尚吃素,要求开斋。他们却把山上养的猪杀掉,强迫僧人吃荤,开始吃很腥气,他们不知怎样搞的,可能放了些酒在里边。
有一年多,他们不管你有罪无罪,吃饭睡觉,随时恣意施以精神和肉体的虐待,使人整天处于失魂落魄的恍惚之中。斗够时候骂得最多的是“你这个老不死的老棺材、你是个特务”,简直像鬼哭狼嚎,叫人心惊胆战。那一段时间里,先劳动,再学习,斗的斗,死的死,实在是不堪回首。
那时,耳朵里整天都塞着口号、报告、开会、谁斗谁的。什么打倒地主啊,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自己啊,还要求每人缴大字报,要检举揭发人,什么道德沉沦、佛教失败呀、无中生有呀。
大字报到处贴,贴满了灵岩山的前院后院。我一直忏悔到现在,有一张大字报写错了,我写的是“安上是大红伞下的走资派”。人被斗晕了,没话找话说,也为了应付红卫兵造反派们。学习了一年多时间,眼看着死了多少人,眼看着这么多人还活着、还活过来了,眼看着就这么些事,没办法,就是这样的。
七、下放
韶一在寒石寺院看庙,归“红帮会”。有天开庙门,来了一个的小姑娘,传出话来说,韶一不正派,动手摸脚的,就送到灵岩山上被斗。冬天回来拿棉袄的,被什么人偷掉了,老昆山有病,又是个聋子,倒也太平无事。
事件总要处理结束的。演老回乡下,送回去的。月波后来看了几天钟楼,病死掉了。韶山死在江北,有了个儿子,可能那时他手里还有点小钱。
我被安排到农场,后来怎么自己要回老家了。整天没头没脑似的。
我去找安上商议,安上说除了做和尚,哪一项都比做和尚好。其实我那时不回去也不要紧,回去的人员名单里没有我——这是以后听人告诉我说的。
回去的日子真难挨。我想是我写的关于“安上是大红伞下的走资派”——因果所致。
第二次到乡下去。“好人不下放,下放不好人”,知青们都看中这般人,盯住,不是好人。明学被说成是坏分子,后来到昆山去了。他起初由兄弟照顾,可兄弟的女眷看不下去,容不得,日子难过。地方干部安排我到粮食加工厂,还算好的,照顾我,也苦。在打碎机上干到半夜,打米、打粉、打草等等,工分到各队去拿,苦得要命。
那是1969年,我47岁。由于同意每位和尚离庙前可带一块铺板,以免下乡没有地方可睡。我就带着清代俞樾老人题写的“五峰古方丈”五个古逸大字的木板到农村去的。在那“夜夜清灯伴孤魂”的日子里,这古匾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托。艰苦的劳动,抑郁的心情,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我终于一次又一次的病倒,胃疼得卧板不起。
当时村上有一农户打家具,听说和尚睡的是块很厚实的银杏木板,便找上门来,愿以高价购买,那时,虽然我连一分钱一块豆腐都不舍得买来补养身子,也没有几个钱,但我没动心,一口回绝。回来后,又拿回来了,现在挂在我日常起居的方丈书斋内。
前面说到的真禅的兄弟,就热死在那地方,是拔草时热死的,当时,倒下心还跳,他对历史很熟悉。睡觉时念佛,被人汇报上去,他说没念,是做梦念的。红卫兵说,你心不死,怀念旧天堂,怀念失去的天堂。后来我听说昆山在那期间也自杀了,阿弥陀佛!
文化大革命这个风气一来,人们的眼晴都斗红了,城里乡下到处斗,六亲不认。人心都浮起来,把坏事都推到别人头上,谁都保不住自己。晚上一听到铁棒拉地响,就知道要来了,人心惶惶。
记得当时有个叫中莲的法师,是山东人,俗名蒋文彬,是个硬骨头,有道心。他在批斗会上高呼,批林批孔下地狱的,孔子是大圣人。后来下放回老家,到山东去还是这一套,吃了几天官司,拨乱反正后落实宗教政策,又回来了,他是专修念佛法门的,死在灵岩山。
后来做过国防部长的******,“文革”中也来寒石寺院住过一段时间,是我来掩护他们的。前天有人来,为写本******的书,来找我调查材料,说******明年春天还要来看我的。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恶梦般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前后,我与寒石寺院的这么些有关大概情况。我保存下了藏经、碑刻,没有什么功劳可谈。
八、二回寒石寺,百废待兴
今天从我第二次回寒石寺院谈起。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粉碎了“四人帮”,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
我是1969年下放到昆山去的,在昆山农村劳动。到1978年秋天,昆城公安局的人叫我上去,找一个叫于玉崑的人,是昆城统战部长——那时宗教归统战部管,后来才设宗教局的。是个午后,打电话过去联系,让到园林管理处,已是下午四点多,晚了。园林处有两个女的办公,出了个条子,让我回到寒石寺,说打电话联系好了,让我去敲门。
跑到寒石寺,关门了。有个看门的叫周圣贤,是公安局的,早晚值班,人很好。负责人姓马,马主任,回去了。
一别近十年之久,院里一片荒凉,庙宇破旧,佛像被封,院落零乱,满目凄凉。所幸的是殿堂、钟楼、碑廊和明清时的几口大钟还依然存在,倍感欣慰和亲切。但大殿内的法器、鼓架都卖光了,很苦。
寺里住着两个僧人——一个叫法忍,他是我以前认识的——1962年前后我在西园做僧值时,他是清众;在灵岩山学习改造时,他是积极分子。我自己觉得待他一直都不错,可没想到……当晚我赶到庙里时,要吃饭了,锅灶上啥东西也没有,法忍让我自己烧。劫后重逢了,怎么这么冷漠,不闻不问地自顾自?我左思右想,纳闷得很。后来才知道他对落实宗教政策有看法,不想要恢复。
另一个叫如法。如法和尚原来也是西园寺的,后来和法忍一块儿住寒石寺院。如法吃面条先供佛,法忍就去汇报——由于文革搞帮派争斗,法忍揣想要保护好自己,必须学会汇报,他养成对佛教的反感乃至抵触情绪,头脑里认为和尚乃至佛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自己平时甚至只烧粥吃,不吃面条。
周圣贤倒很好心,让铺给我睡,铺很小,只能睡一个人,我虽然没铺单,但于心不忍。晚上睡哪里呢?在现在的藏经楼下西北角,那时无寒拾殿,打坐,坐了一夜,蚊子咬得不得了。我很疑惑那时人与人之间为什么那么冷漠狠毒,什么事都不闻不问。经过文化大革命,排斥和尚的思想已根深蒂固了。
第二天早上,马主任过来了。我把园林管理处开的条子交上来,办理报到——接收手续。马主任安排我卖门票,吃饭问题自己解决。
藏经楼下面开着茶室,烧炭炉了,我向周圣贤借了个锅子,借了点米,就着炭火炉烧了锅粥,暖饱了身子。
当时有管一玉、曹广明、周圣贤三个人,再加上我,共四个人负责做事。他们主要负责治安,曹广明现在还在寒石寺院,至今已近二十五年多了,现在服务部做副主任,就是大伙儿称他曹主任的那个人,50多岁了,人也很好。我卖票,吃中饭、小憩或上个厕所什么的,要个人来换班,马主任也没安排人照顾一下子,不管不问,第二天来查票核对,错了自己负责。
现在素斋馆这块地方,原来是堆树条子的。锯树辟柴,做煤球粑饼,打杂卖荒货,买煤球等等,反正干力气活儿,少不了我。好在我会骑三轮车,驮驮送送,小三轮一骑,省劲多了。我才进来,基本就是这样子。
刚进来时,穿工作服,不敢穿僧装——弄不透,被斗怕了,思想上还有顾虑,一步三看。时间一长,就渐渐熟悉了,晓得他们的个性。了解到周圣贤是个公安局的老干部,人很正派。后来管一玉也帮我在门口卖票,经常介绍人进来玩,让周圣贤放。次数一多,周圣贤就责怪管一玉徇私情,做老好人。
九、宗教政策落实了,寒石寺终于又象个庙了
昆城统战部部长于玉崑也时常来看看我,让我多说话,不用怕,说现在落实了宗教政策,尽管多说佛教里面的话,如“念佛”、“参话头”,照宣不误,不要有精神顾虑。
如法后来到西园寺去了。我一想,我一个人,没有人和我知心的,弄不到一块儿不行。于是想到演林还在江北,当时我在昆山下放劳动时,演老还专程去看过我,我就私下里写信让演林过来。大概信发出去不久,演老就过来了。演老来时说,俗家侄眷不愿意让他上来,阻力大。
那时是每个月五至八元的生活日杂费。演林来寒石寺,当时有人怕抢了他们的饭碗,闹情绪。我就去找了园林管理处的徐主任,那人有同情心,开了个介绍信演林来的——当时办公室里有个阿訇,阻拦徐主任出证明,徐主任说人原来是寒石寺的,还回寒石寺去,才打顶过去。
来寺里,马主任还不让接受,说没得吃,我说我担保,我吃什么,他吃什么。就这样两个人搭了个铺,用一个小钢锅儿,放些野干菜什么的,往粥锅里一搅,煮熟了,再在粥碗里放点油盐和着吃。当时的豆腐菠菜都是有计划的,要凭票购买,我平时常送点野干菜给来请我剪头的农民,所以人缘较好。他们有时也送点计划票券给我们,送点粉丝、面条的散脚子给我们,所以食宿不大成问题。
法忍是个冷面人,寺里外的在家人都赞叹我和演老两个人相处得好。宗教政策也一步一步加紧落实了。那时,人事、门票等方面的都是在家人马主任他们管的。不知是从什么途径,来了封人民来信转到我手上,说是看到哪个在家人把香钱往自己口袋里塞,我把这封信送到统战部于玉崑部长手上,于部长说,应该尽快落实宗教政策了,让和尚管理寺院。
这个前后,大概是姓马的主任换掉了,换了个姓缪的,叫缪小晴的,男的,当主任。马主任调到园林管理处去了,他帮园林处说话,还把他在位期间为寒石寺院做的大鼓——大殿里用的——一起用三轮车拉到园林处去了,现在大概还在虎丘吧——缪小晴不同意,但还是强不过他。
这其中有一段时间,入不敷出,开红灯,没有钱。有人说我会拓碑贴,就让我搭火车去上海买宣纸,跑了好几家店,才凑足了一百元的货。回寺后,让我抓紧时间拓碑,生意很好,特别是清末朴学大师俞樾所书的张继诗碑,常常供不应求,日本人排队等着要。那块碑现在还立在碑廊,其书法古雅拙朴,独具一格见长。我专门负责拓碑,经济由缪小晴做主掌握分配。姓马的主任,还来,来一天,休息两天。
拓多了,俞樾的那个碑字迹模糊,拓上来效果不好,以后又请精巧的石工复制了一块,马主任很想把新复制的一块碑也拉走到园林处去,好让他们拓着卖碑贴。缪小晴坚决抗议,不让,没拉成,两人闹对立。——后来我把这事汇报给了于部长。
决定下来香钱归和尚管,是通过在西园寺召开的一次佛教协会代表会议上公布的。要求由和尚负责建立起财务财目,还规定有关宗教方面的事务也由和尚管理。我担心靠香钱维持不了生活,起初在心头盘算,不敢接受。有的法师给我打气,让我先接受下来,我将信将疑地就接了下来。还要求穿僧装,说宗教的话语,保管好藏经楼典籍,寺内来客要求僧人负责接待。
从那次会议后,我们才敢大胆地穿上僧装,心里觉得很宽松,像个人样的。日本人有时拿个小本子来,请我签名留念什么的,我就写上“寒山钟声”、“姑苏城外寒石寺”什么的,日本人常丢个一千块钱日币,有时也有日本人结缘给我钱,我都如数上缴给缪主任。那时的日币还很值钱,是一万日币相当于人民币九百至一千元。那以后,经常有日本人来看看,敲敲钟,拜拜佛。
1978年那年秋天,有个日本人来寒石寺院栽植了一颗五针松,象征友好纪念。11月15日,赵朴初第一次专程来寒石寺视察指导修复,两天后,有净持、果丰、法忍和我四位法师在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第一次着僧装,按照中国佛教仪规,隆重接待了以前田洪范为团长的“日本社会教育友好访华团”一行僧尼十七人。12月,我再次接待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及时向外国来宾友人宣传我国正在恢复落实各项民族宗教政策,拨乱返正,哈哈,接待很成功。上面的领导很高兴。
1979年开始,国内外的形势越来越好,来我寺参访的人数不断增加。这年,我接待过一些美国记者和德国的作家,他们代表西方文化界,来了解中国的宗教现状,我如实地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在进一步恢复和落实。
在这一年的7月份,昆城市人民政府民族宗教处正式恢复工作,及时召开了宗教界人士代表会议,认真研究落实宗教政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并在会上宣布由政府拨款,加速寒石寺院的整修工程。随后,从西园寺请回了释迦佛、两尊者、弥勒、韦驮及寒山拾得二圣的塑像,使寒石寺院具足了三宝,真正象了个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