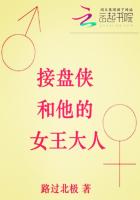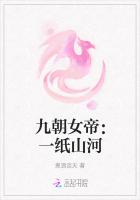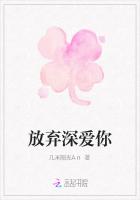中国抒情诗歌的“沉思“特质,还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有关。中国儒道互补的哲学文化结构,对于诗人心理结构有着同样的互补又互相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是儒家的人格理想,另一方面是道家的人格理想一方面不能忘怀于兼济天下,挣脱人与社会关系及其规范,另一方面,又崇尚独善其身,追求人格的独立。诗人又是每个时代社会心理的晴雨表,是最敏感者,最善于思考者。这两方面在现实中的矛盾,使得诗人的内心充满激烈冲突,常常有感而发。抒情诗歌中,面对大自然的沉思,不是一般的表现自然现象,而是“陶性灵,发幽思”。这是中国诗人的一种独特的哲理观念的体现,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中有着“道“的精神,有着物我关系在其中。曹操《性歪歌行》慷慨悲歌,从“对酒当”歌“到“天下归心是人生”情景,人生体验,也是“世界观”。但见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其博大的情怀和悲壮的感叹沉思,是以人类面对的最浩瀚壮观的景象为情感载体,而这些景象也是民族的情感库中最能表现崇高和悲壮情怀的原型意象。曹歪。黯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今君客游思断肠,慌慌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从自然现象写起,面对自然而使特殊心理感受“瞬间再现”。
明月殷殷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位妇女怀念丈夫,始终是在一个无限的时空中的沉思,星汉西流的自然现象和牛郎织女的原型意象,既充分表达了诗人的心理深层情结,也唤起人们的共同情感和精神感受。
在论述中国诗歌鲜明的“思“的特质的时候,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现象就是,东晋玄言诗中酝酿着山水诗的萌芽,这个过程表明了山水、自然与玄学的关系,抒情与沉思的关系。玄学是超世的哲学,它认为字宙的本体是玄虚的“道四时运转、万物兴衰是“道“的外观。从这种观念中引导出人对自然的体悟、追求,以及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观念。把深刻的哲学观照方式引人诗歌中来,同时巧妙地将它与一系列艺术形象相结合把体悟自然与阐述玄理结合起来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永恒与人生的短暂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古人似乎较能面对自然,在自然面前是深刻的思考者,而不能真正面对社会,在社会面前压抑了自己的情。故中国文学借助自然表达沉思,同时借助自然寻求精神的避难所,它的极端也可能偏向瞒和骗,找出奇妙的逃路来。
“象“与“道“和“原型“
中国古典抒情文学的精神特质和深层意蕴是“沉思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意识的结晶,它以“象“与“道“互为表里。“象的艺术符号性、抽象概括性和“表意“性,与“道“的哲理性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性,共同体现着中华民族长于利用抒情来表达深邃思想意识的特性。古典文学中象“意识的形成和围绕“象“概念的不断阐发,使文学中的“象“的特性和功能与领纷中的卦象有了本质上的相通之处。象是宇宙万物的另一种呈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象又是宇宙万物的范型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
“象“与原型有极重要的相似点,这使荣格对《易经》中的卦象及其意义大感兴趣,并因此将之纳入他的原型研究的视野之内。荣格曾与汉学家理查德·魏列姆(一译威廉)一起写作出版了《俭花之秘》一书。
在这本书里,这两位思想家考察了“在中国的神秘方法论与个人化过程,的当事人的体验之间密切的相似与对比《金花之秘》的文字所描述的冥想方法所出自的哲学在广泛程度上正是中国哲学的所有倾向所共同具备的。这种哲学以这样的一种观念为基础经过最后的分析,宇宙与人都服从同一法则,人是一个小宇宙,没有任何明确的界限把他和大宇宙分开。这些相同的法则一个接一个实现,有一条总线索使这条法则导向另一法则。心理之于宇宙,即内心世界之于外部世界。出于天性,人参与了一切宇宙事件,内在地诚如外在地参与其间。
他们意识到,中国哲学中的“道”、“道路“驾驭着人,同样道“也使自然(天地)成为可见与不可见。“道,这个未分的太一,赋予两个对立的现实要素以生命黑暗与光明,阴与阳调和这些对立物的方法成了金花的冥想主题。从中国哲学思想中,荣格发现了对于原型解释的新的思路。惕纷及其深奥的意蕴也是荣格所特别感兴趣的,荣格在《纪念理查威》一文中说惕纷中科学根据的不是因果原理,而是一种我们不熟悉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理。我们曾试图把它命名为同步原理(synchicprinciple)……我所关心的只是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即瞬间中隐藏着性质,竟然在卦象中变得明了起来。这种根据同步原理的思维,在《易经》中达到了高峰,是中国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中国哲学的中心概念是“道威廉把它翻译成为“意义我知道我们的无意识中尽是东方的象征,东方精神确实就在我们的门前。因此在我看来,对道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在追求者中间似乎已成了一种集体现象,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
这里对所谓“同步原理“和“瞬间中隐藏着性质兴趣,主要是与他的原型理论即集体无意识有紧密联系。荣格在晚年还论,与这里所说的“同步原理“具有同一性质。所谓共时现象,是指毫无因果联系的事件同时发生,它们之间似乎隐含着某种联系,荣格称之系辞为“有意义的巧合认为是某些经验的结果,荣格用共时性的概念来强调随机事件所蕴藏的丰富涵义,说明人的潜意识心灵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荣格从《易经》中可能发现了一个对他的原型观点来说至为重要的有直接启迪意义的观点,这就是人类心理体验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关系问题,即原型如何既承载着远古人的精神遗存又能与“当代“人心理相通,以及在不相关的事物中隐含着相通性。这个问题是维柯以来的许多人所感到困惑的。列维一斯特劳斯在他的研究中就竭力在表面现象中寻求不变的共同原则、注意文化的普遍的永恒性,这也和泰勒在《原始文千》中坚持遵循“人类心理同一的公式和文化直线式进化的律则“有相通之处。荣格要使他的原型理论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他就必须对人类心理的这种“同步原理“作出有力的说明,必须对瞬间中包藏性质作出合理地解释,而也《易经》的卦象无疑使他得到启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现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这里看重的就是八卦作为万物之“符号“的特性,它取诸天地万物,而有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使之具有“包藏性质“的功能和古今相通而“同步“的效果。而八卦的符号系统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原型“性质的“纯粹形式它将对人类自身(男女)的特性推衍于万物,抽象出阴阳“这一原型符号来推论和涵盖宇宙现象。这体现着中国先哲希图把握世界的雄心和努力,积淀着远古先民的精神遗存,它具有经过后天的特殊情境获得实在意义的功能。《易经》的神秘、深奥、深刻,是八卦卦象的这种原型特点所决定的。李约瑟博士指出,易主,解释愈抽象,这系统便愈有“观念的贮库”的性质,大自然的具体现象,便都可由这个系统去说明。
《易经》的每一符号,经过世纪又世纪,就具,有抽象的意义,颇能引人……“他认为《易经》是“涵蕴万有的概念之,库。
“象“的意义正在于“瞬间中包藏性质在于它作为特殊符号的功能。了解这一点,是了解中国抒情文学中作为艺术符号的“意象“的特性的关键。中国古典文学重“象就在于“象“具有荣格所说的“同步原理“的性质和“瞬间中包藏着性质“的功能。它能使人的情思与原型相通,触动人的深层的心理情感和体验。
由《易经》八卦可以看出,中国先哲们有将具象进行抽象、把感性体验凝聚为理性模式的能力,也有通过抒情来表达沉思的特性。原型作为模式、范型,它是凝聚了感性的生命、情感、体验的理性模式。原型的瞬间再现就是理性模式重新还原为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型是人类沉思的结晶,是体验的凝聚,是记忆的浓缩,是情感的升华,这在中国文学中就是“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是自然、社会和人的本原与始基,无处不在而又不可名状,它的存在方式与作为“纯粹形式“的原,型有相同之点。“道“是秩序儒家与道家对道的解释,都致力于探索生命之序与人生之序,而且它们的序的依据又都共获于“天人合一“模,式。伦理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序各种伦理规范地建立,伦理义务的,形成,都在于维持或稳定这个“序”。换言之,原型晾于人对天道的感悟,原型带有规律、“秩序“的含义,只是把这种含义与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意识特殊地联系起来。原型“再现“使“序“以人化的方式得到复活。中国叙事文学对情理的演绎,表达的伦理观念,就是对“序“的艺术阐释。
和原型一样道“不可言传而要通过具体物象《意象》才能解释,这在结构上十分接近原型。荣格所感兴趣的《易纷》和“道“与原型和文艺有无联系呢?荣格感到神秘和不可解释的中国哲学,正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抒情文学意蕴的决定性因素,文艺是原型的载体,也是道的特殊载体。周易是用来算卦占卡用的,它需要有意地使其语言重现出朦胧性、暗示性、多义性,有意拉开一段心理距离,并且充满可以激起人联想的词语,以发挥更大的想象力。而中国的古代诗词,在创作和欣赏中有着类似的情况。哲学意蕴通过文学方式(意象)反复表现,这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如人生苦短,人生如梦,生命可贵,独善其身,登高望远,精神不死,大浪淘沙等。哲理不变,但是文学意象却在不断组合,这种变与不变正是文学一方面具有永恒性,另一方面又避免了重复感的重要原因。
刘艇、根据《易系辞》中的学说,从宇宙形成的道理谈起,认为道“转化成阴、阳两仪,天、地、人三才乃至万物,也就并生出华美的“文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易经》“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国文学中渗透着天人合一“的观念,文学创作特别是诗词创作中具有物我的“神秘联系和互渗大量的意象则源于先民对原始自然物象的感悟。而这一切,说到底是人对自己与宇宙自然关系的感知、沉思的表现。
中国文艺原型的根本在于中国人的宇宙意识、“天人合一”。儒家哲学说“大乐与天地同合,大礼与天地同节“《易经》云天地钮氧,万物化醇。“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艺术之境表现于作品,就是要通过网幕,使鸿蒙之理闪闪发光。这秩序的网幕是由各个艺术家的意匠组织线、点、光、色、形体、声音或文字成为有机谐和的艺术形式,以表出意境。从原型与人的心理情感的倾向来说,诗“言志“抒情,诗词激活的是人生感悟、人与宇窗关系理解方面的原型心理,是以原始意象为中介的“当代“人的感悟与久远的“精神遗存“的沟通,诗词的写作和欣赏总与人生的永恒的课题相联系,其集体无意识通向邀远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它所唤醒的集体无意识似乎有先天“遗传“的意味。
中国抒情文学是最能充分表现人的原型心理的艺术,诗词中对于自然的感触、对于人生的体悟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一个艺术作品,是否通过意象(和意境)在其最深层次蕴含了理念,这种蕴含是否含蓄、深刻、巧妙,成为品评艺术作品价值高下的重要标准。而这里的理念,不是纯粹抽象的道理,而是人对天地万物、人生社会诸关系理解的一种概括,是“道是通过建立在感性体验基础上的个体情结而表现的集体无意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十分个性化,而杰出的作家的作品、人们对这些作品评价的标准,却实际是看它对于集体无意识、普遍情感表现的,程度。那些千古绝唱的特点不是对于某种事物描写的逼真和表现的形象,而是触及了普遍的情感体验。作品的艺术魅力,在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作品所揭示的心灵情境与具体情景下人的心理情感的对应,成功的作品正是在以揭示人的心理结构、心理体验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别人不可企及的境界。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作品能否透过具体的表现对象触及人类的普遍的心理原型,表现人的情绪的“记忆读者看到(领悟到)的是意象,而触及心灵深处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体验的模式是一致的或相似的。所谓欣赏者参与作品的再创造,不是说对作品所表现的意象和形象进行改造,而是由此及彼,由眼前的作品而想到自己人生体验和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作品确有其相对的“永恒“的价值,这种永恒不是题材,也不是主题,而是人类经过千百年的实践、积淀所形成的美感需要、美感体验和心理模式的具象化,是集体无意识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