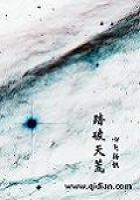——这真让我着急,你难道一直都回避吗?比如我爱你和你爱我这个早已存在的事实
夜晚一过,天空就放晴了。
我带王军去见了王萍妈妈,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她看上去小了一圈,卢达说:她一晚上都这么坐着。
她总是抚摸我,瞅着我直掉泪。“没有受伤吧?”王萍。
我告诉她:我们都很好。她还是不相信,对我看了又看,她似乎不敢把眼睛转向她儿子,直到王军叫了一声“妈”,她才转过头,这一望,就是狠狠的几巴掌,把我给吓了,王军就跪地上了。
我也叫了“妈!”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我的哥,我的妈。
没人注意到卢达,他慢慢向我们走来时,大家都还在悲伤中,他说:我也要出去一趟。只有我听见了这句话,我问他那什么时候回来?
他沉默着。
我抬头一看,院里站着两个警察。卢达会责怪我了,肯定会。
瑾子在二楼,我突然想到被打死的大猫,她也许还不知道,我跑上楼去,瑾子果然在,她漠然地问我:“我爸怎么了?”
“他要参与一些政府的调查工作。”
“会死吗?”
“这要问政府。”
我跟她说大猫被警察打死了,你好自为之,哭是没用的。说完,我就下楼了。听到她在唱歌,唱什么呢?原来是那首《樱花祭》。
我把这次所有的纪实全部给了骡子,连审都没审,这是一道疤痕,盖住了,我就永远不想去揭开。我打算重回新闻社。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
小洛真成了歌手,他说原来认真歌唱真是件美好的事情,比吃喝玩乐美好多了。我说到他的一些往事,他居然再不承认了。他和红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竟然如此和谐。就是有那么一天,他观看了红子的演出,一同走过了一条幽暗的小路,然后送红子回家,他们就开始了恋爱。
他邀请红子给他的歌编成舞。
然后我们看到歌伎馆的黑幕下:一条洁白的路,散布了粉的樱花,红子缓缓地踏过来,落地的团黑发髻和白色如羽的半祼和服,柔软而性感,意欲求他,但心绪不在,两目如水,顾盼生花,逼人的胴体和旷世的悲情,满世纪的青春都放在这个黑白世界里催发了。
那歌唱的是:
这里是花 香 地
夜夜在花 香 地
痴痴寻寻觅觅
来呀来呀 回忆
走呀走呀 失去
这么这么 轻易
只有只有 放弃
慢慢爱哪 爱哪 爱哪
你是我的印记
你和我的花香地
……
……
这里是花 香 地
夜夜在花 香 地
痴痴寻寻觅觅
甜甜蜜蜜 干净
快快活活 死去
看呀看呀 荒地
怎么一地灰烬
我爱哪 爱哪 爱哪
爱是美丽的传奇
你和我的花香地。
那歌听了,有悲惋的情怀。他长大了,终于开始明白什么是情怀。说他长大了的不仅是我,还有他的妈妈木木格,她总是感谢我,我不知道感谢我什么,我以往只是做了一件事:就是陪他玩。他那么相信我,真是我的造化,我想如果我编N个故事给他听,他也许也会相信。等他再大些,我就可以告诉他:那其实就是女人的往事,谁的都一样。
我们常在一起聚餐,我问木木格是不是会让小洛接管她的生意,她说不,这方面这孩子总是缺了点什么,他只要能认真做一件事,我就觉得行啦,我有时甚至不相信他是我儿子,是我的冤家。
2009年,春。
我该结婚了。
天边,一枚春日暖阳阳的落日和浪花的美丽,配上飘散的窗帷,有种催情的效果。突然大风吹过,抖落无数老叶,新叶在树上更新了,风把茶几上的几张新报纸吹落在地。
大伟对我伸出一根指头说:“只给你一天时间。”,像他这样伸出一个指头的动作,毛毛也做过。我至今都觉得大伟对于我来说还是太胖了,要是身材瘦点再瘦点就好了,最好再配个长发……,可是我却不能表现出这种心不在焉,因为那会伤害到爱我的人,正是因为这些爱我的和我爱的人才能成就现在的我。
我从浴室中出来,大伟试图跟我交谈,我回答他的总是一个字:嗯或者啊。然后,他就睡了,躺下去,就睡的晕天黑地。能这样睡觉的人,说明他对身边的一切都感到安全和满足。
我抹开镜子上的水汽,那镜子告诉我:你已经三十大几了。我翻开我的上衣,那对乳房还跟少女时一样坚挺,它们接下来需要抚育男人和孩子了,我从没有感到责任如此重大过。大伟说: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样就很好。
当然,如果里面多一个“没”字,这事就玩完了。
谁都不想这样。大伟就是我身边的一面镜子了,他将看着我一直走下去,到老,到死。
那么毛毛呢?
“那次夜半,在海边的半山涯我们遭到枪击……”
我坐在摄像机的镜头前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报道英模的记者找到了我,现在的记者——他们的深挖能力真是一代胜过一代。
我说有个灯头若往这边照的话,在电视上看起来,这人的脸就像一道菜一样。有人赶紧把那灯关了。我想这一刻,我的肤色会看上去很好。为了结婚,我花了不少时间去保养。大伟笑我:你结的不是婚,你结的是那场亮相。
他说对了,还叫我说什么好呢。我脸红了。
侧边的灯一关,我就隐隐约约中看到了骡子,他还那样抽着烟斗站在那位置。看到他,我就决定好了,准备啥都说,他们想问什么都如实回答。骡子是个极其敬业的男人,他会把我给他的那个纪录片做到极致。果然,他打开了他镜头。
“我们遭到枪击,后来是警察救了我们,毛毛当时也受了伤……当然,我知道那是一场抓捕。”
我记得,他就是受伤之后,不愿意下山去的,院外有四具被围堵的武警打死的尸体,其中有大猫。那个叫红中的公安以及所有的警察都在警戒和搜查,把江雪等人带离现场。谁也没有留意到王军扛着毛毛要往山下走,其实只要走过不到二米的山包,把毛毛抛下海,他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谁也不敢说是谁干的。
我望着王军把毛毛扛过去又扛回来。
“你难道真想坐牢,像我一样。”王军捧着毛毛的头。
“哥,你就别为难我了,我不想做神仙了。”
王军说像他这样的身体,到牢里去,是会死掉的。毛毛很倔,死也不肯离开。王军急了,拿了砖头就想往毛毛头上砸,他那意思就是:把他砸得半晕了,好扛走,只要往海里一扔,回头他还自己醒。是我拦住了王军,我死死拽住他胳膊,大哭。
他说我们都疯了。
我想过这个问题,像毛毛这样一个在逃犯,十几年后追捕回来,按所犯刑法论处的话,一般会判5-10年,他若表现好,可以假释,这其间若做出重大贡献还可以减刑,就算十年出来,他也是四十多,四十多岁的男人,还有再次成为好人的人生,这结果也很好,谁愿意终生躲藏呢。
红中一回头,就看到了我们几个,他还笑眯眯的,说别担心,有人民警察在,没问题。毛毛终于被红中带走了。他依然没有叫我等他,我也依然没说会等他,不过,我依然高兴,因为他被带走的时候,终于说:我爱你。
做为事件的一员,我参与了纪实片的所有过程,我把它给了骡子,他居然不接,他说这样的传奇若不续下去,就是罪过。
可是谁会知道续下去的结局是怎样?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从城市到监狱劳改农场要在小巴车上颠上六个小时,我总希望自己见他的时候可以很美的,可惜,我常常吐得面色腊黄。探监时刻,我和毛毛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把画板、画笔、颜料给他送去,他说等他出来吧,他现在干的是喂猪的活,他看到猪越喂越大,也很有成就感,要不,出来,我们也喂上几口猪吧。我说:我就是那头猪啊。他笑了。
我从没间断去探监,除非出差到国外,那我就要给他写信了。
亲爱的毛毛:
我给你写信的时候,外面闪着跟你眼睛一样的星星。
这里的街上都流行接吻了,我有点不适应,因为我还是喜欢自己的嘴唇住在你那里的感觉。我还是常常做梦,梦到你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的样子,还梦到你和一帮兄弟在一起,却怎么也不理我。这真让我着急,你难道一直都回避吗?比如我爱你和你爱我这个早已存在的事实。
其实,你和我在一起就好了。好好的吧,别折腾了,我们都青春不在了。事实证明,就是你喂的那些猪,折腾久了,也是会早死的。你说最近死了两头猪,总是难过,我建议你看看他们是不是到了随时会殉情的年华,如果是那样,你就是留也留不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们去吧。哈。
寄给你的东西都收到了吧,如果好吃你就多吃点。我在国外,居然还遇到了老同学,他们说的都是我们的故事,我和你、王军和李烟红,肚皮死了,他们都不知道,提到西瓜头,在他们印象中竟然还是一个复旦数学尖子,只有一个女人,想到在某个地方看到西瓜头做为重案犯被捕的事,她问我这人怎么了,干了什么坏事,是个坏人吗?我说:他是个不值得信任的人。我这么说,你会同意吧,我知道,你最不爱评价别人,但那个告密者不是你,那些路线图也是西瓜头提供给公安局的,这是事实。虽然他判的最轻,才三年,不过,他需要用一辈子去填满那三年的自疚。
我直到现在,还总是为李烟红这个名字感到悲悯。一个女人,为爱情什么都做了,还要她怎么样呢?难道爱到尽头,就只有一个死字了吗?你总是猜测她向公安局告密的真实原因,我告诉你:那双幕后的推手,其实就是对爱情的绝望。女人走到爱情的尽头,是可以摧枯拉朽的。别在为你当晚的事自责了,你已经为此自闭了十年,够了,这些再也追不回来的往事,不如就让它结束。
你提到的江雪,我去看过她了,她在监狱里还是一样会打扮自己,她的另一个儿子常去看她,那儿子比大猫出息多了,考上了大学,第一件事做的就是:报名勤工俭学。一看就是个有理想的孩子。别担心江雪,看到她对我展开的笑容,我简直不敢想像,这是一个曾经费尽心机要杀你的女人,看来政府的教育比什么都强大,她甚至开始写自传了,也许二十年后,她就是社会主义新人了。她还叫我一定要告诉你: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她现在已经知道了真相,对西瓜头充满了恨,对你充满了悔恨,原来恨和悔恨之间需要走这么长的时间,这就是人生的印记吧。她现在看的书,名字是《追风筝的人》,看完之后,估计恨和悔恨都没有了。
你总是把我推给王军(我现在还叫哥),别这样伤害自己,对大家都不好。他一直以为告密的人是你。后来知道了李烟红和西瓜头联合告密的事,他现在失掉了对女人的感觉,不是因为不爱,是爱不起来,他给我看李烟红买的许多东西,他甚至把红子接到了家,他说在红子身上他总能看到李烟红的影子,我看他终于知道自己的爱在哪里了。不是我,是烟红。
我们下次见面时,你还像以往那样,把你的手伸给我吧。
那感觉真好。
爱你的我。
我每次去国外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东西回来,相信结婚时可以用上。毛毛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在去探监的路上,遇到了车祸,我只是轻伤,他却不知道,得了些消息,就要从监狱出来看我,差点被看守一枪打死,还好,这监狱有知道我身份的人,他就这么被几个狱警压送着到医院看我,手脚都是拷子,一步步地挪,那场景,至今也忘不掉。我想,就是死了,也值了。
事情坏就坏在他太心急了,平日里总是高要求自己,巴不得减刑。
关于监狱所在地区爆发泥石流的事,我也是到后来才知道的,监狱长带我去看他的尸体,他说:“这真是个好人。”
听说,他救出了八十头猪,只有一头死了,保住了国家财产,他却死了。
他为的根本不是财产,而是为了赚点表现分,可以减刑。
他到底是走了一条通往好人的路,可是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让我为他的不辞而别欲哭无泪。
“你们还有要我说的什么吗?”我问在灯光下看不清楚脸的记者。我想纪实片到此就该结束了吧。
“他什么都没留给你吗?”
我知道我若认真回答这个问题,我终究可能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哭的。于是,我想了想说:“爱”。
骡子让大伟扶我回房休息,那些记者收拾好东西,就可以走了。那你呢?我问骡子,这纪实片拍到现在该结束了吧。
他说:“是。”我说,钱就不用分给我了,都献给爱国主义事业吧或者其他什么他能想到的都行,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别用我的名字,用毛毛的。
我一回房,就看到了那幅画。我的花香地。
明天——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就是我结婚的日子,请祝我幸福!
(2009年三月三十一日完稿)